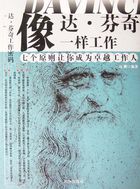一
我又一次被推进了手术室。长长深深的走廊尽头,丈夫搀着女儿的手翘首站立着。这个画面在我的脑海里将会保留永远。
术后的三个月我忧心忡忡地迎送着每一天,我以全部的精力极其敏感地关注着自己身体的点点变化。每过去一天,我就减少一分希望,增添一分恐惧。终于,我必须面对那个可怕的结论了——高位截瘫。
我终于知道了什么叫生不如死。我预感到自己必死无疑。
在痛不欲生的哀泣和呼天抢地的大哭中,我整天想的就是一件事情:我怎么去死?什么时候死?采取什么方式去死?
对我而言,生和死都很痛苦,而站在这两者的临界点上更痛苦。
半年以后,我回到了家里。回家带给我的是更加巨大的刺激和悲恸。
看见久未转动的缝纫机我会泪流满面:我的女红极好,我曾经用它缝制过一件又一件漂亮的衣服,每完成一件,都能得到家人和亲友们的交口称赞。而如今,我再也无法让它转动了。
望着一大堆我的裤子和鞋子,我更加痛不欲生。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一直是一个很注重仪表的人,而这一场变故使我这些心爱之物一下子成了废物,这种心痛的感觉,我至今仍无法用笔来描述。
由于我大小便失禁,只能一人独睡一张小铁床。往日我与丈夫同眠的大床因为只留下丈夫独卧而显得格外的空旷。我只要对那张大床瞥上一眼便会忍不住抽泣半天……
这一场病,老天居然把我做人的权利和做女人的权利统统剥夺得精光……
回到家里,我给家人带来了无休无止的麻烦,使一个原本和谐温暖的家蒙上了一层凄楚的阴影。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讨厌累赘的大包袱压在了家人的头上。
二
在那些日子里,我整日整夜泪眼蒙眬沉默寡言,家里人越是为我忙碌我就越是痛苦。我的脑子里想的只有一件事情:我怎么可以这么自私地永远拖累他们?他们可是我最爱的人啊。
深思熟虑之后,我决定行动了,趁家里无人之际我藏起了一把锋利的剪刀,准备在合适的时候在股动脉上深深地剪上一刀,这样就能彻底解决问题了。
真的到时候了,我又犹豫了,我的眼前有许多割舍不下的东西在奔涌:
我舍不下我的丈夫,我们心心相印一路相携走到今天……
我舍不下我的女儿,她从小就懂事可爱。在我小病住院的时候,她每次来看我总会精心准备一个故事为我消愁解忧……
我舍不下我的公公婆婆,他们一直很疼爱我……
我知道,我这一去就是永别,永生永世都无法与他们相见了……
可我只想让他们解脱,不想离他们太远……
我犹豫了,我松开了紧握剪刀的手。在辗转痛苦之中,我为我自己找到了短期生存的理由:我要看到我的女儿考取重点中学后我再离开人世。而在这期间,无论再苦再难,我都必须尽到一个母亲的职责。
我极其困难地拿起了织衣针,我决定要将家里所有的毛衣都翻织一遍,这既是为我的远行做准备,也是因为心有不甘。在此之前小姐妹们多次问我是否有毛衣需要她们帮忙代织。这样的关心居然使我伤心不已。在我的记忆里这类事情一向都是别人有求于我,现在怎么一切都要颠倒了?
倔强的我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后终于又重新拿起了织衣针。我仰卧病榻,举手而作,每织一针都很艰难。当我看见我的女儿穿着我用心用泪编织成的第一件毛衣出门去赴宴的时候,当我将家里的毛线参照流行时尚编织出一件件漂亮适用的衣物的时候,一种悲喜交加的自豪感油然而生。渐渐地,我的亲戚也会拿来一些毛衣请我帮忙,我也会编织一些新颖别致的小孩衣裤来馈赠朋友。单位里举办艺术节,我的编织品居然还得了奖……
时间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着,我终于如愿看见女儿考进了重点中学。可我的床边还有许多没有织完的毛衣。我的远行计划看来暂时还无法实施。我隐隐约约觉得自己是在寻找活下去的理由。
此时我的生活又增添了新的内容:听广播,看书报。渐渐地,我融入书中了,我会随着书中的内容一起思考了。我能够和书中的伟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倾心交谈了,这样的交谈使我聪明了许多,也坚强了许多。
日积月累,我逐渐有了用文字梳理自己思绪的能力,能够用笔与外界交流,偶尔还能有文章在报刊上发表。面对这些,我的喜悦也是难以形容的,要知道,我连初中也没有毕业呀。
岁月匆匆,我早已将我的“远行”计划淡忘了,虽然病躯的痛苦依然天天在提醒着我,但我已不再绝望。我看到了我的前方有着点点的光亮,我已越过了生死的山界。
三
当灾难初临的时候,我在极端的痛苦之余还有着很多很多的害怕。我害怕丈夫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我害怕从此以后我瘫卧在床只有索取没有回报会把他压垮。
当我哭干了眼泪稍稍恢复常态之后,我就开始细细观察我丈夫的一举一动,因为我实在太在乎他了。如果他的表情中有一丝一毫的嫌弃和厌倦,我就马上会撒手归西。在我的生活中,可以没有面包,可以没有阳光,但必须拥有微笑。这是我的原则。
我没有失望,我的丈夫给了我所需要的一切。他和我一起与死神拔河,奋力把我拉回了人间。他给了我一个永远也不用害怕不用担心的安全的港湾。他将我们俩患难之中的情感演绎得丰满而富有内涵。正是这种感情使我远离死神,使我活得真实,活得有力,活得满足。
当然,在我的满足中也夹杂着一种常人无法体会的难言的苦涩。可恶的病魔残忍地把我们这对恩爱夫妻演变成了一对兄妹。我们已经失去了寻常夫妻间特有的肌肤之亲。我总是将自己丑陋不堪的病体显示在丈夫面前,我每天需要他帮我干最脏最累的事情,将他折腾得劳累之极。我们近在咫尺,却只能异床而同梦。正是因为这些,我几乎每天都是拥着收音机带着腮边的泪慢慢入梦的。
这些年来我一直想给我们这种残缺而凄美的生活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有一天,我终于想到了这样一个比喻:我们就像两条并行的铁轨,虽不相交但又永远相伴……
房金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