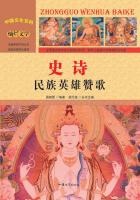迈克尔·法拉第仅仅听到了戴维教授的4次讲演,可那是具有多么重大意义的4个夜晚,对法拉第来讲,正是1812年早春的4个夜晚,他才感到时间飞跃了。戴维教授的举止言谈深深地打动了他,激励着他。通过听讲演,使他看清了今后自己应该走的路,他已下了决心,应该毫不犹豫地从这条路走下去。
在里波先生的小阁楼里,他坐在自己的小桌子前,借着昏暗的烛光,重新整理戴维的讲演稿记录,真像是重理旧梦一样。他的笔记本里,又出现了戴维教授,出现了他演讲的情景,法拉第的目光和戴维的目光相撞了,那不仅仅是目光的相触,那是法拉第与戴维科学的相会。可这毕竟是过去,是逝去的梦。戴维带着他的新婚妻子去了,可法拉第,还回到布兰福德街2号,过去他从不厌烦和他朝夕相处的铜尺、胶水、裁纸刀、纸面、布面、小牛皮面……所有这些东西再也引不起他的兴趣了。
他已经在美丽、庄严、圣洁的科学殿堂里游历过了,那里的阳光灿烂,照得他心里又光明又温暖。新的世界、新的环境强烈地吸引着他。他是一粒种子,一粒科学的种子,过去被抛在岩缝里。他没有抱怨,没有自暴自弃,以顽强的毅力,从石缝中发出了幼芽。他已瞥见了阳光,要他再钻回去那是不可能。他要生长,他要向着太阳生长,他是科学的种子,他要在科学的道路上长叶、开花直至结出丰硕的果实!
科学研究需要时间,需要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他科学的青春,科学的生命,不能总是一辈子和刀、尺、布(纸)面、胶水打交道,不能总是纠缠在这破旧、简陋的瓶瓶罐罐堆里,这里是不会有什么大发展的。迈克尔最可惜的是他没有充足的时间,他给他的哲学会的朋友艾伯特写信,其中他这样写道:
先生,我需要的只是时间,我要大声疾呼——我需要时间。我们现代上流社会的先生们闲得无聊,要是我能出低价论钟点——不!论天,买一些他们的时间,该有多好!
迈克尔·法拉第整天思索着,怎么办好呢?最好、最简单、最直接、最快的方法是向亨弗利·戴维爵士请求帮助,可惜他走了,短时间内他不会回来。除了戴维,还有谁呢?他想起了约瑟夫·班克斯爵士。然而,迈克尔又想,自己从未和这位英国科学界的头号人物见过面,没有什么交往,人家忙不过来,又哪里肯愿意搭理他这个无名小卒呢?但是,在皇家学院说了算的人里,他再也想不到别人了,就找他,先写封信试试。他下定了决心,拿起了鹅翎笔,开始写信了。
可这封信却让他犯难了,怎么称呼呢?怎么开头?他的手有些不听使唤,写几个字,不行,太不好看了,扯掉。又写几个字,不行,再扯掉。好不容易,他的信才写成。他写了自己的经历和爱好,写了自己的理想和希望,他向班克斯爵士表示愿意到皇家学院来工作,不管干什么都行,只要是为科学服务,他就心甘情愿,就获得了最大的幸福,等等。
他把写好的信揣在怀里,边走边寻思,慢慢腾腾来到了艾伯马尔街21号。大门紧闭着,他依旧是在大门口来回踱着步,不过他这次不是等待门开进去,而是等待里边的人出来。等啊等啊,就是不见有人出来。这时,路过此处的人告诉他,这里如果没有什么特殊,大门是不开的,人们进出都走旁边的小侧门。他来到侧门口,刚想举手敲门,忽然又犹豫起来了。他想,这不是一件小事情,这样草率从事可以吗?他以前可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是否应再考虑一下呢?他的脑海里千头万绪。他首先想起了家庭,爸爸、妈妈的养育之恩,哥哥的帮助,不都是希望自己将来有个出息吗?可惜爸爸两年前已经去世了,如果爸爸还活着那该多好。迈克尔想到了自己这些年来的刻苦努力,他点点滴滴地看书学习,积累知识,他一丝不苟地实验,虽然仪器设备简陋,但也锻炼了动手操作的能力,他能完全听懂戴维教授的讲演,不仅图文并茂地记录下来,而且还有相当的补充,说明自己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这些年来,一直在黑暗中摸索、徘徊,现在应该获得光明。
想到这里,迈克尔终于鼓足了勇气,他伸手敲门了。门还真的开了,从里面出来一个年老的仆人,法拉第似乎觉得,就是他第一次来听演讲时看到的毕恭毕敬地出来迎接戴维夫妇的那个穿制服的人。可仆人今天可没有像那天那样谦恭,他用鄙夷的眼光在法拉第那身破旧的衣服上上下下地打量了许久,险些把本来就不结实的衣服看出个洞来。他不无傲慢地开口问:
“年轻人,有什么事?”
年轻人好像是让他给瞅呆了,忽然把怀里的信递给了他。他又歪着头打量了年轻人一番,然后,“啪”的一声把门关上了。
法拉第坐卧不宁地等待着,布兰福德街2号,每从外面走进来一个人,他都在心里暗暗发问:“是送约瑟夫·班克斯爵士的回信吗?”不是的,没有回信。他表面上好像埋头干活,实际上心不在焉,是在暗中等信。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一个星期过去了,还是不见约瑟夫·班克斯爵士回信。法拉第实在忍不住了,他想,这大人物对下人的上访或请求回信,可能不需要别人送,是让自己去取,如果方便的话,就地就解决问题。他又来到艾伯马尔街,这一次仆人没有出来,只是把门打开一条缝,连瞅都没瞅法拉第一眼,只说了一句:
“约瑟夫·班克斯爵士说,你的信不必回复。”说完就把门关上了。
法拉第急得在地上直跺脚,可他无可奈何。皇家学院的门关上了。“难道永远关上了吗?”法拉第问自己,“难道我就是这个命,难道我注定一辈子做订书匠吗?”自己这些年的辛辛苦苦难道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不,这不可能。是的,法拉第是一个敢于同命运抗争的人,他要用自己的奋斗改变命运,他决不会坐等命运来安排自己,只要自己坚持不懈地努力,机遇就一定会到来。他等待着,寻找着。
1812年10月,法拉第满师了。他成了迈克尔·法拉第师傅了。现在他比较自由了,他可以回家里住,可以登门到别人家里去干活,也可以应聘到别的店里去干活。他经人介绍,来到了法国人德拉罗舍先生的书籍装订铺。
现在的老板是一个典型的生意人,不像里波先生那样心肠好又善理解人。他不理解法拉第的心思、爱好和对科学的旨趣。在他看来,法拉第的职业是订书,一个好雇员的唯一标准是专心订好书,不务别的外业,工作期间更不准搞“副业”,否则就是见异思迁,不守本分。化学实验与订书有什么关系,看书对订书有啥帮助?法拉第被里波先生惯坏了,现在该是由他来管教了。在他的书铺里是不允许看书的,当然更不允许进行化学实验这种玩意儿了。
法拉第热爱科学,但伦敦的科学界当时并不知道这个无名小卒。环境催逼,更使他萌发了跳出现在职业圈子的念头。他给市哲学会里的朋友医科大学生赫克斯特布尔写信说:
我还在干我的老本行,一有机会我就将设法离开它。关于科学的进展,我本来就知道得很少,现在更不可能知道多少了。确实,只要我目前的处境得不到改变,我就不得不让位,让那些有幸比我占有更多时间和金钱的人去思考学术问题。
正当法拉第发愁没有机遇的时候,机遇却悄悄来到了他的身边。
戴维夫妇的蜜月旅行,原计划要在苏格兰的首府爱丁堡多住些日子。戴维夫人,这个出身贵族、身材娇小、黑头发、黑眼睛的美人儿过惯了上流社会的生活。她喜欢享乐,喜欢在舞会上、在歌剧院的包厢里展示自己的美貌和魅力,她喜欢幽居乡间,也喜欢出入宫廷。她心里有着如意的计划,他们新婚夫妇可以到幽静的苏格兰乡间别墅,在那里钓鱼、吃野餐,充分享受大自然的快乐。她带着戴维探亲访友,特别拜访了她的一位远亲,当时英国有名的诗人、小说家瓦尔特·司各特爵士(1771-1832)。她一方面是为了向丈夫显示自己出身的高贵,另一方面也向自己的亲朋好友炫耀自己嫁了一个多么英俊潇洒、才华横溢的有贵族头衔的科学家。这样,就可在亲友和丈夫之间无形中抬高了自己。可戴维的生活方式即是工作和娱乐相结合。他知道是蜜月旅行,即便如此,让他停止工作,停止他的化学实验,也会使他憋死的。他旅行出发的时候,就和夫人商量,要带上一箱化学仪器,有空时可进行他的实验。爵士夫人觉得,这样带着仪器、带着科学一起进行蜜月旅行,更富有浪漫主义情调,也就同意了。
可是,事情的发展往往出人意料。戴维的朋友安培(1775-1836,法国物理学家,对电磁学中的基本原理有重要发现。为纪念他,电流的单位称做“安培”)从巴黎给他写信来,告诉他发现了一种新的氮和氯的化合物,这是一种很容易爆炸的液体,制造它的迪隆先生不小心炸掉了一只眼睛和一只手指。
这个消息对戴维是极大的刺激,他虽然还年轻,但在科学的疆场上却是身经百战的老战士,现在,战友负伤了,他就应毫不犹豫地冲上去。他用随身带的仪器,在苏格兰开始做这个实验,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再前进一步那已是不可能了,因为他缺乏设备仪器,也没有良好的实验条件,况且这种实验又很危险,也不能够在一般的场合随便进行。他和夫人商量,打算提前结束蜜月旅行回到伦敦。商量的结果是,夫人允许他一人先独自回伦敦。
戴维回到伦敦,就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很少有人知道他回来,法拉第根本不知道。他实验不久,就发生了一起爆炸。他给妻子写信告诉她是发生了一起意外的“小事故”,让妻子放心,那是不要紧的。可事实上他伤得很厉害,头上、手上都绑满了绷带,眼睛也遭到损伤,医生告诉他,至少要几个月不能进实验室。
法拉第知道戴维回到伦敦,并且在家养伤的消息是这一年的12月。他渴望戴维回来,可现在的戴维又出现意外事故,这对法拉第的打击很大。法拉第心想,戴维是他进入皇家学院的唯一希望所在,如果不马上找他,恐怕要失去机会。如果现在写信或亲自登门,的确有点不太礼貌,况且,戴维正在养伤期间,已经闭门谢客了,所有公私事务暂停办理。法拉第又犯难了,怎么办呢?想来想去,最后,他还是决定立即给爵士写信,因为他相信,戴维爱科学胜过爱生命,他的这封信即使戴维爵士现在看不到或不能看,将来一定能看到。到那时,他的追求科学、酷爱科学的急切心情,一定会得到戴维爵士的理解和同情。
他给戴维爵士写信,言词比上次给约瑟夫·班克斯爵士写的信更加恳切。他把这封信,连同自己整理装订的《亨·戴维爵士讲演录》一起送到了皇家学院。
法拉第给戴维先生送去了一份“厚礼”,虽然里面的精髓是戴维爵士送给他的,可他回赠给戴维爵士的却是加进了他的血汗和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
戴维爵士收到法拉第的信件大约是在圣诞节前,当时他的伤还没有痊愈,尤其是眼睛,看东西还十分吃力。那天早晨皇家学院的仆役给他送书信,他一眼就瞥见一本四开本的大厚书,书脊上印着几个烫金的字:“亨·戴维爵士讲演录”。戴维觉得奇怪,自己从来没有出版过什么讲演录,也没有什么人借讲稿联系出版事宜,这突然从哪里冒出来这一本书?难道是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抢在英国的前头,出版了他的讲演录?戴维爵士好奇地信手把书翻开,发现是手写的。它的封面上用工工整整的手写体写着:“四次讲演:化学哲学纲要讲座的部分记录,亨·戴维爵士(法学博士,皇家学会秘书,等等)讲于皇家学院。迈·法拉第记录整理,1812年。”
戴维爵士怔住了,他哪曾想到,自己那四次讲演总共才4个多小时,可这位听众之一的法拉第竟整理记录了386页!这哪是记录,这仿佛是在改写,是在原来基础上的增补和扩充。讲过的内容都记录下来,与此有关的许多没讲的内容也都作了大量的补充。娟秀的书法,精美的插图,严肃认真。这字里行间熔铸了多少爱戴、敬仰和信任!这是一种多么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这本洋洋386页的大作,作者又是谁呢?扉页上写着是亨·戴维爵士。不,应该是迈·法拉第。这位法拉第又是谁呢?戴维寻思,他一定是一位老成练达、富有实践经验的一位中老年科学工作者。这里有一封他本人写来的信。戴维爵士忍着伤痛,从头到尾详详细细地看了这封信,他吃了一惊,这书的作者竟是20岁刚出头的青年学徒工。
戴维被深深地感动了。他看了法拉第的经历,想起自己。十几年以前,自己不也和今天这个写信的法拉第一样吗,出身卑微,家境贫穷,没有享受充分的学校教育的权力,上帝和世人给他安排的命运是当学徒工,出头露面之时是一名工人师傅……可是,自己……他从法拉第的成长过程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勇敢地面对人生,向命运挑战,大胆地追求本来就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对未来充满了希望,珍惜青春,艰苦奋斗。
戴维看了《亨·戴维爵士讲演录》,那书记录完满,整理、誊抄工整,装订漂亮、精致。他感觉到自己从前工作过程中,有很多欠缺的地方。戴维精力过人,他在实验室里紧张工作就像战场上打仗一样。他常常几个实验同时进行,这里加热、煮沸,那里过滤、蒸发、结晶,有时人家以为他实验刚刚开始,他却收拾东西已经结束了。他的实验节省了大量的时间,但也有问题。为了短时间内记录下全部的几个实验过程,这不仅需要有速度,还要求分门别类,在几张纸上记录。所以记录起来,戴维常常是笔走龙蛇,龙飞凤舞,忙中出差,错记、篡记在所难免。出现错误,他就大笔涂改,有时这不够劲,就索性用大拇指在墨水缸里蘸一下,在写错的地方一按,他的实验记录别人是很难看懂的,有些地方他自己再看时也得仔细推敲。他工作大胆,有魄力,敢干。有一次做水煤气的实验,他猛吸了三大口,险些把命送掉;他工作显得杂乱,不够严密,不够细致,而法拉第,从《亨·戴维爵士讲演录》就可以看出,他的工作是那样的有条不紊,严密细致。戴维心里十分清楚,那样的习惯和作风将来对于科学研究是多么的重要啊!
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出现在自己的面前,虽未见其人,但凭着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他知道法拉第诚挚、勤奋、坚毅,有天分,有献身精神,摆在自己面前的这本《亨·戴维爵士讲演录》就是绝好的证明。他缺少的只是机会,他实在没有能力为自己找到机会,才最后向我请求。我该怎么办呢?这事已经在戴维的心中占据一定的位置,他这几天老是思考着。圣诞节前夕的一天早晨,戴维遇到佩皮斯先生,他是皇家学院最老的理事之一。
“佩皮斯先生,有一事我想听一听你的意见,”戴维对佩皮斯先生说,“这里有一封信,是一个名叫法拉第的青年人写来的。他听到我的讲演,做了一份详尽的记录,并且誊抄清楚,整理成一本书给我送来。他热爱科学,请求我录用他到皇家学院来工作,你看我能叫他干什么呢?”
“干什么?”佩皮斯先生说,“叫他洗瓶子吧!要是他还有点用,那他就会来的,要是他不肯来干,那他就是个没用的人。”
“不,不,”戴维说,“我们得试一试,让他干好一点的工作。”
就在当天晚上,皇家学院的戴维爵士给韦默思街的法拉第先生写出了回信。
先生:
承蒙寄来大作,读后不胜愉快。它展示了你巨大的热情,记忆力和专心致志的精神。最近我不得不离开伦敦,到一月底才能回来。到那时我将在你方便的时候见你。
我很乐意为你效劳。我希望这是我力所能及的事。
先生,我是你顺从、谦恭的仆人。
亨·戴维
1812年12月24日
戴维是当时公认的第一大化学家,他发表过许多的科学论文,也写过不少的诗篇,然而,他的“最伟大的作品”却是写给法拉第的这封短信,因为正是这封信,造就了人类历史上又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戴维一生中最自豪的最感到有意义的是发现了法拉第。在他看来,他发现的钠、钾、氯、氟等元素都是不值一提的。
1813年1月,戴维通知法拉第到皇家学院相见。法拉第激动不已,整个心怦怦地跳个不停,像急着要飞出来一样。他来到皇家学院。戴维的助手佩恩先生领他到讲演大厅的前厅等候。这时的法拉第竟不知道是站着还是坐着,门开了,他无限敬仰、无限期望的、也是他将来的大恩人戴维爵士迈着轻快的步子进来了。他没有架子,热情地招呼法拉第说:
“来,来,坐到这里来,法拉第先生,这里靠窗,亮一些。”
法拉第感觉轻松了许多,他走过来和这位伟大的学者并排坐到了一起。
“法拉第先生,你的笔记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戴维说,“很显然,我讲的你全都听懂了。你从哪里学到这么多的化学知识?”
“我在书籍装订铺工作,”法拉第腼腆地说,“自己看了一些书。我还听过塔特姆先生的讲演。另外,我在家里搞了一个小实验室,我能够做到的,都亲自动手做一遍。”
戴维听着法拉第的话,频频点头说:
“嗯,很好,很好。可是,法拉第先生,我能帮你什么忙呢?这样吧,将来我的书全都交给你装订,皇家学会、皇家学院的书也尽量都给你装订。”
“谢谢您,先生,”法拉第说,“可是我对装订书籍不感兴趣,我希望能到皇家学院来工作,做什么工作都可以。”
“你想献身科学,是不是?”
法拉第点了点头,他有点脸红了。
“年轻人,也许你想错了。牛顿(1642-1727)曾经说过,‘科学是个很厉害的女主人,对于为她献身的人,只给予很少的报酬。’她不仅吝啬,有时候还很凶狠呢。你看,我为他效劳十几年,她给我的就是这样的奖赏。”戴维伸出手,指着自己手上、脸上的伤痕给法拉第看。
“这个我不怕。”法拉第说。
“可是年轻人,”戴维看着法拉第那张倔强的嘴,微笑着说,“这里工资很低,或许还不如你当订书匠挣的钱多呢!”
“我不在乎钱多钱少,先生。”
“嗯,别这么说,将来也许你会后悔的。”
“我不会后悔的,先生。”
其实,双方对谈到这里,主考官的心里已经很满意了,他已决定录用了。可他却没有表露出来,却继续询问法拉第:
“法拉第先生,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到底为什么决心从事科学工作?”
“我对买卖不感兴趣,先生,那只是为了赚钱,自私自利。可是科学工作是为了追求真理,科学家都有高尚的道德感情。”
戴维听到这样严肃的话从这个青年工匠嘴里说出来,不禁哈哈笑了起来。
“年轻人,你到这里来待上几年就会改变这个看法了。”戴维看了看墙上的钟,站起来说,“这样吧,年轻人,你先回去,现在皇家学院没有空缺。以后需要人的时候,我再来找你,行不行?”
法拉第再三感谢爵士对自己的关心。因为兴奋,他的脸上红彤彤的。他正要告辞,戴维又说:
“你走以前想不想看看这里的实验室?它在地下室。”
“那太好了,先生。”法拉第高兴地说。
他们一起走出前厅。戴维边走边说:
“实验室里又脏又乱,满地都是破碎的玻璃屑,你见了一定会摇头的……”
这时佩恩先生从走廊那头走过来。戴维见到他就说:“法拉第先生,再见吧!佩恩先生会送您出去的。”
法拉第又一次感谢了亨弗利·戴维爵士,向爵士行礼道别以后,跟在佩恩后面下了楼。他们一行来到了一楼。
“走这里。”佩恩指着出门口,粗声粗气地说。
“戴维爵士让我看看实验室。”法拉第对佩恩说。
“戴维爵士让我带你出去。”佩恩瞪了法拉第一眼。
皇家学院的大门又一次在法拉第的身后关上了。可这不同于前几次,门虽关上了,但不是永久地把他谢绝于门外,而是为他下次再来留有余地。外边很冷,可是刚出门的法拉第一点也不觉得冷,出门时佩恩有意给他加了点凉风,可它未冲淡在室内获得的戴维爵士加给他身上的热能。
法拉第情不自禁,想呼喊,想歌唱,但他还是控制住了自己。虽然和自己崇敬的戴维爵士真挚交谈,他已看到科学仿佛向他招手,可是这空缺什么时候才会出现?它能不能是位虚假的主人,光向客人招手而不让客人进屋呢?戴维是肯定不能,那么其他人,佩恩会不会设置什么路障呢?事未成,还是先别高兴得太早。他自己告慰自己,其实已大可不必了。
不久以后,法拉第接到戴维的通知,叫他到皇家学院来帮几天忙,帮助戴维整理手稿。对于迈克尔·法拉第来说已是时来运转了。又过了十多天,戴维的助手佩恩和皇家学院制造玻璃仪器的师傅发生口角,佩恩举手就打,打得这位师傅鼻青眼肿。戴维当场就把这个脾气暴躁的佩恩解雇了。3月1日,皇家学院理事会的议事录上有这样一条决议:
亨·戴维爵士将有幸通知本理事会,他已经物色到一个愿意接替威廉·佩恩职务的人。他的名字叫迈克尔·法拉第,是一个22岁的青年。根据亨·戴维爵士的观察和了解,他是这项职务的合适人选。他作风正派,积极肯干,性情和善,聪慧机敏。在佩恩先生离职的时候,这个青年愿意按照同样待遇在本院工作。
决议:把佩恩先生的职务授予迈克尔·法拉第,待遇照旧。
迈克尔·法拉第全然不知这一切,但他第六感觉,觉得有人经常在背后议论自己。这位刻薄的东家似乎看出这位平时寡言少语、手艺出众的年轻人恐怕在这里待不长了,就开始挽留法拉第。他说,法拉第人很老实,能干,心眼好,手艺又高,他自己没儿没女,将来只要法拉第留下,就可以将这店铺传给他,等等。学徒出身的人能当老板,又能继承一笔钱财,这在一般人的眼里是最神圣不过的了,可是法拉第却对这些“财运亨通”不屑一顾。
几天以后的一个夜晚,法拉第已上床解衣,忽然听到楼下有人大声敲门。他把头伸出窗外,看到戴维爵士的马车停在狭窄的韦默思街上。法拉第抓起放在椅子上的衣服,边跑边穿奔下楼去。车夫递给他一封信,是戴维爵士写来的,通知他明天到皇家学院去。
法拉第谢过车夫,借着从窗子射出去的微弱灯光,拆开了戴维的信。戴维告诉他,如果他的意愿没有改变的话,他将获得实验室助手的职务,周薪25先令,外加皇家学院顶楼的两间住房。
皇家学院的大门终于打开了,法拉第是再兴奋不过了。法拉第打点行装,辞别了东家德拉罗舍先生,义无反顾地大踏步走入皇家学院这科学的圣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