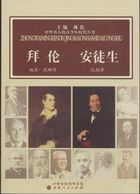迈克尔·法拉第在和市哲学会会员的接触中已经知道了许多东西,如皇家学院是干什么的,来历如何?戴维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身世如何?
皇家学院是一个美国人倡议建立的,这个美国人颇具传奇色彩。他的原名叫汤普森,1753年出生在北美,他的家境也不富裕。少年时代当过学徒工,靠刻苦自学,成了一名教师。从此时来运转,和一个有钱的寡妇结了婚,使他年纪轻轻就发了大财。北美独立战争爆发后,他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逃到一艘英国军舰上来到英国。不久在英国官场上崭露头角。1784年他又冒险来到慕尼黑,替巴伐利亚国君效劳,很快赢得了新主人的青睐,当上了国防和警察大臣,被封为神圣罗马帝国伦福德伯爵。从此这个光宗耀祖的姓氏跟随着他,后人就只知道伦福德伯爵了。
伦福德伯爵有一个最大的爱好就是喜欢科学,可当时的科学还只是掌握在有钱人手里的奢侈品。因为科学研究需要设备仪器、图书资料、场地馆所、辅员助手,一般资产的人是很难办到的。同时,科学研究还需要大量的时间,当时的科学家和大众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老百姓不知道科学家是干什么的,而不少科学家也只是蹲在屋子里埋头实验,根本不关心老百姓的需要。伦福德伯爵就是想改变这种科学和生活相脱节的状况,使科学为生产和生活服务。
1796年,伦福德伯爵来到伦敦发起募捐,想组织起一个带有慈善性质的学术机构,伯爵看到许多人都没有受过教育,生活十分困苦,就想到创办一个慈善性的学术机构,来赈济贫苦人民,对他们进行职业技术教育,向他们传授科学知识,使之能获得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同时也是为了促进新发明、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发挥其社会作用,改进社会生产和生活。伯爵的倡议得到伦敦上层社会的广泛响应,一些贵族官僚,特别是在工业革命中受益的工业资本家,很多都成为伯爵倡议的此项活动的财东。
1799年,伯爵用募捐来的钱,开始筹建慈善性学术机构。他在艾伯马尔街买下了一幢四层的大楼,把里面的房间改建成讲演厅、实验室、图书馆和办公室,取名为英国皇家学院。由英国皇家学会的会长约瑟夫·班克斯爵士(1743-1820)任院长,伦福德伯爵任理事会秘书,掌握实权。
创建皇家学院,本来是面向穷苦大众,可一些工业资本家的财东们说,皇家学院是应该为穷苦人服务,但是首先应该为工业服务,因为只有工业发展了,穷苦大众才能找到比较好的职业,才能改善生活条件。这样,慈善性的学术机构就演变成纯粹的学术机构,它和公众发生关系,仅仅在于它定期举行的各种通俗科学的讲演。来听讲的也不是穷人,而大多数是有钱有势的有产阶层。皇家学院的化学讲座主讲人是格拉斯哥安德森学院的加内特教授,由于他不善辞令,新近又死了妻子,口才和情绪使他的讲演乏味而无生动性。伦福德伯爵就开始物色一位新的人物来代替加内特。听讲的好多人都不约而同地向伯爵推荐一个年轻人,这人就是亨弗利·戴维。
戴维出生在英格兰西南的彭赞斯,他家世贫寒,十几岁时,父亲就离开了人世,他的母亲虽然很能干,但仍无法养活未成年的五个孩子,戴维不得不在16岁时当了学徒工。这是他的外公和母亲替他选择的人生之路,他的师傅是一位药剂师。外公和母亲认为,像戴维这样贫穷家庭出身的孩子,将来能当上个药剂师,那就很不错了,他们没有什么非分之想。可戴维自己不这样认为,他有自己的想法和打算,就是在开始学徒的那一年,他就为自己制订了一个庞大的学习计划,计划开设的学习科目很多,单是语言方面,就有英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希伯来文共7门。他并不满足于大人们为他设计的药剂师的这个行当,他当时感兴趣的是化学,他就自己悄悄地研究化学,决心将来当个化学家。他从研究光和热的现象入手,很快就提出了自己的独立见解。虽有独到之处,但也不难看到青年人长于想象而忽视实际的臆想因素的存在。尽管如此,他发现,冰互相摩擦,能够融化成水,这为热运动理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他把自己的发现寄给里斯托尔的名医贝多斯教授,教授对他十分看重,认为这青年将来必大有作为,不能等闲视之。
不久,贝多斯先生创办克利夫顿气体疗养院,在由谁来主持这个问题上犯了寻思,最后,他想到了这位年轻气盛的戴维。他向戴维发去了热情洋溢的邀请信,戴维更巴不得结束这学徒生活,他告别了彭赞斯,来到了克利夫顿,任气体疗养院的院长,当时的戴维,还不满20岁。
贝多斯教授在疗养院里做了大量的实验,戴维有时观看,有时动手操作,使他的实验能力有很大提高,名气也越来越大,小小的疗养院自然留不下这个大凤凰了。
他被介绍来伦敦,来到了艾伯马尔街21号——英国皇家学院。伦福德伯爵看到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二十几岁的毛头小伙子,还带有乡音,很不以为然,心里充满了担心,为了稳妥起见,他还是让戴维先在小讲堂里进行一次试讲。戴维看着左右,从容不迫地走上讲台。伦福德伯爵微闭双眼,煞有介事地坐在下面,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戴维一开讲,声音倒很好,伯爵一怔,接着往下听,内容也相当好,遣词造句都十分恰当,如果能记录下来,那一定是一篇优美出色的好文章。
伯爵听到这里,开始有些心动,他上下打量着这位令他刮目相看的才子,他个子不是很高,但是身材比较匀称。讲话举止言谈大方,动作机敏,真诚坦率,一副惹人喜欢的样子。再看他的手,上下摆动,打着手势,多么灵巧。那是做实验的手,那是发现真理的手,那是创造事业的手。
戴维讲完了,所有听讲的人脸上都充满了喜悦,有些坐在后面的老者,还特意走到前面,摘下老花镜,仔细地瞧上这年轻人几眼。
戴维很快就得到了任命,任命他为皇家学院助理化学讲师并兼任实验室主任和出版部助理编辑,年薪100畿尼,外加免费住房和煤火费。他得到英国皇家学会会长兼皇家学院院长约瑟夫·班克斯爵士、伦福德伯爵以及皇家学院的一些名人的器重。从此,一个从外地来到首都的乡下年青人,跻身于英国科学界的巨子之列,平步青云。
一年以后,23岁的戴维被任命为皇家学院的化学教授。他口才好,又有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因此,他的通俗化学演讲风靡伦敦,吸引着成千上万的听众。到皇家学院听戴维教授讲演,谈论电呀、元素呀、合成、分解呀,已经成了上流社会的时髦。700个座位的讲演厅时常是座无虚席,而且两侧的过道上挤满了人。听众里面还有很多青年女子,她们为才貌双全的戴维所倾倒,有很多女子还向他寄来了十四行诗,表示爱慕之情。一些达官显贵纷纷来信表示祝贺,这些他都放到了一边。他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埋头在皇家学院的地下实验室里,晚上不是作演讲就是参加晚宴、上戏院、玩弹子、读小说。他的生活充实,工作起来忙得如痴如狂,玩起来也是兴致十足。
戴维成为一颗耀眼的科技新星,在英国乃至全世界迅速上升,1803年,不满25岁就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805年,获得英国皇家学会的最高荣誉——柯普莱奖。他的演讲不仅吸引了大批的听众,也为皇家学院吸引来了大量的捐款,他靠自己的奋斗,赢得了人们的爱戴!
1807年底,戴维生了一场大病,前来探望关心他的人实在是太多,有时连皇家学院的大门也都被前来探望的人拥挤得无法开启,没有办法,只好在皇家学院的大门口插上了一块“戴维教授病情公报”牌,以缓解人流。生病后的第二年,戴维没有举行演讲,结果皇家学院的年收入竟减少了四分之三。
戴维到皇家学院以后不久,伦福德伯爵就和法国化学家拉瓦锡(1743-1794)的寡妻结了婚,搬到巴黎去定居了。戴维教授成为皇家学院的灵魂,由于他的努力,皇家学院已经成了英国的科学中心。他对于氯气的研究、他发现的钠和钾,给全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伦福德伯爵和戴维教授,尤其是戴维教授给迈克尔留下的印象太深了。迈克尔想,他们都和自己一样,都是学徒工出身,他们靠自己的学习、自己的努力,不仅踏入皇家学院并且成为其中的举世闻名的人物,难道我就不能吗?命运就真的让我做一辈子学徒工吗?戴维先生22岁进入皇家学院,可自己也是20出头的人了,皇家学院对他来说是那样的神秘,那是上流社会有钱有势人出没的地方,像他这样衣着破旧的穷学徒,如果没有引荐,他是永远也不会进入皇家学院的。然而,又哪有有势之人或科学界的名人认识他、了解他呢?
迈克尔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中,他希望终于有一天,有人能把他带入皇家学院,能够亲自聆听戴维教授的化学讲演!
然而,这一天已经不远了。
因为里波先生人善,脾气好,既讲信用又不误事,不少科学界的人士都把书送到他的订书铺来装订。一天,皇家学院的当斯先生腋下夹着一沓书稿,来到了里波先生的订书店。他把书稿交给里波先生,没说上两句话,自己竟朝坐在角落里的法拉第走去。
当斯先生比较熟悉法拉第,里波先生向他介绍过,并且把法拉第整理装订的《塔特姆自然哲学讲演录》给当斯先生看过。里面详尽的记录、工整的字迹、精美的插图,都使当斯先生赞叹不已。他前几次来也曾经注意过法拉第,在他的印象里,法拉第不是一般人,他干活既快又好,不仅能很好地装书,而且还能很好地“编”书,奇才,奇才呀!
法拉第也认识当斯先生,知道他是皇家学院的,也曾向他请教过问题,但只是一般的认识,还没有什么深交。当斯先生向他走来,两眼注意地望着他。迈克尔看到当斯先生向自己走来,就放下手里的活计,一边点头示意,一边拿起一本厚厚的书,准备请教。
当斯先生知道法拉第要向他请教,可他不等法拉第开口,就开玩笑说:
“迈克尔,你老盯住我,像蜜蜂叮住花朵一样。你把我的蜜采光喽!”他拍拍法拉第的肩膀,笑着说,“今天你别问我。我来问你,你到皇家学院去过吗?”
“没有,”法拉第说。
“你想去吗?”
“当然……”法拉第有些犹豫了,他不知怎么才好,“嗯……先生,您问这是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意思,就是问你想不想去?”
“去干什么?”
“去听讲演,听戴维教授讲化学。”
“真的?”法拉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过,他知道,这当斯先生是绝对不会开这个玩笑的。这太好了!他举起双手大声欢呼着。
“怎么?”当斯先生又半开玩笑地问,“不想去吗?”
“哪里,我太想去了!我听人家说,戴维教授的讲演好极了。英国——不,全世界找不出第二个人,讲得像他那样好。”
“你听谁说的?”
“听市哲学会的人说的。”
“你是市哲学会会员?”
“不,我还没有参加市哲学会。不过我常到塔特姆先生那里听讲演,和他们常见面,有时还和他们一起讨论问题。”
“你晚上下班以后再赶去,一定很累吧!”
“不,”法拉第说,“讨论起问题来,就一点也不觉得累了。”
当斯先生看着法拉第,看到年轻人那双清澈透明的大眼睛,泛出了一片特别动人的柔和光彩。他觉得自己仿佛看到了年轻人圣洁的内心世界和无比渴望的满怀激情,看到了年轻人的理想,看到了他的远大抱负和追求!这样的人才哪能失掉,失掉太可惜了!
“年轻人,你对一切都感兴趣。你对戴维教授的讲演也一定会感兴趣的。你拿去吧,去听吧!”当斯从衣袋里掏出四张入场券塞在法拉第手里。
“当斯先生……”
法拉第还没来得及道谢,当斯先生已经拿起礼帽,轻轻地扬了一下,走出了书店。他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法拉第这年轻人,这学徒工,真是很特别呀!”
迈克尔追到窗口,当斯先生已走在街上了。太阳照在他的身上,他的全身都在发光发热。
法拉第的梦想成真了,他像要出嫁的新娘一样准备着,郑重地迎接那一天的到来。对于法拉第,这几天怎么过得这样慢,白天觉得天黑得慢,黑天又觉得天亮得慢。他耐住性子,盼呀,等呀,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1812年2月29日,这天晚上他早早地吃完晚饭,换上了星期天上教堂才穿的干净衣服,急匆匆地走出了里波先生的铺子。
2月的伦敦,天黑得早,昏暗的街灯照着行人道上一行人在积雪道上急速地走着,身后的影子一会儿由长变短,一会儿又由短变长。这些,法拉第看不见了。他心里只记着皇家学院,只记着戴维教授的讲演,只想着到艾伯马尔街21号的近路怎么走。他拐过几个弯,来到了皮卡迪利广场。这里是伦敦的花花世界,有灯红酒绿的建筑、熙熙攘攘的人群;有马的嘶鸣声,也有人的欢笑声。这些,法拉第不仅看不见,也听不见,他像一个在荒野里赶路的人一样,匆匆又匆匆,穿过广场,来到了艾伯马尔街。
法拉第突然停住了脚步,他的前面是一幢灰白色的四层大楼,楼的正面是14根高大的柱子,柱子上方的石檐上刻着“英国皇家学院”。法拉第的心怦怦地跳起来。他当学徒已经6年了,6年多来,这个地方他来过几次。然而那只是路过而已,这座对他来说既庄严又神圣的殿堂并没有向他招手。可是今天,这座殿堂的门终于对他打开了。6年多来,他的每一个便士、每一段空闲时间,他青春的全部光华和热力,统统都奉献给科学了。他没有过高的奢求,他对科学的热爱,只想得到科学的回报。这一时刻终于到来了,他兴奋,他喜悦,他激动!虽然里波先生的铺子离这儿不太远,可对于他,好像是经过千里迢迢的长途跋涉才来到了这个新世界的门口。
然而,皇家学院的大门还是紧闭着。他知道,这是他来得太早了。他在艾伯马尔街上来回踱着步,心里想象着,那讲演大厅里是什么样子,那里一定会有很多座位,也许还有桌子可以放笔记本吧!那戴维教授一定是风度翩翩,英俊潇洒……
忽然,在他的身后有马的嘶鸣声,他赶紧向旁边躲闪,只见一头高头大马拉着车停在他面前,从车上走下一位头戴黑色礼帽、身穿黑色衣服的绅士,手里挽着一位身穿皮大衣的贵夫人,这两个人刚下车,皇家学院的大门就朝他俩首先敞开了,从里面走出来一个穿制服的差役,毕恭毕敬地把那绅士和他的夫人迎了进去。这时,三三两两的听讲的人开始往门里走,他们有些坐车来的,也有步行来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穿戴整齐。法拉第不禁低下了头,虽然他穿了自己最好的衣服,可那裤子上已经出现了经纬条。他觉得脸上有点发烧,深深地倒吸了一口凉气,掏出票子,跟在别人后面,走了进去。忽然,他听到有人叫他,原来是当斯先生笑呵呵地从里面迎了出来。
啊!真太好了。有当斯先生陪着,法拉第觉得自在多了。当斯先生领他上了楼,从大演讲厅的后面走了进去,这里的座位一行一行是阶梯形排列的。法拉第拾级而下,在第七排中间坐了下来,他的座位下面是一条过道,没有安放椅子,他前面有一条栏杆。他坐在这里居高临下,既看得清楚,做笔记也方便。他略舒展一下身子,从旧书包里掏出了笔记本和笔,焦急地等待着。这里,其他人在声音不大不小地议论着,可迈克尔根本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
戴维终于出现了,坐得满满的大厅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戴维迈着十分轻快的步子,边走边向大家招手,来到马蹄形的大讲桌旁边,向大家点头致意,然后向前走了两步,站在讲桌的中央,微笑着面向大家,大厅里顿时安静下来。
“女士们,先生们,这一讲……”
他讲的题目是“发光发热物质”。他精神抖擞,神采奕奕,讲得是那样的轻松自如,却又是那样的明晰透彻。物质的光和热,连同他天才的光华和热力,正从他身上向整个大厅散发,向整个世界散发,一直吹到人们心里,每个人的心里都觉得暖洋洋的。大厅里的无数双眼睛,从不同的高度、不同的角度愣愣地盯着他,一动不动地倾听着。法拉第也和他们一样,聚精会神地看着、听着。忽然,他马上想起了什么,赶忙打开笔记本,先写上发光发热物质,然后就飞快地记录着,翻过一页又一页……时间像是长了翅膀,不一会儿,一小时的讲演结束了。
法拉第躺在小阁楼的木床上,两只圆圆的眼睛一动不动地望着天棚,他失眠了。他一次又一次地回忆那美好的时刻,时间只有一小时,可这甜美的夜晚,法拉第一辈子也忘不了。过去的梦,如今真的变成了美好的现实,这样美好的时刻对法拉第还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
美好的时刻是那样的短暂,美好的时刻的间歇却又是那样的漫长,它不仅给人们留下了咀嚼,留下回味,同时也给人们留下了更美好的时刻和向往。
4月9日,法拉第和前几次一样,早早地来到讲演大厅,仍然坐在靠近过道里的那个位置上。戴维教授讲的题目是“金属”,那是他最熟悉的,他要讲的钠和钾这两种奇妙的金属都是他用自己发明的电解方法制造出来的。如果不是他,换一个别人,谁来讲都没有真情实感,都不会像他那样具有说服力。他拿出一把镊子,从一个装着油的玻璃瓶里夹出一粒黄豆大小的银灰色的东西。他说:
“诸位一定都这样认为,金属都是沉甸甸的。但是,请看这粒东西,它就是一种新的金属,我们把它叫做钾,比水还轻。”
戴维把手里用镊子夹着的那粒黄豆大小的钾粒举起来给大家看,然后把它轻轻地放在一个装着水的玻璃缸里。“噗”的一下,水面上冒出一小团美丽的蓝紫色的火焰,那粒银灰色的钾缩成一个球,带着那团火焰在火面上飞快地打转,一面发出轻轻的咝咝声,渐渐变小,转眼就消失了。这时,水面上又迅速恢复了平静。听众们在惊讶,在议论,在赞叹。法拉第在飞快地写着,他记下了实验的过程,也画下了戴维实验所用的所有仪器。
讲演结束了,但是戴维并没有走,今天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日子,他不愿意离开讲台,他心里好像还有更多的话要跟大家说,可他说什么呢?10年前,当他开始登上这个讲台的时候,他就曾说过:
“人类财富和劳动的分配不平等,地位和生活条件有差别,这是文明生活的力量源泉,是它的推动力,甚至可以说是它的灵魂。”
不管人们赞成还是不赞成,戴维用自己这10年奋斗和成就,证实了自己的主张。谁敢勇于面对现实,并坚持不懈地为现实而奋斗,谁就是强者。
戴维是强者,他胜利了。就是在昨天,他从摄政王手里接过爵士的绶带和证书,他已经成为亨弗利·戴维爵士。他以自己的科学成就,为自己赢得了贵族的头衔和称号。他的婚礼将在后天举行,昨天的授爵,成为他新婚的最好贺礼。结婚以后,他将和新娘一起到苏格兰去蜜月旅行。广大的听众都知道,他已决定今后不再作通俗化学讲演了,他将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创造性的科学研究工作中去。人们还晓得,戴维已经把自己的决定通知了皇家学会的会长兼皇家学院的院长约瑟夫·班克斯爵士,已经得到批准,这已是不能更改的了。今天,是戴维教授首次以爵士身份在这里讲演,也将是他对广大听众的告别讲演。
他的心情有些激动,同时也有些留恋,他不时地看着过道上面正对着他的那座大钟,他认为还有时间,他应该再讲几句。但他的心里却不知道说什么好,那就随便谈谈吧,谈谈科学、文艺的进步和国家经济的关系吧……
那么年轻、那么幸福、那么光芒四射的亨弗利·戴维爵士告别了皇家学院的讲坛,告别了听众,他走了。对于戴维的离去,大家自然有些依依不舍。有些人10年来场场必到,从没有漏听一次。可迈克尔·法拉第如果没有当斯先生的帮助,戴维教授的讲演他将一次也听不到,那将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
大厅里的人都走了,只有法拉第还在那里,默默地画着、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