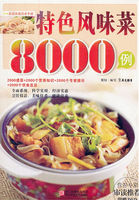又到了秋天。中国人一到了秋天,就会被一种横行的动物挑动味觉神经。尤其住在江南水乡,更是近水楼台先得蟹,晋代诗人毕卓就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到了唐代,许多诗人干脆住到船上,“相逢便倚蒹葭泊,更唱菱歌擘蟹螯”。到了宋代,甚至有人嗜蟹成痴,还特别编写一本《蟹谱》,详细说明螃蟹的种类、习性之外,最重要的还是如何吃螃蟹。
蟹在江南是美食,到了北方,可就成了稀罕之物,不是有钱有闲之人,恐怕消受不起。北宋的首都开封虽是繁华之地,可是螃蟹仍是稀罕。一回,桌上有新鲜的螃蟹,仁宗随口问问价钱,可了不得,三十八只螃蟹费钱二十八千!(当时用制钱,一千钱一串,二十八千者,二万八千钱,这可是一般中上人家好几个月的伙食费)连贵为皇帝者,听了这价钱都觉得心疼,于是下令撤去不食。只是皇帝不吃,大概也没得退的,最后还是便宜了那帮太监。
其实,运输不便,也不见得能阻挡人类的口腹之欲。唐代能千里迢迢地运送荔枝,何以北宋时期就不能运输螃蟹?想来是因开封地处华北,饮食习惯不可食无肉,但对鱼虾没有太大兴趣。南宋时期,首都迁到了杭州,近鱼米之乡,就不可一日食无鱼了。
的确,江南多水泽,鱼虾蟹蛤生长容易,在古代运输不易,多为就地消耗,除了趁鲜食用外,甚至有人将蟹肉挑出,做成汤包的馅料,如果加上蟹膏、蟹黄,就是蟹黄包子,而用蟹肉作馅的饺子,也好吃极了。
螃蟹当令之际,解决螃蟹供应过多的另一种必要做法,就是将肥美的母蟹用盐水、料酒加上各种小料腌渍几天,做成“脍蟹”,切开之后,即可食用。
我的一位老师,原籍苏北,在上海求学,颇好饮食之道。因为只身在台,在宿舍中包伙,但遵医嘱,必须忌口,诸肉不宜,老是嫌“口淡”,每次有同学探望时,就要借机会下馆子解馋。我经常陪老师到一些老江浙馆子吃家乡口味,吃风鸡、干丝加上煨面之类,就可以让老师高兴许久,但是到了秋高气爽、螃蟹上市时,就非吃炝蟹、蟹黄包子不可了。
可惜,当时大闸蟹未能进口,台湾吃的螃蟹多来自金门;现在已经方便,前两天,大闸蟹已经抢先在台上市,但老师作古有年,终究没有吃到真正的家乡味;倒是去年秋天,我趁前往南京开会之便,来到江南吴地看看鱼米之乡,也尝了原乡的大闸蟹。
当时,车子从南京出发,一路东南行,经溧阳、金坛等地,逐渐进入吴方言区,耳边尽是轻声细气的吴侬软语。车到宜兴,在熟人引荐之下,找到当地一家颇负盛名的餐厅,东道主殷勤劝酒之际,也端出大闸蟹待客,上桌时,真是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只见一盘十只的大闸蟹,五公五母紧偎相依,一碟姜丝一碗醋,更凸显食材原味。
主人殷勤待客,说大闸蟹是惯吃之物,远客应当多多享用。于是,我并老实不客气地用禄山之爪,将这些无肠君统统祭了五脏庙。
螃蟹虽是好吃之物,却给人“横行霸道”的刻板印象。当年日军占领华北,著名的画家齐白石多画螃蟹,观者还以为画家喜欢吃螃蟹,等到齐白石写上“看你横行到几时”的评语之后,大家才了解此中原有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