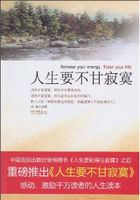黄宗羲在《原君》中愤怒地谴责了历代君主的不人道,他说:“其既得之(天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这话真是千真万确。宫廷内有两种人专供王、后享乐。一类人是歌舞演奏者。据《文献通考》,“唐全盛时,内外教坊近及二千员,梨园三百员”。又有资料说,散乐三百八十二人,仗内散乐一千人,音乐人一万二千人。杜甫说:“先帝侍女八千人”,并没有夸张。第二类是“宫人”,由皇帝的妻妾和普通宫女组成,这类人有多少没有统计,白居易在《长恨歌》中说“后宫佳丽三千人”,这是诗句,不是确数。《唐会要》载,太宗时,后宫里“无用宫人,动有数万”。《旧唐书》载,玄宗的武惠妃死后,“后庭数千,无可意者”。再用《新唐书》中关于释放宫人的记载来印证:太宗即位后,“放(高祖的)宫女三千余人”;中宗复位后,“放宫女三千人”;肃宗即位后,“出宫女三千人”;德宗“罢梨园乐工三百人”,“出宫人”(无数据);顺宗在位仅一年,“放后宫三百人”,又“放后宫及教坊女妓六百人”;文宗“出宫人三千,省教坊乐工,翰林伎术冗员千二百七十人”;武宗在位六年,宣宗(在位四年)即位后“出宫女五百人”;懿宗“出宫人五百”等。数字表明,中唐以前,每次出宫人三千,这大概是“吐故纳新”,若以三分之一计算,内宫约万人左右。唐中宗时全国户数六百余万,人口三千七百余万。这就是说,六百个家庭中有一家的女儿要到宫中服务。如果加上皇亲国戚、各级官员、豪门贵族的女佣女妓(官妓、家妓)在内,又不知有多少家庭的女儿要受罪。所以,在唐朝特别是盛世的繁华里面都浸透了唐代妇女特别是少女的辛酸眼泪,这也正是唐诗中宫怨诗、闺怨诗特别多的原因。
唐人写宫词宫怨诗几乎是一种时尚。宫内的人写,了解宫内生活的宫外的人写,连与宫廷未沾过边的人也爱写。写宫词的“专业大户”有三个:一是花蕊夫人,仿作宫词一百五十多首,她曾得幸于后蜀国君孟昶,亡国后又被宋太祖所获,属于熟知宫内生活的;二是王建,有宫词百首,是唐人写宫词的祖师爷,他的同宗兄长王守澄是“内官”,宫词内容都来源于这位在宫内供职的宗兄;三是后唐和凝,也写宫词百首,不知有何特殊经历,恐怕只是附庸风雅。以上是就内容真实性而言,写得好的当然是王建,但最能表现宫人哀怨的、艺术成就较高的宫怨诗还是白居易、元稹、张祜等大诗人的诗。
先看王建《宫词百首》第九十首:
树头树底觅残红,一片西飞一片东。
自是桃花贪结子,错教人恨五更风。
诗中的宫人看到桃花纷纷纷坠,便责怪五更风使坏;仔细一想,“自是桃花贪结子”所作出的牺牲,怪不了风;再将自己的命运同桃花相比,在宫内耗尽了如花的青春,又有什么值得留恋的结果呢?自己是在为谁作出牺牲呢?诗的意蕴是很深的。
再看白居易的《新乐府·上阳白发人》:
上阳人,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
绿衣监使守宫门,一闭上阳多少春。
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
同时采择百余人,零落年深残此身。
忆昔吞悲别亲族,扶入车中不教哭:
皆云入内便承恩,脸似芙蓉胸似玉。
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
妒令潜配上阳宫,一生遂向空房宿。
宿空房,秋夜长,夜长无寐天不明:
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
春日迟,日迟独坐天难暮:
宫莺百啭愁厌闻,梁燕双栖老休妒。
莺归燕去长悄然,春往秋来不记年;
唯向深宫望明月,东西四五百回圆。
今日宫中年最老,大家遥赐尚书号。
小头鞵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
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汝。
上阳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
少苦老苦两何如?
君不见昔人吕向《美人赋》,
又不见今日上阳宫人《白发歌》!
这首诗还有一个副标题是“愍怨旷也”(怜悯哀伤女子不让结婚,没有丈夫)。正文前还有个自注:“天宝五载(746年)已后,杨贵妃专宠,后宫人无复进幸矣。六宫有美色者,辄置别所,上阳是其一也,贞元(785—805年)中尚存焉。”事情是真实无疑的,但诗人从杨贵妃专宠,其他后宫人得不到皇上宠幸的角度去“愍”这位上阳宫白发宫人,却是很肤浅的。据《新唐书》介绍,唐制:皇后而下,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是为夫人。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是为九嫔。婕妤、美人、才人各九,合二十七,是世代妇。宝林、御女、采女各二十七,合八十一,是代御妻。计有一百二十二人幸加上六尚、二十四司、二十四典、二十四掌,计二百人,还有其他名目不算。即没有专宠,没有妒忌,不可能个个得到宠幸幸;即个个得到宠幸,那,是不文明,不人知的。成百上千的少子供皇上一人之淫乐,这是何等的专制和野蛮!如果说这,算婚姻,那只能说是为了加强皇族势力,维护家天下的婚姻!是禽兽的婚姻!然而,诗的内涵与作者的主观意图并不能画等号。诗中被“潜配”(暗中软禁)的老宫少是封建时代千千千千个宫少的代表,她的命运和遭遇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充分暴露了封建宫廷的黑暗、残酷和野蛮。
白居易诗的丰富内涵被元稹浓缩在了一首五言绝句中: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张祜的一首《宫词》则直白地叙述了宫人远离父母和家乡,幽闭深宫的悲惨遭遇,抒发了恨君(而非思君)的怨情:
故国(家乡)三千里,深宫二十年。
一声《河满子》(曲),双泪落君(皇上)前。
离宫(皇帝正式宫殿以外的宫殿)的宫人命运尤其悲惨。少少时被选入宫练习歌舞,专供皇上到离宫来了侍奉他,谁不一辈子,不不知皇上是什么样,老死了就埋到苑墙城外,丛冢累累,不不知道葬了了少少少的一生。杜牧的《宫人冢》中就有真实的记录:
尽是离宫院中女,苑墙城外冢累累。
少年入内教歌舞,不识君王到老时。
唐代有不少宫人实在忍受不住这种精神折磨了,便写诗并巧妙地寄出禁苑,表达自己对自由和爱情的向往追求。有一个天宝时的宫人把诗(《全唐诗》名之为《题洛苑梧叶上》)题在梧桐叶上,随御沟流出去了。诗人顾况看到了,只见上面写道:
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
聊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
这位青春少女禁于“深宫”,过着“不见春”的监狱般生活,到哪里去寻求“有情人”呢?只能出此下策,以抒发心中的悲痛。多情的顾况立即和了一首诗,题于叶上让它漂回,《全唐诗》名之为《叶上题诗从苑中流出》:
花落深宫莺亦悲,上阳宫女断肠时。
君恩不闭东流水,叶上题诗寄与谁?
诗中的同情和疑问深深深动了这位宫女,于是写了《又题》》放入御沟流出:
一叶题诗出禁城,谁人酬和独含情。
自嗟不及波中叶,荡漾乘春取次行。
这“一叶”原本寄托了自己的幻想,没想到真碰到了“含情”人的独和;可惜我不如波中梧叶,可以乘着春天随便任意(取次)地漂出“禁城”啊!
天宝宫人开启了先例后,历届宫女都仿着去做。宣宗时又有一位韩氏宫女在红叶上写了一首《题红叶》,放入御沟流出宫禁。
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
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
这片题诗的红叶被到京城应举的卢偓得到了,这位渴望“到人间”的“深宫”少女的一片痴情感动了他,于是把红叶珍藏于箱底。后来宫里放出部分宫女,卢偓娶到韩氏,韩氏为得知音而感慨叹息不已。能有这种圆满结局的会有几个呢?绝大多数的宫女只能在悲苦中煎熬。
唐代的盛世带给女性的苦痛另一突出的表现是闺怨。唐诗中的闺怨诗特别多,就反映了这种现实。从内容分,闺怨诗又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征夫之妻的闺怨,二是商人之妻的闺怨,三是宦游者之妻的闺怨。
唐朝的统一、稳定和繁荣,与战争武力是分不开的。初唐、盛唐时期,有征服四方、对外扩张的战争,还有边镇戍守;接着有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中唐以后又有藩镇割据的战争和朝廷镇压叛乱的战争。唐代的男子特别是青壮年则首当其冲。仅边镇戍守常年就有六十万,京城宿卫十二万,打起仗来则无数量限制。据,新唐书》兵志介绍,太宗贞观十年规定:“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禄(箭囊)、横刀、砺石、大觿(解结用具)、毡帽、毡装、行縢皆一,麦饭九斗,米二斗,皆自备,并其介胄(盔甲)、戎具藏于库。”又规定:“凡民年二十为兵,六十而免。”平时每年服役一月以上,战争时无限期。男人服役去了,女人在家,既要种地养蚕,又要操持家务,扶老携幼,还要供应丈夫的衣物,忍受独居之苦,其闺怨之深可想而知。
葛鸦儿是个劳动妇女,其夫服役去了,到了轮换时也不见回来,她在,怀良人(丈夫)》诗中写道:
蓬鬓荆钗世所稀,布裙犹是嫁时衣。
胡麻好种无人种,正是归时底不归?
这首诗反映了征夫之妻持家的贫苦和艰难。丈夫不在家,百事集于身,没有钱添制新衣、好衣,唯一的一条布裙还是出嫁时带来的;无钱买首饰,只好用荆条当钗管束头发;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去打扮,弄得蓬头垢面;芝麻(胡麻)要种好、收成好,必须夫妻合种,现在只能由我一个人种,丈夫啊,到了你轮回时为什么总不能回来呀?
中唐诗人张仲素,写了很多乐府歌词,流传较广,秋闺思二首》就很有名。
碧窗斜月蔼深晖,愁听寒泪湿衣。
梦里分明见关塞,不知何路问金微。
秋天一夜静无云,断续鸿声到晓闻。
欲寄征衣问消息,居延城外又移军。
前诗中女子的丈夫是在金微(山名,在今新疆北部、蒙古西部的阿尔泰山)驻防,路途遥远,音信全无,只能梦中到边塞去搜寻丈夫的身影,但又不知道金微山在什么地方。后诗中女子的丈夫在居延城(今内蒙西部)戍守,日夜挂牵着他,有时整夜睡不着觉,由秋雁声想到寄信给丈夫,秋天到了要给丈夫寄冬衣了,谁知向官府一打听,“居延城外又移军”了,移到哪里去了呢?这冬衣寄不到,丈夫如何过冬呀?
陈玉兰是吴(江浙地区)人王驾之妻,她的《寄夫》诗表达了戍人之妻的共同心声:
夫戍边关妾在吴,西风吹妾妾忧夫。
一行书信千行泪,寒到君边衣到无?
上述征夫之妻虽然忍受着各种痛苦,但对丈夫的回家团聚总还抱一线希望,而裴羽仙连这一点希望也失去了。当得知丈夫征戍在外,因为深入敌军被擒而音信断绝时,她写了《哭夫二首》。
风卷平沙日欲曛,狼烟遥认犬羊群。
李陵一战无归日,望断胡天哭塞云。
良人平昔逐蕃浑,力战轻行出塞门。
从此不归成万古,空留贱妾怨黄昏。
这“力战轻行”是统帅的失误,丈夫“从此不归成万古(死了)”,再怎么“望断胡天哭塞云”,也无望了,那“空留贱妾怨黄昏”的日子该怎么度过呀?这裴羽仙的命运只是成千上万,甚至十万百万征夫之妻命运的一个缩影。
唐代的商业十分发达,除了国内的市场,还有国际市场,经商的人数很多。行商的特点是成年累月在外奔走,这就带来两个问题:一是丈夫的安全问题,说不定就会遇到匪盗或翻船之类;二是丈夫很少回家,有的竟在外宿妓(商业发达处妓女很多),根本就不回家。这样,担心丈夫和怨恨丈夫就成了商人之妻闺怨诗的两大重点内容。
李白走南闯北,见事很多,他的《江夏行》就是写商人妻子的悔恨的。
忆昔娇小姿,春心亦自持。
为言嫁夫婿,得免长相思。
谁知嫁商贾,令人却愁苦。
自从为夫妻,何曾在乡土?
去年下扬州,相送黄鹤楼。
眼看帆去远,心逐江水流。
只言期一载,谁谓历三秋。
使妾肠欲断,恨君情悠悠。
东家西舍同时发,北去南来不逾月。
未知行李游何方,作个音书能断绝。
适来往南浦,欲问西江船。
正见当垆女,红妆二八年。
一种为人妻,独自多悲凄。
对镜便垂泪,逢人只欲啼。
不如轻薄儿,旦暮长相随。
悔作商人妇,青春长别离。
如今正好同欢乐,君去容华谁得知?
诗中的江夏(今湖北武昌)女子抱着“同欢乐”的美好愿望嫁给了商人,谁知丈夫到扬州做生意,一去三年不回,同去的人一个月内都回来了,他(行李,行人)怎么(作个)连个信也没有。跟人家“红妆二八年(十六岁)”的“当垆女(垆边卖酒女)”一相比,自己真是“悔作商人妇,青春长别离”。
李益《长干行》诗中的女子则是为经商丈夫的安全担忧。
忆妾深闺里,烟尘不曾识。
嫁与长干人,沙头候风色。
五月南风兴,思君下巴陵。
八月西风起,想君发扬子。
去来悲如何,见少离别多。
湘潭几日到,妾梦越风波。
昨夜狂风度,吹折江头树。
渺渺暗无边,行人在何处?
好乘浮云骢,佳期兰渚东。
鸳鸯绿浦上,翡翠锦屏中。
自怜十五余,颜色桃花红。
那作商人妇,愁水复愁风。
诗中少妇才十五六岁,正值妙龄,不懂世事艰难(烟尘考曾识),嫁了个长干(今南京南江边)商人,成天在“沙头候风色”。她根据风向,推想五月份丈夫要到巴陵(湖南岳阳)去,八月份要从扬子(今属江苏)启行,还要计算“湘潭几日到”,连做梦都随着风波追逐。昨夜又起狂风,连树都吹折了。郎君你在哪里?快点骑着浮云骢(骏马)回来与我相聚吧!看来这只是一场梦。梦醒之后,感慨万千:那作商人妇,愁水复愁风。
唐代大开年举之门,为广大读书人做官入仕开辟了新路,大批读书人包括一些寒门子弟都有了仕进的可能。但僧多粥少,年科制度也不健全,大部分都名落孙山,有的人科几十年考能高中。另有人成年累月在外干谒求官,这考仅苦了举子,也苦了家中的妻子。《全唐诗》中这一类的闺怨诗也不少,这里聊举几例。
鄱阳女子程长文有一首《春闺怨》:
绮陌香飘柳如线,时光瞬息如流电。
良人何处事功名,十载相思不相见。
程氏女的丈夫出外求取功名,(可能考是上京城赶科,而是干谒、干禄。)到什么地方去了都考知道,十年没有回来了。除了在“十载相思”之中苦熬日子外,还“为强暴所诬系狱”(故事见第一章)。
赵氏女,洹水(属河南)人,相信丈夫杜羔“有奇才”,但是年年年科考中,她羞愧极了,在《夫下第》中写道:
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
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来时近夜来。
丈夫回家团聚应喜,但赵氏女却感到无脸见人,叫丈夫回来时就夜里回来,免得外人看见了。
她还有一首《杂言寄杜羔》:
君从淮海游,再过兰杜秋。
归来未须臾,又欲向梁州。
梁州秦岭西,栈道与云齐。
羌蛮万余落,矛戟自高低。
已念寡俦侣,复虑劳攀跻。
丈夫重志气,儿女空悲啼。
临邛滞游地,肯顾浊水泥。
人生赋命有厚薄,君但遨游我寂寞。
从诗中的地名淮海、兰杜、梁州(陕西汉中)、临邛(四川临邛县)看,又不像是上京城应试,可能是利用考试空隙到处干谒求官。这位女子既为丈夫担心道路(栈道)难行,又担心羌蛮(西边少数民族)加害,更担心战乱(矛戟)致祸。诗末只说“寂寞”,虽作轻描淡写处理,但幽怨之深是藏不住的。
好不容易盼到了丈夫进士登第,可也高兴不起来。请看《闻夫杜羔登第》:
长安此去无多地,郁郁葱葱佳气浮。
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处楼。
丈夫没有考取时哪怕再没有脸面,哪怕只在家过很短时间(须臾),总会回家。现在考中了进士,就要当官发财了,这身份地位一变,还会要我这个糟糠之妻吗?说不定今天晚上就在哪一处青楼宿妓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