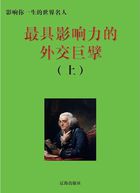一
我故乡的农民,没有宗教信仰,只有神灵崇拜。宗教面对灵魂归宿问题,追求人生终极意义。农民对此,并不感兴趣。他们只关注现在,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小民百姓,活着太难,碰上这事那事,人没办法,不求神求谁?与其说是迷信,不如说是无奈。人创造了神,神安慰了人。亏得我们的祖宗弄出了那么多神,若不然,我的父老乡亲的庸常生活就少了丝丝亮色。神灵固然虚妄,得到的心理熨帖却是实在的。
传统农民的悲剧也正在这里。
想起了邻家三婶。她十六岁嫁给三叔。我记得,结婚前夜,我给新娘新郎压过喜床。还记得,花轿抬进家,盖头一揭,她羞涩地头一低,全村老少都看迷了,那眉眼儿,那脸蛋儿,赛似洋画上的美人儿,都说,方圆一百里,挑不来这人样儿。三叔在南阳念中学,每个月只回来一次。小两口恩恩爱爱,亲得泥儿一般。三叔不在家,三婶好孤单。我每去她家,都见她给三叔做新鞋,针针线线想必都牵引着思念。我每去她家,都给我拿吃物儿,有次给我一把糖豆儿,我一吃,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甜的东西。她家富足,乡下有田地,镇上有生意。全村女人,只她有一件蓝阴丹士林布衫,谁家媳妇走亲戚,都去借。那年初冬,一个黄叶飘落的日子,三叔在家住一夜又回校。临走说,过年放假回来。走后不多天,三婶就生了,生个小子。孩子满月,已是春节,三叔并没有回来。春节过完,三叔仍没有回来。这时三婶才听说,三叔回校不久,共产党的军队攻下了南阳,国民党军队溃逃时,带走一批学生。从此,三叔再无音讯。三婶想他,盼他回来;想中盼中,愁苦难排。一场大雪后,满地泥泞,三婶跑八十里路,去卧龙岗诸葛庙,烧香,磕头,给道人一块银圆,而后抽签。道人一番念念有词,三婶听不懂。三婶只记住一个意思,就是:等着吧,能回来。诸葛亮原是人,足智多谋,死后成了神,灵验得很,三婶深信不疑。从此,三婶把鸭蛋形的玻璃镜藏进箱底,再不梳妆打扮,开始了等待。心中有了底,等待就有了意义。等待中,三婶仍给三叔做鞋,新鞋挂在床头,积了两嘟噜,穿鞋的人还没回来。等待中,日出日落,月缺月圆,燕回燕去,时光好似过得很慢,又似过得很快。等待中,世事沧桑,社会变动,作为一个“地主婆”,她忍受了一切屈辱,一切肉体和心灵的磨难。等待中,她以一个女人的纤弱之躯,支撑起一个破碎的家,为公婆养老送终,烧纸添坟,把儿子养大成人,娶妻生子。在不见尽头的漫长等待中,她由红颜少妇变作白发老妪,驼了的脊背像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袱。终于,在等待中死去。死前,交代儿子:“你爹回来了,去坟上烧张纸,给我说说。你爹属羊,今年七十二啦……”儿子没见过爹,爹也没见过儿子。儿子早就听说,爹当年跟军队逃到湖南,得了病,病死在一座庙里,兵荒马乱中,尸骨没人收拾。这情况,他不敢给妈说;村人也知道,都不忍说透。三婶啊,临死还蒙在鼓里,临死心中仍不空虚。
道人的话,本无根据。无根据的一句假话,拯救了一个女人,给了她长久不灭的希望,生活下去的勇气,使她送别了三叔后,又顽强地走完五十年风雨人生路。五十年都在永也难圆的梦中。梦中的她,活出了自己的价值。当初,假若道人告诉她,三叔不会回来,或者已经死去,她后来的日子将十倍凄惨,后来的心境将十倍凄凉。或许,早就不在人世了。
又想起邻居五叔。他不满一岁,父亲暴病而死,二十岁时,母亲瘫痪在床。瞎子算卦,说他命硬,先克父母,后冲儿女。把不幸归于命,似只能归于命,其他解释,似都讲不出道理。三叔深感自己有罪,而且十分惶恐,已经对不起父母,不能再对不起儿女。怎么办?人莫能助,只能靠神。于是,他就去武当山烧香。背上干粮,带上香烛,总是腊月二十三启程,为表虔诚,赤脚上路,顶风雪,踩冰凌,步行五百里,五百里艰难赎罪路。除夕赶到山下,临上登山道,半尺长的银针横插两腮,一步一滴血,十步一叩头,头触石阶,也碰出血来,点点鲜血滴上金顶,金顶曙色已红。烧满炉香,磕一百头,而后长跪不起,求告真武大帝,赦免自己一出生就带来的罪孽。老道似也感动,拔下银针,用香灰在两腮伤口处一按,说声“祖始爷保佑,回吧”,三叔才下山。下山路上,身心轻松许多,仿佛命中的罪少了几分。到家,人已消瘦得变了形象,精神却比往日好。一连三年,年年朝山,折磨了躯体,安抚了灵魂,受尽千辛万苦,得到心态平衡……三叔现在还活着,已是八十老翁;满堂儿孙,闹闹嚷嚷,晚境好生快乐。两腮的疤痕犹在,当初的负罪感早就没了。
显然,算命先生纯是一派谎言,但是,谁能把那些谎言揭穿?一说是命,已成定数,容不得商量,也不能怀疑。祖祖辈辈都信命,三叔能不信?“人的命,天管定”,“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命里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千百年传下的理念已成共识,三叔敢和天抗争?敢向命挑战?他只能承认,只能服从。他实在愚昧,我却不忍心指责他愚昧,因为他实在无法不愚昧。他对自己实在残酷,我却不忍心指责他残酷,因为除了折磨自己,他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消除心上浓重的阴影。我甚至想到,亏得他相信真武大帝,相信苦苦求神可以免去自己罪愆,三次朝山,损其体肤,伤及血肉,否则,他将一辈子痛苦,一辈子恐惧,一辈子不得安宁。
求神者从来不会意识到,倒是神残害了人。这景况,实实可叹可悯。
二
人造了神,是人的需要。不只心理需要,生活中时时需要。有了三灾八难,都得去求神。
我小时候,乡村敬神风气极盛,家家奉神像,村村有庙宇。人生活在人的关系中,也生活在和各路神仙的关系中。人与人的关系当然复杂,总而言之,不过都为利益而相互依存。人和神的关系似乎较为简单,但也是相互利用。农民眼中的神也和人一样,是自私的,得到利益,才施恩惠,便用对付人的办法对付神,力图以小利换大益。
想起了土地庙。
土地神原为社神,源于先民的土地崇拜,在远古,是非常尊贵的。天帝主宰世界,土地负载万物,社神和天帝相对应,为国家一级大神,由皇帝专祀。《诗经》中就有周天子社祭的记载,那场面是十分壮观的。后来,不知为何,土地神的级别直线下降,降成了神祇中的“基层干部”,以至于村村都有土地庙,每一位土地爷只管自己所辖范围内的事情。土地庙都小,不像别的庙宇,飞檐枓栱,气象轩昂。
我们村的土地庙,在村东一片鳖盖形的高地上。那里,不种庄稼,只长野草,长得最茂盛的是驴尾巴蒿。土地庙高不过八尺,宽不过一庹,青砖砌的台上一间简陋瓦屋,屋里只有方桌面那么大的地方。我常在高地上放牛,牛不吃驴尾巴蒿,只吃席地生长的葛巴草。常看见乌鸦落上土地庙,我一走近,都哇哇叫着飞去;屋顶的瓦垄就被鸦粪糊了一层灰白。牛吃草,不用管,我就常站庙前看土地爷。那是一尊一尺高的塑像,一个白胡子老头儿,身穿土黄色长袍,手握扭了几道弯的龙头拐杖,端端坐着,表情和善。看见他,我总想到东村那个自认为通晓天文地理的堪舆先生。土地爷两侧,排开二十几个土地奶。乡村习俗,谁有了病,主要是小病,比如头痛发热,谁有了事,主要是小事,比如丢了猪羊,就去土地庙,上三炷香许愿(大病大事则要去大庙,求大神;土地爷神通小,无能为力)。如果病好了,猪羊找到了,要还愿。据说,土地爷好色,爱讨小老婆,就买个泥捏的土地奶送进庙里。买个土地奶,只花半升高粱。在人和神的交易中,人并不吃亏。那些土地奶,都不到一拃高,都塑得妩媚标致,且神态各异,有娇滴滴的,憨实实的,苗条条的,病恹恹的,还有眉峰紧蹙、满腹心事的,眼含秋波、顾盼有情的,嘴角翘着、笑容可掬的,二目微闭、羞态难掩的……活脱脱两队美人儿。土地神已经大大地世俗化,比世人还庸俗。正因为他庸俗,才宜于小百姓时时利用。
有时候,我和小伙伴们也钻进土地庙玩。屋顶太低,地方太小,站起碰头,蹲着盛不下,只好屁股顶着墙,弓着腰,半站半蹲着。土地爷和他的太太们便只能屈尊于我们的胯下、股间。正因为土地爷是小神,和人更接近,似也更具人性,就少了很多凛然不可侵犯的神的威严。此时,在孩子们眼中,土地爷一家已不是神,而是大家的玩伴,或者说,是大家的玩具。我们把土地奶一个个拿起,端详她们的眉眼、脸面、身腰,以儿童的审美趣味比较谁更漂亮,常因意见不合争吵。看够了,就把她们排成两队,让土地爷站外面当队长,再把她们排成方阵,让土地爷站中间当元帅。无论怎么摆弄,土地爷和善如故,土地奶美丽如故,都听调遣,都不生气。玩腻了,我们还会说傻话:“土地爷这么多女人,养活得了吗?”“夜里睡觉,床上挤得下吗?几十条腿伸一块儿,知道哪是谁的腿?”“土地奶生娃娃吗?娃娃们在哪儿?长大干啥?也当土地爷?”……也曾碰上大人从庙前过,看见我们的恶作剧,有的,笑笑就走了;有的,故作惊恐状:“哎哟哟,有罪呀,土地爷恼了,你们要害眼哩!”惹恼了土地爷,他只能叫人害眼,并不会得重病,更不会要了性命,可见他老人家并不厉害。
土地爷和他管辖的土里刨食的庄稼人一样,十分低贱,甚至窝囊。土地庙的香火供品,总是清淡寒俭,就像庄稼人的日子一样。土地爷是农民创造的。小百姓正该有一位近在身边的侍候得了的小神。
过年,是敬神的高潮。那些天,到处都有神,石磨上,牛槽上,门墩儿上,捶布石上,井台上,碾盘上,大车上,石磙上,甚至村南那棵一搂粗的大杨树上,都贴了有字的红纸条儿,在前面撮土为炉,插上了香。这种泛神意识,想必源远流长,来自初民的自然崇拜。那些物件,都与农民的凡俗生活息息相关。它们为人服务了一年,如今当神敬一敬,倒也应该。那些物质的东西,被农民赋予了形而上的意义,一时间变得尊贵。细想想,很有人情味,很有知恩必报的良心。过年时,奶奶总告诫我,说话做事要谨慎小心;说错做错,轻则不吉利,重则得罪神。比如,蒸出的白面馍裂了口儿,不能说“馍裂了”,应当说“馍笑了”,当院的捶布石不能再捶布,更不能踩它坐它……村当中的空地上,临时搭了神棚,高粱秆织的箔围三面墙,上面以苇席苫顶,虽简单,却庄严。棚下置神案,挂神像。玉皇大帝和火神画在一张巨幅纸上,工笔线描,色彩斑斓。玉帝居上,戴冕旒,着锦袍,道貌岸然;身旁,有瑞气祥云。火神居下,红脸,红胡子,红衣冠,一副凶相;身旁,有烈火,闪着红光。神像两侧的对联,不是字,是画,画的“八仙”,一边是吕洞宾、韩湘子、何仙姑、蓝采和,另一边是张果老、李铁拐、曹国舅、汉钟离。八位仙人,各有各的妙处,吕洞宾安逸悠闲,韩湘子风流潇洒,何仙姑秀美俏丽,蓝采和背着细腰酒葫芦,醉意未醒,张果老倒骑着粉鼻子粉嘴四只银蹄儿的小毛驴儿,逍遥自在……他们都驾着轻烟浮云,衣袂飘飘,像正凭虚御风赶往西天,去赴王母娘娘的蟠桃会呢。神像是我最早接触的美术作品,被画中的艺术感染,更对神仙不可侵犯的威仪和超自然的能力敬畏,体验了美,也认识了神。农民管玉皇大帝叫老天爷。老天爷是天上地下最大的神,统领一切神祇,震慑一切鬼魅;风雨雷电,旱涝虫雹,都是他的意旨的体现,庄稼的收成,庄稼人的福祸,都与他直接有关。理所当然地,农民对老天爷的崇拜无以复加。农民把火神尊为火神爷。对他,主要是惧怕。他一发怒,一场大火就把家产烧成一堆灰,顷刻间一贫如洗。平时,夜间看见流星在天空划出一道刺目的黄红,人们都惊叫:“啊,火神爷放光啦!”心里都怵怵的,生怕失火。向神表示敬意,主要是烧香。神棚里的香炉斗那么大。香炉两旁的蜡烛棒槌那么粗。再穷的人家也要买成大把的香。初一早晨,为争烧头炉香,好多人通宵不睡。在家里,给灶神和祖宗只各烧三炷;在神棚,却要向玉帝、火神敬献一把高香。烧香时要放炮,在家里只放小炮儿,在神棚前都放大鞭。直到初五,家家每天去神棚烧三次香,几家富户则烧五次。香烟袅袅,鞭炮声声,敬了神,也浓了节日气氛。那些天,我和小伙伴们日夜守候在神棚,看烧香,捂着耳朵听放炮,你争我抢拾炮,大家都高兴。就连大人们,也一群一伙凑在那儿,看热闹,说喜庆的话。即便过罢年就揭不开锅的人,那几天脸上也有笑意,不再露出晦气。曾想,如果不挂神像、烧香、放鞭炮,庄稼人过年将多么单调、枯燥、没有味道。有了那一切,敬奉了神,也愉悦了人,人神都快乐。
人没有见过神,见到的只是神像,或塑像,或画像;却坚信有神在。在神面前,人只能是乞求者。
三
人去求神,泥胎纸像不会说话。神的态度如何,人不得而知。于是,便出现了神婆。神婆充当了沟通人神的角色。
村村都有神婆。我们村的神婆,是个麻脸老奶奶。她质朴,且善良,家中敬一尊铜佛,烧几十年香,铜佛已熏成黑的。她在村中威望高,老少对她都敬重,绝不像《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那么狡诈虚伪,辈分更高,高得村人没法称呼,便都叫她老祖奶。村人都说她是半仙之体。她说她一闭眼就能看见神仙,就能听见神仙说话。有次,我发烧,喝一把谷籽儿,烧仍不退。奶奶就请来老祖奶下神。我瑟瑟地偎奶奶身边看。见老祖奶坐在圈椅上(圈椅是从邻居家借的,我家没像样的坐具),闭目有顷,呼吸急促,而后,打哈欠,流鼻涕,接着,开始似说似唱,声音委婉绵软,好像还押韵合辙。说唱的啥,我听不懂,奶奶恐怕也不懂。好一会儿,才住声儿,又有顷,才睁眼。睁开眼,好似刚才出了很大力,累得直喘气。歇一歇,才告诉奶奶:神说了,我在地里玩,撞上野鬼了;正晌午,去村东十字路口,烧三张表,送走野鬼,就好了。第二天,奶奶照办。第三天,我果然不再发烧。
五十年代,为破除封建迷信,有人编出小戏,揭露神婆骗人。戏文中说,神婆到王老五家下神,看见墙上挂个罐子,以为是蜂蜜,就唱道:“王母娘娘下天堂,想吃你墙上那罐蜂糖。”王老五女人说:“那不是蜂糖,是桐油啊。”神婆又唱:“王母娘娘太慌张,错把桐油当蜂糖。没有蜂糖也算罢,买个猪头我尝尝。”这戏在我们村演出,乡亲们都说是瞎编的,老祖奶就不骗吃骗喝要东西。这也是真的。那次在我家下神,临走奶奶要送她一手巾兜儿鸡蛋,她坚决不收,说要收下,神要降罪。她是个特殊的神婆,好似真的能时时进入虚幻的神界。她满足于这种状态,满足于村人的认可和敬重,不追求物质,只为了精神。她死时,全村老少都戴孝,送殡路上,从村庄到墓地,汇一条白色的长长人流。
神是虚假的。众人都信,就成了真实的。
想起了又一次求神经历。据奶奶说,我周岁时,算命先生“掐八字”,算定七岁有灾。六岁那年,为了消灾,奶奶带我去三十里外的一个村子烧香。那里一家神堂,远近有名。天亮坐上牛车,半路过道河,近中午才到。去烧香的人可多,那家门前,停好几辆牛车,拴好几头背上铺了布垫的驴。堂屋,靠三面墙都是神台,排列塑像二十来尊。我认识的只有两尊,一是关老爷,因为是红脸立眉,手拿一把刀;另一尊是送子奶奶,因为她面前有两个光屁股胖娃娃。烧香的都带了供品,多是十个特大的圆形的白馍,一块半熟的插两根筷子的大肉。求哪位神,就把供品摆哪位面前;其他各位,只上三炷香。每尊神前,都有供品。送子奶奶身边,白馍堆了几十个,大肉码了一排。我看见,两个娃娃的鸡鸡儿,都只剩半截,露出了干硬的黄泥,好生奇怪。后来才知道,求子心切的媳妇烧罢香,总偷偷抠鸡鸡儿上的土,当即吃了,据说吃了能生男孩。我奶奶或许认为关老爷本事大,就把供品送给他,插上香,跪下磕头。也让我磕头,那青砖地硌膝盖,跪着疼,我只磕一下就站起,奶奶一直磕一百个头。求罢神,供品当然不能带走,全留给神,也就是留给开神堂的人了。当时我就想,那家不种庄稼也能顿顿吃白馍,天天吃肉,哪像我家,收了麦才吃几天白馍,大年初一才吃一次肉……我平安长过七岁。奶奶说,亏得去求了关老爷。
在我整个童年,总忘不了那二十多尊神,特别眼馋那丰盛的供品,一想起,就流口水。现在想,那户人家开神堂,也是一种营生,一下子摆布那么多神,更是一个聪明主意。只要是神,都有人拜。前人创造的,后人都有用。
老祖宗还创造了管牲口的神。村西五十里,有座牛王庙。听说牛王爷的个子忒大,脚脖子就有水桶粗。邻家老七爷去过,他的牛长了疽,兽医治不好,去求牛王爷。黄石寨有座马王庙,是财主修建的,穷人养不起马。听说马王爷有三只眼睛,第三只竖着长在额头正中。民谣道:“马王爷,三只眼,驴和骡子他不管。”驴不算大牲口,骡子不是正经东西,所以神不管它们的事。农业生产是人和牲畜共同参与的,自然经济离不开牛马。牛神马神的出现,也是历史的必然。
农村有多种庙宇,惟独没有财神庙,也没人敬财神。难道庄稼人不想发财?怕主要是小块土地上讨生活,根本就不可能发财。农民追求的,只是有吃有穿,日子安顺。有一次去古镇上瞧外婆,曾跟外婆到一户富商家借钱,见客厅挂有财神像。那财神,好富态,戴乌纱,穿官服,似乎意味着做官与发财颇有关联。近来看闲书,才知道财神分文武,文财神是比干(一说范蠡),武财神是赵公明。在中原,民间只敬文财神,似不敬赵公元帅。
四
我看到过神像是怎么做成的。
我们村西南隅,一片榛树刺林,围一个独门院落。那户人家,不种田地,祖辈相传,制神像为业,村人称为“画匠家”。据说,当时还在世的老画匠的爷爷技艺最精,在中国还有皇帝时候,曾被官府召到南阳,塑过武乡侯孔明像,因为塑得好,得到很多赏银。画匠家常常大门紧闭,村人无事,不去串门儿。
有一次,邻村的社火头儿带人去请神,我和小伙伴们随着看热闹的大人,在鼓乐声和鞭炮声中,拥进画匠家。我在人群中钻进钻出,从院里看到屋里。院当中,放几口均州大缸,盛了细腻的黄泥。靠院墙的席棚下,摆满各种各样的神和没有做成的神。有的已经涂金描彩,衣冠整齐,有的还是一身黄泥,有的刚刚捏出凸起的鼻子和衣服的褶皱,有的还是木板上的一团黄泥,有的只在木板上钉了木棍儿,缠了麻绳,绑了麦秸。这些,等于展示了制神的全过程。窗台上,我一眼看出有一排土地奶的成品和半成品;土地庙里那些她们的同类都来自这里。画匠家屋内,也到处是塑像。木板搭架子,架上架下罗列各路神仙。莲花盆里的观世音菩萨放在门后,面朝墙坐着,另一扇门后的旮旯里,坐着白胡子老君爷。床底下的杂物之间,也塞了大肚子弥勒佛、额头突出的老寿星。墙壁上,挂满神的画像,都是哪方面的神灵,我不知道,只觉着都是好看的画儿。屋正中的长案上,放十几个盛颜色的碗碟,十几杆大大小小的毛笔。一套神像还没画完,一幅,刚用香头儿起了稿儿,一幅,刚用墨笔勾了线,一幅,才涂上两种浅色……老画匠黧面白发,脑后拖一条大清朝留下的辫子,正用柔柔的笔道给一个什么神描眉,很专心,好像不知道满院满屋都是人。临村拉来几袋粮食,请五尊神,一路吹吹打打,回了。
在画匠家,神像只是商品;请回去,摆在神位上,才是神。俗话说:“画匠不给神磕头——知道你是哪个坑里的泥。”其实,人们都知道神像是怎么制成的,却都真心信奉。
五十年代开始,上级不准敬神,庙里的神像都拉倒砸了。画匠家分了土地,成了农民。老画匠死了,儿子继承了父亲的技艺,却无处施展。合作化后,大呼隆干活儿,歇息时无聊,小画匠从水沟里挖一团泥,比着乡亲捏泥人儿,捏谁像谁,神情活现。“文革”中,在上级办的展览馆里,他塑过领袖像,领袖作挥手远望状,形象高大。有乡亲去参观过,回来说,他塑的领袖像越看越像寺里的佛爷。
又可以敬神时候,当年的小画匠也成了老画匠。他不断被请到大小寺庙,重塑各种神像。最后,花一年工夫,为三尖山丹霞寺塑成了三世佛。开光后,他坐佛前的门槛上看三尊佛像,看了三天,突然跪下叩头。而后,竟把工钱捐给寺里,出家了。亲手制神的人,最后也皈依了神……
他儿子连画笔也没摸过,连个小狗也不会捏。祖传的造神技艺,终于断了传人。乡亲们都惋惜不已。
五
想起了灶神。
灶神来源很早,为先民五祀之一。《礼记》中说:“炎帝神农,以火德王天下,死托祀于灶神。”人要吃饭,吃饭得有锅灶,锅灶须用火烧,让炎帝神农氏做灶神是有道理的。民以食为天,吃饭是大事,灶神在家中的作用就很重要。所以,《论语》中说:“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与其巴结天帝,不如巴结灶神。灶王爷是老天爷派到各家的特命全权大使。
家家敬灶神。在中原,灶神不是敬在锅灶前,而是和祖宗三代的牌位并列,庄严地供奉在堂屋正中。灶神像两侧的对联,常常是“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上边的横批,永远是“一家之主”。家庭的事,人做不了主,只靠神做主。灶神像是从年集上请回的木版印刷品(虽也花钱,却不能说买,只能说请),薄薄一张纸,画面大红大绿,色彩鲜艳。灶神是带着太太下界履任的。农民管他们叫灶爷爷灶奶奶。那老两口儿,都胖乎乎的,笑眯眯的,慈祥绵善,人味十足,不像别的神,人只能敬拜,而不敢亲近。我无论什么时候看灶爷爷灶奶奶,老两口儿都喜洋洋地看我,像马上就要说话,给我讲个故事,给我念首儿歌。腊月二十三,按惯例,灶爷爷回天宫汇报工作,说好说坏,至关重要。所以,年年都祭灶,祭灶就是为灶爷爷饯行。这是一年中最隆重的一次家庭祀神仪式。我奶奶最重视祭灶。灶神像前,包了红枣的大个儿白馍摆两个品字形,上边再一反一正摞两个。来自猪腰窝的那块最肥的肉横放中间,上插两双筷子(大概是考虑到灶爷爷灶奶奶各用一双)。还摆了家制的黄酒,买来的灶糖、柿饼。灶糖、柿饼只各有四块,我真怕他们二位贪嘴,全部吃掉,我就不能吃了。祭灶开始,奶奶点着红蜡,顷刻间满屋明亮。点着香,顷刻间青烟飘过屋梁。奶奶跪下,让我抱一只红公鸡也跪下。奶奶说,公鸡是灶爷爷上天骑的马。奶奶向灶爷爷絮絮叨叨好久,我总暗想,一只公鸡能驮动灶爷爷吗?上天的路到底有多远?祭灶毕,把公鸡杀掉,意思是当即它就变成了红马。杀了鸡,我望着高不可攀的天空傻想:这会儿,我家的灶爷爷,邻家的灶爷爷,千家万户的灶爷爷,都正骑着红马赶往天庭呢。还傻想,到了玉皇爷那儿,那么多马拴哪儿呢?玉皇爷的屋子再大,总也站不下一万个灶爷爷吧?一万个灶爷爷都向玉皇爷说话,听谁的呢?报告那么多事儿,能记住吗?想问奶奶,不敢问……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再也请不来灶神像。原来敬灶神的地方,家家都挂上了毛泽东画像。曾记得,老族长八太爷第一次看见领袖像,端详多时,点头道:“哦,毛主席不是凡人,下巴上的瘊儿,长的是地方。坐天下,应该。”从那时起,毛主席成了一家之主。
毛泽东画像挂了二十多年,伟大领袖去世,英明领袖接班,上级发下了华国锋像。堂屋正中一挂,心里又有了主儿。
乡亲们说:“噫,华主席也是福相。江山传给他,应该。”谁知,挂了几年,上级又叫取下。取下后,再也没有谁的像往上挂。后来听说,朝里邓小平当家。邓大人叫分田到户,叫大家吃饱肚子,真该挂他的像,可是,买不来。于是乎,堂屋后墙正中敬了几千年神的地方,挂了几十年领袖像的地方,便空了,空成一个沉重的遗憾。有史以来第一次,没了一家之主。墙上空着,心里也就空落落的。
农民需要一家之主,呼唤一家之主。
八十年代后期,我常常下乡采访。在一个户户盖楼的小村村头,和一位宰牛致富的老农闲谈时,老人说了如下一番话:
“……上头知道不知道?咱老农民堂屋里没啥挂哟。进屋看见白墙,别扭,心里不踏实。我房子盖好,我娃买回来一张画,画的下山虎。墙上一贴,我说不中。进门看见一只虎,不吉利。下山虎都是饿虎,更恶。我娃又去买一张画,可大,墙都占满了,画上两边有山,当中有大水,水从高处往下栽,怕人。我说还不中,恁大的水不把咱的家业都冲走?我娃还算听话,问我墙上挂啥好,我也说不了。后来,他买了一张白纸,请人画一对喜鹊,喜鹊落在梅花树上。我说,算了,就这吧……村北头张记家,正当门贴一张女人画,露着屁股,咧着嘴笑,浪里吧唧,不像话。那是敬神敬领袖的地方。把那东西放那儿,不是敬个狐狸精?……我想啊,总得敬个正经的神。我杀多年牛。早些年穷嘛,没别的生财门路。如今不杀了。养奶羊,卖羊奶,弄钱不多,不坏良心。牛是生灵,杀了有罪;赚那钱,心里不安哪。想请个神,烧烧香,免罪。你说说,敬个啥神好?你不信?我信,信神的人多啦。葫芦湾胡大炮,是个工头儿,去城里盖十年大楼,挣几十万,家里敬着老佛爷、鲁班,还有钟馗。人哪,靠啥都不中,还得靠神……”
不知道那位老农后来敬了什么神。我相信他一定会请一尊神,敬在堂屋正中的神台上,每日一炉香。有了神,才有主,心才安。
二十世纪即将结尾时候,中国农民竟然仍需要神。在神面前,人只能下跪。树立起神的尊严,人就没了尊严。只有神消失了权威,人才能发现自己。待一切神灵都成了真正的虚假,农民才可能成为真正的人。那一天,还远着呢。
2000年5月30日于南阳豆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