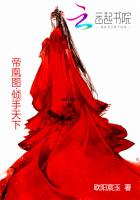清明节前,回一趟老家,一来扫墓,二来看望族人乡邻,母亲在世时,他们多有照顾。就买了糕点、糖果、火腿肠、油炸馓子之类的吃食,大包小包的。人老了,不便搭长途公交车,公交车折回的地方,距我们那个松松散散的大村庄还有十里路程。不得不向一位做官的朋友借部小车,快到报废期的“桑塔纳”。司机也是借朋友的,那小伙子在城市长大,几乎没到过农村,他说,正想到乡下玩玩,乐于为我服务。为了招待司机,还带了肉、菜、酒、矿泉水、果汁饮料。塑料袋、编织袋塞满了后备箱。
国道、省道、县道、乡道,最后,小车颠颠簸簸开上通往村庄的土路。土路上干了的泥碴子尖锐似狼牙。司机心疼车,怕咬破轮胎,忽左忽右谨慎行驶,好像路上布满地雷。走着感叹着这里真穷,连沙土路也修不起。我们村离河几十里,买回一车沙得几十块钱,乡亲们盖房买沙都犯愁,怎舍得把钱铺路上。
路两边的田地,长短宽窄不同,横竖不成规矩。大半种小麦,刚刚半尺深,小半是白地,准备种棉花。也有油菜花开,星星点点不成片。家家户户种庄稼,家家户户地都少,田野就像百衲衣,绝无我在电视里看到的一望无际的没有阡陌切割的壮阔景象。
进入我们村的地界,我就下车,给迎面走来和在路边田里劳作的乡亲打招呼,敬烟。打招呼必先叫“爷”叫“叔”,严格遵循辈分,即便他们年龄比我小,也理当作为爷和叔尊重,即便他们干活的位置离路较远,也要大步走去递上烟,点着火,还要小心不能踩了庄稼。当年骑自行车回老家也是这样。如果不下车径直进村,乡亲们会捣断脊梁的。即便在外边混得再阔,也不可在家门口卖大。这是古来的传统。我们村至今还没有在外边混阔的人。当年,八爷的小儿子在街上的食品站卖肉,回村时自行车一直骑到家门口,见谁也不搭理。乡亲们说他不如狗,狗见熟人还摇摇尾巴哩。我们全村同姓,我家属长门,辈分低,某个小媳妇怀抱的婴儿或许就是爷辈的人。我见乡亲就更有必要谦恭。
我家房屋还在,锅灶还在,早已没人住,就来到近族侄儿家。立即惊动东邻西舍,大多是老人孩子,迎接我,也看车。小轿车很少进过我们村,十年也难见一次。一个爷问我:“娃,你当啥官了,回来坐着小卧车儿?”真不好回答他。吃公家饭几十年,直到范进中举的年龄,我才混个副科级,且从未行使过那个副科级的权力(也无权力可行使)。在我所属的系统,即便正科级也算不上官,也没车坐。如果说车是借的,怕他也难理解。牛驴可以借来使使,卧车乃官员身份的象征,谁肯出借,借车岂不等于借县太爷的轿?又一个爷说:“娃,你可是见老了,也瘦了。公家的事嘛,别操那么多心了。”他不知道,我多年没办过什么公事,写文章似乎只算自己的事。其实他更老,满脸皱纹沟壑纵横,门牙只剩两颗,却不对应,虽然他比我小三岁。当年曾一块儿放驴(驴卸了磨才拉地里放),老鸹回窝时候他的驴还没吃饱,急着回家,驴不走,硬拉拉不动,气得他直哭。如今,他孙子已经虚岁二十,正筹钱盖房娶孙媳。我儿子还在大学念书,何时结婚我当不了家。孙子嘛,更没影儿呢。
老少爷儿们坐侄儿家堂屋拉家常。椅子、凳子、木墩儿、蒲团儿不够坐,有人坐门槛上,有人脱了鞋子垫屁股下坐地上。我一遍遍让烟,满屋云雾翻滚。闲谈中,我听到好多可记可述的事。
从春节前到现在,村里娶了四个媳妇。娶个媳妇至少需要三万元,建房、彩礼、嫁妆及结婚前后的开销,大约各需一万。嫁妆是婆家买齐送娘家,送亲那天再拉来。年轻人大都外出打工,多数在建筑工地干粗活,下死力,挣小钱。结了婚的,挣钱为还娶媳妇欠的债。没结婚的,挣钱为了娶媳妇。挣钱花钱都为娶媳妇,娶来媳妇还受穷。只二叔结婚省钱,没盖房,没置办嫁妆,除了床上铺的高粱秆织的箔和麦秆织的稿荐换了新的,没添任何家具、电器,女方只要七千元彩礼和两身新衣裳。二叔五十岁出头,头发已花白,腰也弯了。那女的刚十九岁,傻,识不了十个数,会吃饭,不会干活,连做饭时向灶膛填柴烧火也不会。女方说,那七千元是饭钱,养活一二十年,粮食也吃几千斤哩。二叔说,只要是个女人,能生个下辈人就好。
开春以来,村里死了三个老人。一个是高血压,见羊进地啃麦苗,跑去撵,捡一块土坷垃砸羊,攒足劲,猛一扔,还没扔出,一头栽下,没气了。一个因为感冒,用传统的老办法喝一把谷籽儿发汗,没治好,引起肺炎,咳嗽,又用偏方“蛤蟆皮”(一种野草)炒鸡蛋治,仍不见效,接着高烧,这才去找医生,吃几片“安乃近”,出一身大汗,烧退了,人也慢慢停止呼吸。一个是家里突然瘟死几只鸡,舍不得扔,拔毛开肚炒了吃,吃多了,不消化,窝肚里,很难受,就吃泻药泻,拉稀两天,虚脱而死。这些都不是正常的寿终正寝,怕都算非正常死亡。
一个叔养头母猪,一年下两窝,每窝都十来个崽儿。上月,扑扑腾腾一下子产十三个,个个胖得赛似泥儿捏的。都说他运气好,一窝猪娃能卖几百块。他说:“咋好?一万猪娃也不如一个人娃。没有人,钱再多也没用,吃饭没味儿,干活没劲儿,睡到半夜越想心里越凉。将来两眼一闭,挣一屋子元宝也都是人家的。”却原来,他只有两个妞,媳妇已经结扎。所谓没有人就是没有儿子。没儿子,就没希望,一切都没了意义。
一个爷问:“娃,你一个月领多少钱?”我据实回答:“扣这扣那,净领差十几块不到一千七百块。”他听了吓一跳:“哟,比得上我卖五亩地麦子的钱。麦子从种到收,得九个月,投工投钱、累死累活还不算。”又问:“听说报上登文章也给钱?一篇几个钱?”我说:“有时三五十块,有时百八十块。”他感叹道:“哦,你一篇文章比我两车红薯卖钱还多呀。”他最后归结一句话:“干啥都比种庄稼强啊。”我无言以对。
一个爷说,这些年乡下贼多,不知道上级知道不。近一个月全村丢四头牛。大多是夜里墙上挖个窟窿偷的,窟窿的大小正好能牵出牛。弄得都不敢睡觉,点灯熬油看牛。老四爷五更里困极打个盹儿,猛一惊醒牛没了,看见后墙有个洞,亮亮的。忙出去找,就在他家堂屋房后找到一个牛头,一堆骨架,还有一摊鲜血。当场宰杀,连杂碎也不留下。东庄一家,老头睡牛屋看牛,半夜里一直头,见墙上斗大个窟窿,贼正揭砖,就说:“伙计,别扒了。你不知道我家多可怜,老婆子瘫床上五年了,为治病钱花干了,连粮食都卖了。两个娃都快三十岁了,没人说媳妇。穷啊,就这牛算是家业。牛也瘦啊,剥不下多少肉。人还缺东西吃哩,能给它喂料?”贼听后竟然感动,说:“哦,你比我还穷,算了。这窟窿不大,明儿你找个泥水匠补补吧。”老头说:“你是好心人,进屋吸袋烟再走吧。”
一个叔说:“那天夜里,我坐电视机前搓麻绳——我那牛有个贱毛病,好嚼牛绳,不几天就嚼坏一根,得换,买皮绳太贵——看见你演电视哩。”是有那回事,春节前参加一个会,因有领导人在场,电视就报道了,我的影像可能在荧屏上显了一下。他那个“演”字用得独到。乡民以为,上电视的人都是在表演。
一个叔问:“是不是当官的都贪,不塞钱办不成事?”我说:“也有不贪的吧。”他说:“我亲家,糊涂桥王庄的。那村的干部是一窝狼,恶极。村支书的爹死了,家家都送孝礼,最少也得二十元。我亲家性子别,硬不送,村支书的爹还得叫我亲家叔哩。这就把支书得罪了。计划生育别人生三胎不罚,亲家小儿媳妇生二胎罚三千块。还说,往后,每年都罚,一直罚到十六岁。不公,亲家找支书说理。亲家说话也难听,一说就戗,支书的两个娃把亲家鼻子打塌,一脸血,肩膀上打掉一块肉。打倒抬出院子,扔大路上,大门一关,没事了。告到哪儿都不管,一级推一级。上边那些当官的,支书早喂熟了,买通了。老亲家冤呐。你给我介绍一个黑脸老包,叫亲家去找他。”我一时却没话说了,我不知道谁贪谁不贪……
我们在屋里说话,门前一群娃娃妞妞都脱下鞋子,鞋子堆一起,光着脚在灰土地上玩“踢老鸹窝”,都沾了一身尘土。那也是我小时候常玩的游戏。一个坐一边哄弟弟的小妞拉着弟弟的小手念儿歌:“织布织布哐当,一天织了三丈。夜里缝缝,明早穿上……”那也是我小时候常念的儿歌。半个多世纪过去,那一切竟然都没变。
晌午,侄儿媳妇烙油馍,熬小米稀饭,炒八盘菜(盘子是借的,乡下人家大多没有盘子,喝饭吃菜都用碗,喝茶水也用碗,只有来了贵客,比如说亲的媒人、回门的姑爷,才借盘子或租盘子),大肉片子一指厚,比扑克牌还大,牛肉切的不成片,像一盘柴草棍儿,火腿肠截成寸把长一段一段,浇上好多香油。农家妇女会炒南瓜,炒萝卜丝,稍稍讲究一点就不知道如何操作。我请来近族的两位堂叔,两个堂兄弟,让他们陪客。司机是惟一的客人,堂兄硬拉他坐首座,那位年过八十最懂礼法谁家待客都请他到场招呼的堂叔(那角色俗称“大照客”)作主陪。没有酒杯,我带回的纸杯盛酒。堂叔先向司机敬酒,咕咚咚倒半杯,双手捧起,肃立,躬身,强让司机喝下,一副你不得不喝、你不喝就对不起我一腔真诚的样子。司机说,开车不能喝酒。堂叔说:“当年我赶大车往南阳府送军饷,腰里挂个酒葫芦,装二斤烧酒,临走先喝半斤,嘿,人有精神马撒欢,甩一路响鞭,牲口飞一样,蹄子嗒嗒嗒嗒,车轱辘格当当当,灰土地上扬一溜烟。八十里路,日头平西就到了。酒是粮食精,不喝酒,人哪有劲呐。”看司机吃菜少,以为他客气,堂叔端起盘子,筷子一扫,把将近一半大肉拨进司机饭碗里。看司机吃馍少,又抓起几片油馍放他饭碗里。这都是我家乡传统的陪客路数,司机很不习惯,可面对主人真心实意的热情,只好勉强吃下。第二瓶酒喝到仅剩瓶底,陪客的都醉了,说话就更随便了。一位叔说:“电视里说国家取消农业税,这可是天大的功德。往年,庄稼人啥都敢抗,就是不敢抗皇粮,抗粮是杀头之罪。光不交税,老百姓还过不好。朝里人知道不知道,下边的干部坏呀,只会吃喝敛钱,欺邻害户,指望他办事,除非是他亲爹——东庄余二娃,他爹托他买五只洋山羊,一只硬赚他爹三十块,亲爹也敢坑。电视里说的那些好干部咱这儿咋没出一个?”一个堂哥说:“听说城里,老鳖、泥鳅、黄鳝也上桌。吃那东西晦气,咋能待客?那年四狗待他老丈人,没钱买肉,去泥沟里摸十几条泥鳅炒一盘。老丈人气呀,喝几盅酒,醉劲儿上来,呼隆一声把饭桌掀个腿朝天。听说城里,猪肋巴骨比猪肉还贵,鸡爪子比鸡大腿还贵?羊蛋(羊的睾丸)、牛鞭子都是好菜?城里人不嫌那东西臊?听说城里一桌菜得五六百元,全是肉也不值那么多钱,买一头大猪也不过四五百元呐。”……司机听着直笑,笑出了眼泪,笑得几乎岔了气。乡下人怎会知道,城市里富人自掏腰包的和官员公款吃喝的筵席,每桌何止五六百元,上万元的也有。菜肴的精美,场面的奢华,老农民不仅没见过,挖空心思想也想不出来啊。如果让他们去见识一下那些珍馐美味、名酒名烟,和温柔甜蜜的“三陪”服务,不知道会有什么话说。
饭后,我要回城。二爷送我一兜儿用塑料纸包着的芝麻,说:“去年雨多,芝麻都淹死了,连种子也赔了。这是前年的,生虫了,簸簸拣拣还能吃,炕干饼放一把,可香。”四爷背来半化肥袋红薯,说:“窖里只剩这几个,再吃就得等到秋后了。”三叔掂半编织袋红薯干,说:“这东西二十年前顿顿吃,都吃得害胃病,吐酸水;如今,成稀罕物儿了。你带回去换换胃口。”五婶提一篮野荠菜,说:“刚从地里剜的。拿回去包饺子,可鲜。”
临离开我才发现,好多家的门前,桃花开了,满树红妍,春意在枝头热闹,梨花开了,粉瓣儿结成疙瘩连成串,闪烁雪白的亮光。却都是一棵两棵,不成林,不成片。乡亲们种果树,只为自己吃果子,好似就没想到过多种一些卖钱。
车出村,看见二嫂在路上走,担着水桶,扛着铁铲,走路不利索,水桶时时蹭了地,叮叮当当响。她心眼少,干活可有劲,比得上男人。我忙下车打招呼。她放下担子,说去地里栽辣椒苗,是那种又小又尖的辣椒,可辣,舌头舔一下能蜇出眼泪;秋后有人收,可值钱,就是种着费事。她轻轻摸摸车门,眼巴巴看着我问:“这车坐上晕不晕?俺没坐过汽车,只坐过牛车。”我知道,她连拉货的卡车也没坐过,只在嫁来那天坐过一次牛车。我问她,地在哪儿,她仰起下巴朝前一指:“过前头那棵歪脖子柳树就到了。”我和司机商量,能不能拉上她捎到地里。司机一笑:“上来吧。”于是,把水桶、扁担、铁铲放进后备箱,让她上车。因为紧张,腾一声碰了头。问她疼不疼,她摸一下额角说:“不疼,痒也不痒。”坐下又说:“俺身上都是灰,把您的车坐脏了。”坐定,两眼圆睁睁盯着窗外。很快,柳树过去了,停车。她说:“哟,眼还没眨哩,可跑到了。”下车时,弯腰勾头,像从洞中钻出。我把她的农具一一拿出,她一直站路边,眯眼望着远去的车,脸上凝固呆板的笑。
穿过集镇的牲口市(买卖牲口的人和牲口已散,留满地牛粪驴粪)。上了公路。司机打个饱嗝儿,说:“你老家人陪客怎么是那个陪法,人家不想吃硬强逼人家吃,快把我撑坏了。”我说:“那是乡下陪客的规矩。往年穷,吃食少,生怕客人爱面子,不敢吃,吃不饱,就用那种办法,把菜倒你碗里,馍擩你碗里,不吃也得吃。我老家有个说法:走一次亲戚,三顿不饿。那年月,想想心酸呐。”
2005年3月9日于南阳豆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