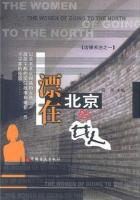这六首诗也是去年十月间译成的,曾寄北京的朋友孙铭传、饶孟侃、杨世恩诸位看过,前两个月又抄了一份寄给美国的闻一多,郑振铎先生也看过,最近又抄了一份寄给周作人先生,确凿有据,可以证明。
近人有一种习气,就是,一个有名的人所作的文章字字都是圣经,一个无名的人所作的文章字字都是恶札;这是一班浅人的必有的倾向,要勉强他们,也是不能的;但是这么大的中国,难道尽为这一班本性难移的劣者所充斥吗?难道竟没有三数个或一个眼光如炬的批评家来发覆扬微,推倒“名”的旗帜而竖起“真”的赤帜吗?我自己不知究竟有批评的天赋没有,然而我发一个愿心在这里,——并望朋友们常常提撕我——就是,以大公的态度来遍阅一切的新文学产物,不以“名”为判断的标准,也不射有意或无意的暗箭。
我个人的倾向原是在创作与介绍两方面的;但是如今我自身感到了一种兴奋,我的精力是不自己的要分一部分到这方面了。
让我将我这一方面的努力的第一成绩公之天下。便是,上学期考试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的“文学概论”,有李君伯昌作有《农村晚景》一诗:
稻儿打完了,枯草晒在溪边;黄昏里——两个孩子赶一群白鹅,从水田中叽叽的叫进茅舍去了。
这首诗是新诗写景诗中一个极好的例子,擅于写景的康白情先生所作的同性质的一首诗比起它来决赶不上它的自然。但李君有什么资格?一个一年级的大学生。又有方君卓有这么一段批评:
国内创作家很多,好的创作却极少。鲁迅的下层阶级描写比较是好的;郁达夫的性的苦闷的呼声确是人生问题之一;冰心比庐隐清丽,庐隐比冰心切要,然而都是很淡泊的描写,没有鲁迅达夫的深刻动人;落花生叶圣陶很有小说的聪明,却不能捉住人生的根本要点,用力描写,一味支离琐碎,平淡寡味,实在可惜之至。
作得出这一段的人便是一个硬里子的真批评家。但这位真批评家有什么资格?一个一年级的大学生。
唉,资格,资格?天下为了你,不知曲没了多少人了?
听到朋友彭基相说,北大的学生以终身在校中读书,当局不仅不将他们开除——如清华开除了我这个中英文永远是超等上等,没有中等过,一切客观的道德藩篱(如嫖赌烟酒)向来没有犯越过,只因喜欢专读文学书籍常时逃课,以致只差半年即可游美的时候被学校开除掉了一般——并且极力的奖励他们;即如彭基相,余文伟两位我的朋友,又如朱谦之先生,大学教员已经当过了许多处的,而资格只是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一年级的学生。
资格?我向你正式的挑战,我的战具不用许多,我只用近来这几天作的一首诗:
葬我于荷花池水下,让滑泥作我的殓衣,在绿荷叶的灵灯上,夜萤闪它的青辉;葬我于马樱花底,永作着芬芳的梦;葬我于泰山之巅,长聆听挽歌的天风;不然,便焚我为轻尘,洒入初涨的春水,沐着暖阳,赏着银月,同流往不可知的去处。
资格?不公平?你们不要狞笑?我还未葬哪?我如今才二十二岁哪?我还有四十年来与你们周旋?朋友们哪?一切的叛徒呀?雪莱、Goldsmith呀:请听我的战呼?
“一个开除的学生?”
(载1925年3月11日《京报副刊》八五号)悼杜莱塞戴望舒美联社十二月二十九日电:七十四岁高龄的美名作家杜莱塞,已于本日患心脏病逝世。
这个简单的电文,带着悲怅,哀悼,给与了全世界爱好自由,民主,进步的人。世界上一位最伟大而且是最勇敢的自由的斗士,已经离开了我们,去作永恒的安息了,然而他的思想,他的行动,却永远存留着,作为我们的先导,我们的典范。
杜莱塞于一八七一年生于美国印第安那州之高地,少时从事新闻事业,而从这条邻近的路,他走上了文学的路。他的文学生活是在一九○○年顷开始的。最初出版的两部长篇小说《加里的周围》和《珍尼·葛拉特》使他立刻闻名于文坛,而且确立了他的新现实主义的倾向。
他以后的着作,就是朝着这个方向走过去的,他抓住了现实,而把这现实无情地摊陈在我们前面。《财政家》如此,《巨人》
如此,《天才》也如此,像爱米尔·左拉一样,他完全以旁观者的态度去参加生存的悲剧。天使或是魔鬼,仁善或是刁恶,在他看来都是一样的文献,一样的材料,他冷静地把他们活生生地描画下来,而一点也不参加他自己的一点主观。从这一点上,他是左拉一个大弟子。
他的写实主义不仅仅只是表面的发展,却深深地推到心理上去。他是心理和精神崩溃之研究的专家,而《天才》就是在这一方面的他的杰作。
在《天才》之后,他休息了几年,接着他在一九二五年出版了他的《一个美国的悲剧》。这部书,追踪着雨果和陀斯托也夫斯基,他对于犯罪者作了一个深刻的研究。忠实于他的方法,杜莱塞把书中的主人公格里斐士的犯罪心理从萌芽,长成,发展,像我们拆开一架机器似的,一件件地分析出来。到了这部小说,从艺术方面来说,杜莱塞已达到了它们的顶点了。
然而,杜莱塞真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美国社会的罪恶,腐败,而无动于衷吗?作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对于这一切肮脏,黑暗,他会不起正义的感觉而起来和它们战斗吗?他所崇拜的法国大小说家左拉,不是也终于加入到社会主义的集团,从象牙之塔走到十字街头吗?
是的,杜莱塞是一个有正义感的艺术家,他之所以没有立刻成为一个战士,是为了时机还没有成熟。
这时,一个新的世界吸引了他:社会主义的苏联。在一九二八年,他到苏联去旅行。他看见了。他知道了。他看到了和资本主义的腐败相反的进步,他知道了人类憧憬着的理想是终于可以实现。从苏联回来之后,他出版了他的《杜莱塞看苏联》,而对于苏联表示着他的深切的同情。苏联的旅行在他的心头印了一种深刻的印象,因而在他的态度上,也起了一个重要的变化。
从这个时候起,他已不再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一个明知道黑暗,腐败,罪恶而漠然无动于衷的人了。新的世界已给了他以启示,指示了他的道路,他已深知道单单观察,并且把他所观察到的写出来是不够,他需要行动,需要用他艺术家的力量去打倒这些黑暗,腐败,和罪恶了。
在一九三○年,他就公开拥护苏联,公开地反对帝国主义者对苏联的进攻,从那个时候起,苏联已成为他的理想国。他说:
“我反对和苏联的任何冲突,不论那冲突是从哪方面来的。”在一九三一年,这位伟大的作家更显明了他的革命的岗位。他不仅仅把自己限制于对于时局的反应上,却在行动上参加了劳动阶级的斗争。他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去揭发出在资本主义的美国,劳动者们所处的地位是怎样地令人不能忍受。他细心地分析美国,研究美国的官方报告,经济状况,国家的统计,预算,并且亲自去作种种的实际调查。经过了长期的研究,调查,分析,他便写成了一部在美国文学史上空前,在他个人的文艺生活中也是特有伟大的作品:《悲剧的美国》,而把它掷到那自在自满的美国资产者们的脸上去。
杜莱塞的这部新着作,可以说是他的巨着《一个美国的悲剧》的续编。在这部书中,杜莱塞矫正了他的过去,他在一九二五年所写的那部小说是写一个美国中产阶级者的个人的悲剧,在那部书中,杜莱塞还是以为资本主义的大厦是不可动摇的。可是在这部新着中呢,美国资本主义的机构是在一个新的光亮之下显出来了。杜莱塞用着无数的事实和统计数字做武器,用着大艺术家的尖锐和把握做武器,把美国的所谓“民主”的资产阶级和社会法西斯的面具,无情地撕了下来。
这部书出版以后,资本主义的美国的惊惶是不言而喻的了。
他受到了各方面的猛烈的攻击,他被一些人视为洪水猛兽,然而,他却得到了更广大的人,奋斗着而进步着的人们的深深的同情,爱护。
从这个时候起,他已成为一个进步的世界的斗士了。他参加美国的革命运动,他为《工人日报》经常不断地撰稿,他亲自推动并担任“保卫政治犯委员会”的主席,他和危害人类的法西斯主义作着生死的战斗。西班牙之受法西斯危害,中国之被日本侵略,他都起来仗义发言,向全世界呼吁起来打倒法西斯主义。
从这一切看来,杜莱塞之走到社会主义的路上去,决不是偶然的事,果然,在他逝世之前不久,他以七十四的高龄加入了美国共产党,据他自己说,他之所以毅然加入共产党,是因为西班牙大画家比加索和法国大诗人阿拉贡之加入法国共产党,而受到了深深的感动,亦是为了深为近年来共产党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的英勇业绩所鼓舞。在他写给美国共产党首领福斯特的信中,他说:“对于人类的伟大与尊敬的信心,早已成就了我生活与工作的逻辑,它引导我加入了美国共产党。”然而,我们如果从他的思想行动看来,这是必然的结果,即使他没有加入共产党,他也早已是一个共产党了。
然而在这毅然的举动之后不久,这个伟大的人便离开了我们。杜莱塞逝世了,然而杜莱塞的精神却永存在我们之间。
(载《新生日报·文协》第四期,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