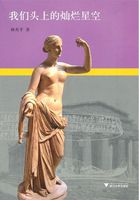中国的哲学是一个很大的范围,即使是做一个适合本书篇幅的概括,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手头的有限空间只能展示它的一些主要特征。
道德哲学,这个我们立刻遭遇的问题在遥远古代的中国是一件极端麻烦的事情。即使到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但是根据普遍接受的儒学教导,中国人可以暂时搁置这个问题。孔子毫不含糊地说人生下来就是好的,只有接触到坏的环境他才会变成坏人。他没有再详述这些教条,只是强调这是自然法则。谁知道在一两个世纪后它成为了严重的问题。他伟大的继承者孟子,继续维护这个论断,应对所有挑战者的攻击,尤其是其中一位叫告子的厉害哲学家。告子宣称正义从人的天性产生,就好像好的杯子和碗是用柳木块制作的一样,也就是塑造人心的环境决定了它的善恶。坏的匠艺会造成坏的结果,而好的匠艺会造就好的结果。明白地说,人的天性既不好也不坏,它之后变化取决于成长期的影响和成年期后的环境。孟子反驳道在用一块木头制作杯子和碗的过程,木头本身被毁掉了。然后,他指出,根据告子的推理,人的天性在从提取善的过程中已经被毁坏了。
告子还认为人的天性无所谓善恶,就像水一样随意向东方或者西方流动。根据每个具体的情况,水会没有分辨力地向任意一个方向移动。如果有向东流的可能性,它会流向东方;如果有向西流的可能性,它会流向西方。人性也是如此,它也是类似这样向善的或者恶的方向流动。作为回答,孟子坦率地承认,水会随意向东方或者向西方流。但他诘问是否水会没有分辨力地随意向上或者向下流动呢?然后,他宣称人类天性中向善的倾向就如同水向下流而不是向上流的自然性质。他说人们通过打击水面可以强迫水升起来,通过机械,人们可以把水升到山的顶端,但是,这些情况下人们的所作所为完全违背了水的自然性质,仅仅是暴力的结果;事实上,正是类似的暴力把人的性情扭转向邪恶。
告子说“人出生的时候只有天性”,他暗示所有的天性都是一样的,就像白色羽毛的“白”和白雪的“白”在性质上是一样的。孟子则说要是按他的理论,狗的天性就会和牛的一样,牛的天性也会和人的一样,这显然不可能。最后,孟子宣称:无论人们做了多大的恶,他们的天性从来没有被玷污过。他声称在黄金时代大多数的人是善良的,而在末世,大多数人则是邪恶的。这两种情况都完全不影响上天赋予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的善的天性,而不是人们所在环境塑造了他们的天性。
但是人类天性的问题并没有被孟子的辩论一劳永逸地解决。一个叫荀子的哲学家,他的活跃年代在孟子之后不久,得出了一种从孔子的理论看来远称不上善良的理论。甚至相比而言,告子的理论都比他的更加中立。他断言人一出生的天性是绝对恶的,他用下面的论述来支持这个观点:从最早的童年开始,人就被为自己个人欲望牟利的倾向支配,他的行为中最突出的是自私和争斗。他是妒忌、憎恨和其它激情的奴隶。法律的限制,师长的教导和影响,对于良好的政府和社会生活的安定十分必要。就像木头必须屈服于压力,才能变得平直;金属必须屈服于磨刀石,才能变得更加锋利。人的天性必须服从于训练和教育,才能从中获得塑造人类善的一面的正直与自我奉献的德行。不能用“眼睛能看,耳朵能听”来说明人天性就是善的,因为眼睛和耳朵的概念是从它们的性质而得名,不能看的眼睛就不能称为眼睛,不能听的耳朵就不能称为耳朵。能听和能视对人类而言是天性,而善是要人为培养,后天习得的。就像陶工或木匠通过加工手上的特定材料而制成一个碟子或一个凳子,贤者和人类的导师通过对人性的加工,使得人类拥有了正直的德性,他们就像转化木头的木匠和转化泥土的陶工。我们不相信上帝有偏向,会对某些人尤其不公。当一些人是邪恶的时候,而另一些人怎么可能是善的呢?荀子的回答是前者遵循了他们自然的天性,后者接受了制约,信从他们师长的教导。的确任何人都可能成为一个英雄,但并非所有人都必然成为英雄,也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强迫他们这样做。如果一个人有着改进的潜能,当遇到好导师的指导,同时和那些拥有诸如自我奉献、真诚、善良等等美德的优秀朋友交流,他会自然地吸收这些美德而达到同样的道德标准;然而,如果他的身边是那些邪恶的邻居,他每天都要见证欺诈、腐败和总体而言肮脏的行为,那么他会逐渐滑落到类似的轨道中去。谚语说:如果你不了解自己的儿子,就去看他的朋友。
下一步是哲学家扬雄(公元前53年到公元18年)采取的。他采取了一个折中上述两个理论的新理论。他的学说讲人的天性并非是全部善的,也并非是全部恶的,而是两者的混合,它向哪个方向发展完全取决于环境。这个对前两者折中的说法没有原来极端化的观点那么引人入胜。虽然后人还经常怀着敬意提及它,但扬雄尝试的解决方案没有获得多少重视。为了调和孟子和荀子明显分歧严重的理论,以及扬雄建议的折中之说,还存在另一种学说。著名的韩愈(他活跃在公元768年到公元824年)——之后还会马上提到——是儒教的支柱和推广者,他为了真理的事业服务了漫长的岁月,他的牌位被供在孔庙,只有那些丝毫没有争议的正统贤者才能获得这个荣誉。韩愈致力于修订“人性论”这个重要教条,他小心地伪装成批评孟子,而不是孔子,其实提出性善论的真正的责任人是孔子。韩愈宣称:根据他自己的意见,人的天性并非是统一的,而是分成三品——也就是上、中和下。上品的天性是善的,并且是完全的善,除了善没有其它;下品的天性是恶,完全的恶,除了恶没有其它;而中品的天性在正确的引导下向至善上升,或者在错误的引导下向至恶下滑。
在孟子的年代争议不断的另一个问题,从当时两个哲学家墨翟和杨朱的激烈争论中产生。前者传授一套兼相爱、交相利的学说,来治疗不良统治带来的问题,并适应社会和谐的需要。他的学说颇有几分道理:如果封建国家间停止战争,家族间停止争执,盗贼停止偷窃,主君和臣民凭着宽仁和忠诚而活,父亲和子女凭着善良和孝道而活——那么帝国的统治会相当良好。但除了说明导师的影响能阻止邪恶和鼓励兼爱,我们的哲学家并没有为我们到达这个理想的境地提出任何实际建议。
杨朱的学说可以总结为“人人为己”,于是他就自然和墨翟的学说针锋相对。某日有人向他提问,是否愿意让出自己的一根头发来增益这个世界。杨朱回答说一根头发不可能对这个世界有任何增益。那个人进一步追问如果一根头发真的会对世界有增益,他是否愿意。杨朱据说没有作出答复。针对这个故事,孟子说:杨朱的理论是“人人为己”,虽然拔下一根头发杨朱或许可能增益整个世界,但即使如此他也不会去做;墨子的学说是“兼爱”,如果拔下他头上所有的头发,乃至直到他脚上为止的毛发,能够增益整个国家,墨子就会那样做。这两个理论都不美妙,中间道路才是正确的选择。
中国的哲学家很自然地开始思辨宇宙的起源问题。我们从传说中得知有个叫盘古的不可思议的存在,没有人可以说清楚他到底如何出现的。盘古拥有完美的知识,他的职能是安排好逐渐发展的宇宙的秩序。他经常在图像上被描绘成手上有一柄巨斧,从刚刚逐渐成形的物质中选取材料构建世界。盘古死亡的时候,他创造世界的细节部分浮现出来:盘古的呼吸成了风,他的声音成了雷霆,他的左目是太阳,右目是月亮。他的血液成了河流,头发成了树林与植被,肉块变成了土壤,汗水变成了雨滴,他身上的寄生虫是人类族群的先驱。这种材料只能满足那些没有知识的人,而那些知识分子和受过教育的人需要更多的东西。于是产生了下面的学说:原本十分费解的《易经》——通常它被认为是儒学经典最古老部分——在11世纪到12世纪,经过逐渐的完善,达到了确定的状态。根据这套学说,曾经有段时间,在数字能够表达的时间之外,那时没有东西存在,接着出现一个法则。一段时间的流逝后,这个法则演化为两个各方面特征完全对立的法则。一个法则代表光明、热、男性,类似的现象被分类为阳性;另一个代表黑暗、寒冷、女性,其它类似现象被分类为阴性。两个法则的互动经过适当比例的调整产生了土、火、水、木和金五种元素。所有能见到的自然就轻易、迅速地形成了。这就是儒学的理论,但是孔子从来没有抱有过这些观念,这个理论和《易经》联系的真实性也充满疑问。
庄子,一个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的哲学家,他不仅是一个神秘学家,也是一个道德主义者和社会改革者。关于世界起源的主题他认为:“如果有一个存在,那它一定是‘无’。如果这个时期存在,在它之先必须还有一个时期,那是一个即使“无”也不存在的时期。对于‘无’,真有人能说出它是存在还是不存在吗?”
“无”是庄子思想练习中一个偏爱的术语。光问无道:“先生,你存在还是不存在?”它没有回答,光去看无的表情。无隐藏着,无如同虚空,整天在看,却看不见它。光大声呼喊:“太棒了,谁能和它相比,我可以成为无(也就是黑暗),但我不能成为无无。”
孔子对于死亡和彼岸状态的主题没有发表任何观点。他的主题始终是此生和此生的责任,他把对未知的思辨看成纯粹在浪费时间。当他三个朋友中的一人死亡时,孔子派遣一个弟子去吊唁余下的两人,弟子发现他们坐在尸体的旁边,欢乐地歌唱和弹奏古琴。他们坦白相信较新的信仰:生命是梦幻,而死亡才是觉醒。他们相信死亡的时候,真人“登上了天堂,在云中漫步,超越了空间的限制,超越了存在,永远没有止境”。当震惊的弟子报告他看到的事情,孔子说:“这些人在人生的法则之外旅行,我在人生的法则内旅行。所以,我们的道路不会相遇。我不该让你去致哀。他们把人生看成巨大的肿瘤,死亡则让他们解脱。他们同样不知道诞生前他们在哪,死后他们去哪里。他们忽略了自己的激情,他们不凭借自己的耳朵和眼睛。在永恒内他们来来往往,不承认有一个起点和一个终点。他们在尘世的尘埃外漫步,在无为的王国漫游。这些人怎么会为这个世界的陈规而烦恼,或者在意别人怎么看待他们呢?”
庄子说:生命来到,不能被拒绝;生命离开,不能被挽留。但是人们还是需要保养好自己的肉体,这样才能保持生命。虽然这还不够,但是必须这样做,不能忽视。如果有人忽略了肉体,最好尽快离开这个世界,因为告别这个世界此人可以摆脱世界的关心。然而,内在于肉体的是气,它是同等重要,需要不断关照的对象。那些肉体完美的人,生气保持在最初的纯净状态——他和神合一。人经过这个尘世的生活,就像太阳光经过缝隙。不过停留一会儿,就奔向下一个目标。在凡人的熙熙攘攘的生活中没有什么真正的主题。某个变化带来了生命,而下一个变化就是死亡。生物悲鸣,人类觉得哀伤。箭筒滑下、衣袋落下,迷惑中灵魂拍起翅膀,肉体跟随着它,走上回乡的旅程。
庄子举了个例子告诉人们经过培育肉体可以达到什么程度。有某个人的鼻子结了非常硬的疥癣,它曾经还没有苍蝇的翅膀那样厚。他找了一个石匠来砍下来疥癣,后者以极大的灵巧性挥舞他的扁斧,而病人站得绝对笔直,一块肌肉都没有挪动,随石匠的斧子砍下,疥癣被完全切除,鼻子完全没有受损。这等神技当然众口皆传,一个封建王子,他的鼻子上也有疥癣,邀请石匠来切除它。然而石匠拒绝了这个尝试,宣称这个成功并不很依赖操作者的技巧,而是依赖病人的精神控制,病人把肉体变成了一个完美的无生机的物体。
哲学家惠子和庄子同时,但他的学派思想完全不同。惠子尤其喜爱诡辩,这也是古希腊智者学派和那些不高明的推理者热爱的东西。庄子承认他是个有很多想法的人,他的著作装满了5个推车——不过需要记住,它们是写在用弦条绑在一起的竹简上。但是他补充道惠子的学说似是而非,他的术语模棱两可。比如说,惠子声称诸如“坚”和“白”这样的抽象概念是不相联系的存在,理智只能同时分别意识到其中一种。他宣称新生的蛋有羽毛,因为最终它们会出现在小鸡身上。他断言火是不热的,感觉热的是人类。眼睛不能看,是人在看。圆规不能成圆,是人画出了圆。马和乌鸦是三个,因为分开来看它们是两个,而合起来是一个——二加一等于三。没有母亲的马驹从来没有母亲,如果它有过母亲,它就不是“无母亲的”。如果你有一个一尺长的木棍,每天切下它的一半,永远不能到达它的终点。
他的最大对手问惠子这些有什么用,惠子的努力和那些牛蝇与蚊子的努力差别不大,他发出噪音来压过回声,他像一个和他自己的影子赛跑的人。
当庄子临终的时候,他的弟子表达了要给他举办盛大葬礼的愿望。但是庄子说,“有了天和地做我的棺材和房子的骨架,太阳、月亮、星星做我的丧服,所有的造物护送我到自己的坟墓——我葬礼的一切不是都准备就绪了吗?”一个弟子争辩道“我们害怕天上的秃鹫会吃掉我们师傅的肉体。”庄子回答:“在地下我会成为秃鹫的食物,在地下我会成为蟋蟀和蚂蚁的食物。为什么剥夺一方的食物而送给另一方呢?”
中国的生活不全部是由读书学习和商业构成。最早的中国记载说在更遥远的时代普通人模仿贵族的行为,比起严肃的商人更热爱运动。目前王朝的第一位皇帝也是一位知名的运动家,他组织了周期性的围猎,规模十分盛大。
用鹰行猎在公元前一个世纪就开始实行,因为我们有一条那个时代某人的记载:“他热爱用马和狗来追逐到处奔跑的动物,或者用一个猎鹰来追踪野鸡和野兔。”这个运动现在还能在中国的北方见到:一只野兔被放开,一对土生的灰犬被派去追逐它,然而这些动物很快会被野兔拉开距离,兔子只需要直线跑而不是折回跑就足以摆脱它们。但是猎鹰突然降临,它利爪的一击,常常第一下就会让兔子呆住,使得猎犬能够追上得手。
那些以此为业的户外运动者经常使用时常创意十足的方法,这些方法运用在比起猎枪打猎的报酬更多的活动上,但它们很难被分类成运动。一个搜寻野鸭的人会追踪一群浅水区的鸭子,他给自己的头和肩膀戴上木条,逐渐接近鸭群,好像木条箱在水表面漂浮。一旦到达它们中间,他抬起一只水下的手,牢牢抓住一只野鸭子的腿,迅速地把鸭子拽下去。伙伴的突然消失看上去没有让它的同伴烦恼,在较短的时间内猎鸭人就能获得大丰收。传说孔子也喜爱运动,他从来没有让任何一只在树上栖息的鸟飞走——由此看来他的武器是弓和箭,这个故事是用来说明孔子是有高度自制力的。
很多中国诗人把娱乐放在到内陆湖泊的垂钓和打渔,但是除了纯粹运动方面,鱼竿让位给了专业性质的渔网。使用鸬鹚打渔曾被认为是外国旅行家编写的故事,但这确实是真事:在中国南方的河流可以见到小型木筏会带着几只鸬鹚,渔夫在木筏的尾部划桨。鸬鹚抓住了一条游来的鱼,渔夫再从它的喙拿过鱼。受过训练的鸬鹚在它的颈部套有一个环,这样鸬鹚就不能吞咽下它的猎物。每捕到一个猎物,渔夫就奖赏鸬鹚一小片鱼肉。训练良好的鸬鹚不用环箍住颈部也能值得信赖地去捕鱼。据说孔子喜爱打渔,但他不使用渔网。另有个古代的贤者甚至不使用鱼钩,而是在鱼竿上挂一块直的铁片,他似乎在想对于鱼群而言这个优势是不公平的。他公开宣称,只抓那些自愿上钩的鱼。通过这些简单的故事,中国人努力向孩子们传达伟大的真理。
很多曾经在中国的普遍的运动,已经在国家生活中消失了,只在书籍的记载中存在。在古老的过去其中有一项运动叫“角力”,公元前2世纪的记载提到过。这个运动需要披上牛皮,在头上戴上牛角和其它饰品,完成这些装戴后,再尝试击倒对手。1000年后的历史告诉我们了这种运动的结果:“头被打碎,手臂折断,宫廷的场地上流满了血。”
拳术,包括摔跤在内,在角力引进的几个世纪前就被中国人练习。一所公元500年建立的佛教寺庙的僧侣在拳术修习上达到了最高的成就。毫无疑问从他们的传人身上,日本人获得了现代柔术的知识,这是中国古代术语中“柔软的技艺”的对应名词。一部16世纪军事著作中关于“拳术”的一些说法能让我们对这项中国运动有一些概念。
“学拳要身法活便,手法便利,脚法轻固,进退得宜。腿可飞腾,而其妙也。颠起倒插,而其猛也。披劈横拳,而其快也。活捉朝天,而其柔也,知当斜闪。”引自戚继光《纪效新书·拳经捷要篇》。——译者
中国人很早就在玩足球,起初,它是一个中间填塞了毛发的球体。从公元5世纪开始,它成了一个用羽毛制成的鼓满了的气囊。我们找到了一幅球门的图画,有点类似凯旋门的拱,也知道了球员的技术术语和位置。但即使我们统计到超过70种踢法,仍不清楚游戏的具体规则。一个作家记载道:“胜利者会受到奖赏,得到花卉、水果和酒,甚至银碗和锦缎。而失败队伍的队长会接受鞭打,忍受其它没有尊严的事情。”这个游戏消失了几个世纪,现在外国人管理的学校和学院重新复兴了这个运动,新生一代对此十分欢迎。
马球最早在中国文献中被提到是公元710年,这个被记载的游戏在皇帝和他的宫廷前举行。马球流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女性都学习这个游戏——她们是在驴背上比赛。契丹族的鞑靼人是技巧最好的选手。有人疑问是否这个游戏是从契丹发源的,也有可能马球是从波斯引进的,遥远的古代中国和这个国家有过交流。公元10世纪的一位大臣厌恶皇帝过度沉迷于这个游戏,提交了一份长篇奏折迫使他的君主放弃练习这个游戏。这个建议提出的理由有三条:“(1)君主和他的臣民一道游戏,必然存在竞争。如果君主胜利,则臣民蒙羞;如果前者失败,后者则欣喜。(2)君主跃上马背,挥动马球棒,到处跑马,模糊了阶级的区别,而只存有胜负之心,这对于所有礼仪中君臣的关系是毁灭性的。(3)君主把对帝国的责任放在一边,却观看这场有潜在事故可能的游戏,是对国家的失职,也没有考虑他尊贵的皇太后的感情。”
一个大臣需要记住他的主要职责是没有畏惧或者谄媚地向他的君主提出建议,当君主的行为会对国家不利,或者败坏宫廷的名誉时,需要大臣公开大声地抗议。大家很清楚这样的抗议会给大臣们自己带来极大的危险,他们需要准备为可能被诬蔑为误国的建议而丢掉脑袋,虽然事实上这些建议只是在那个时刻让君主不快而已。
在公元814年某位皇帝——他曾经是一个狂热的佛教徒——为了接受佛骨安排了盛大的典礼,佛骨是从印度来的圣物。当时的主要大臣韩愈(前文已述)觉得这种行为实在过分,他是一个来自民众的人,通过自己的才能得到提升,更糟糕的是,他曾经因为递交一份关于税收的攻击性奏折而被流放了11年,他已经忘记了这件事,现在才回想起来。他立刻寄了一份尊敬但语气强烈的排佛宣言和他所有的作品,恳请他的君主不能因为容忍这个要举行的堕落展览而玷污了儒学的纯净。如果不是朋友的说情,对这份大胆奏折的答复只有死刑。最后的结果是韩愈被流放到现代汕头的附近,那时那里是个荒蛮的未开化地区,还没有完全融入帝国。他亲自致力于开化当地粗野的居民,直到流放令很快被撤销,他再次回到朝廷任职。今日那里还有保存着一个纪念韩愈的神龛,有着下列铭文:“他到哪里,就洁净那里。”
另一为著名的大臣——他的盛年是200多年后——也曾经经历过几次流放,在对他的先驱者的荣誉和光荣致敬的铭文中,他写道:“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引自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译者
从公元14世纪起,开始存在称为都察院这样一个固定的机构,它的成员被称为君主的“耳目”,它的任务是揭露任何政府或者任何个体的大臣以皇帝名义行使的恶政,并有权建议否决这些恶政。进行指责的那个言官名义上完全免除任何惩罚;但在实践上他清楚自己不能太依赖正义或者仁慈。如果他判断自己的言论不会被宽恕,他会递交奏折,然后立刻自杀以吸引公众的关注。
允许自杀,不必忍受公开处决的耻辱,有时候被扩展为高级官员的特权,他可以在某些不需要特别黜免的情况下结束生命。从皇帝那里送来的丝绢会奉给有问题的官员,他会立刻结束自己的生命,虽然未必要使用自缢的方式。这是较普遍的情况,他可能服用毒药,称为“吞金”。长期以来,人们一直相信中国的高级官员未必会真的吞下金子,金子的属性是无毒的,有人说他们使用的是金子做的叶子,叶子被吸入人体,引起窒息而死。一些头脑简单的人——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有——现在还相信这点。但一些当地的权威人士指出,那些被雇佣来提炼黄金的工人常常偷窃并且吞咽下金条,并没有产生任何严重的后果。另一个解释可能更像真的:“吞金”是个委婉的语汇,中国人喜欢用它来表达痛苦和反感的主题。没有一个皇帝“死了”,而是“宾天”。没有一个儿子会说他的父母“死了”,而仅仅是“他们不在了”。一个官员的死亡被表达为“捐馆”,一个普通人的死可称为“作古”,就像我们说“他随了大多数人的路”。棺材中的尸体是安放在“寿材”里,下葬的时候,坟墓被称为“寿域”或者“夜台”。所以,说一个人服毒自尽,是一个听上去不礼貌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