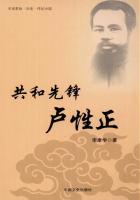爷爷马德禄的相声生涯最得意、最兴旺的时期就是与“万人迷”李德钖搭伴时期。“万人迷”实际是父子两代,第一代“万人迷”是李德钖的父亲李广义,他善于说书、唱太平歌词连二黄梆子也无所不能,特别是说神说鬼能达到迷人的地步。他说鬼不是完全依据《聊斋志异》或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而是他自己看了大量的神鬼故事搜罗了许多有关神鬼的民间传说,再糅进一些迷信的东西加以编撰达到了“自神其术”的地步。据说他可以从晌午开场一直说到午夜,颠簸离奇的内容、绘声绘色的描述,往往使听众心寒胆战散场后非跟他一道走不可。李广义以这种口头民间艺术的魅力赢得了“万人迷”的绰号。光绪二十年慈禧六十寿辰为观赏取乐,把北京城各行各业的生意人及作艺的召集到颐和园宫外摆摊设案亮地划锅。叫卖的、唱戏、唱歌词的、说相声的、耍大刀的、盘杠子的应有尽有。李广义也被召去并且以学唱二黄梆子得到封赏,故一时名噪京都。
李广义死后他的儿子小锁子继承了其父的衣钵继续说书、说笑话,后来小锁子拜恩绪为师才取名德钖,艺名“小万人迷”。“小万人迷”初露头角就轰动一时,当他和爷爷马德禄搭伴到天津的时候已经是三十二岁的中年人了。因此将“小万人迷”的“小”字抹去,承袭了“万人迷”的艺名。
据说当时号称“大腕儿”的“万人迷”是不随便找搭伴的,自从与爷爷合作二人如鱼得水配合默契演出效果不断攀升,两人相对稳定了许多年直到“万人迷”去世。旧社会吃开口饭的本来就衣食无靠,特别是相声行当逗捧双方在台上是演出伙伴,生活中就是相依为命的亲人,演出的收入就是一家老小的活命钱。因此“万人迷”的沉浮对爷爷是至关重要的。
李德钖爷爷不愧是我爷爷的亲密伙伴,有很多高人之处,他高高的个头,黑黝黝的脸,两只眼珠滴溜溜炯炯有神,一上场逗人发笑独不见他一丝笑意。他的“玩意儿”可称得雅俗共赏,南市、鸟市、三不管儿的市民百姓劳苦大众欢迎他,文人墨客也多有为他捧场。当年天津四大文人名士:严范孙、华世奎、孟广慧、赵元礼都是“万人迷”的热情听众。他们不仅爱听“万人迷”说相声,而且与“万人迷”交朋友,赞助“万人迷”编创相声段子,整理他的演出本子。这些名士对“万人迷”的相声有一定的影响,“万人迷”拿手的段子属文字游戏的许多都是经过名士润色、雕琢的。他的脍炙人口的单口相声“柳罐上任”(解放后改编为“糊涂县官”)针砭清末卖官鬻爵的腐败时政、讽刺一个暴发户花钱买了个知县,上任以后不懂官场规矩,闹了许许多多笑话。这段故事本来是用漫画手法展现出来,经过文士笔下加工,再经“万人迷”有声有色的表演,将这幅漫画中的人物一个个都活跃起来。
“万人迷”有成功的才能也有失败的缘由,他为人落拓不羁,颇有几分穷不怕的遗风。他嗜赌好抽(鸦片烟)经常身无分文,无钱吃饭便把衣物送进当铺,没米下锅也不见他犯愁,数九寒冬常常单衣薄衫蹲在墙角里晒太阳。不过,在“万人迷”短暂的一生中也曾“抖”过一次。那是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的时期,“长腿将军”张宗昌在天津听“万人迷”相声每有赏钱,总在百元之谱。有一回“万人迷”在山东济南府说相声,应了一个堂会,赶巧张宗昌是这个堂会的上宾。一方面有点儿“他乡遇故知”的意味,另一方面也是听相声笑得十分开心,当时正在赌博场上的张宗昌一时乐不可支。为了显富,竟把赌桌上的赌注、赌资悉扫一光全部赏赠给了“万人迷”,据说约有千金。“万人迷”得了这笔“重赏”回到天津赎了旧当,置了新装,典了房子、娶了妻子,结束了光棍汉的生活。当然,这样一笔钱并不能改变“万人迷”这样一个旧艺人的命运。1929年风靡京津的“万人迷”,贫困潦倒溘然而逝终年不过四十岁。爷爷和艺友为其办了后事,还凑钱还了部分债务。
“万人迷”作古了,爷爷马德禄失去了搭伴,孤掌难鸣又被戏园辞退。“万人迷”的凄凉下场已经够让他寒心的了,再加上没有稳定的收入,家里的日子更不好过了。这就直接导致了爸爸的弃学从艺,奠定了他毕生从事相声事业的基础。爷爷生于1882年,这位“相声八德”中的佼佼者一世奔波兴衰荣辱,曾给多少人家带来过欢乐,到头来自己却连累带气于1935年黯然去世。享年五十四岁。他有两个弟弟也就是我二爷、三爷,生活都很拮据,很早就分家另过。据说互差三岁。大约可以推算出二爷生于1885年卒于1951年,三爷生于1888年卒于1949年。另外三奶奶早逝,二爷去世后爸爸把二奶奶接到家中一起生活。二奶奶叫安玉文,她老人家生于1897年,1967年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享年七十岁。
我大伯马桂元生于1912年,由于爷爷看透了作艺在那个年代是没有出路的,恨不得脱离这个行当,所以从小供我大伯上学堂直到天津东马路甲种商业学校毕业,还在青年会补习过英语。虽然爷爷奶奶都指望我大伯走“学而优则仕”之路,怎奈这样的家庭哪有高亲贵友可攀,出出进进大多是相声行人,耳濡目染全是说、学、逗、唱。我大伯有文化、有心路,记忆力又好,潜移默化中“贯口活”的“趟子”不管多长、多拗口他说起来不费劲,而且气口好,嘴皮子利索。连我爷爷有时都纳闷儿,真的是“无师自通”吗?“万人迷”闻知此事还考了我大伯一次,包括单口、对口、群活,结果是成绩优秀。“考官”不断地连连点头儿说:“味儿真‘正’呀!”“万人迷”对爷爷说:“桂元是说相声的料,瞧他说嘛是嘛,学嘛像嘛、唱什么有什么味儿,看来‘命里注定’吃这碗饭!”而我大伯自己也对相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识时务者为俊杰”,爷爷经过反复考虑认为大伯也是很难当官作贾,况且“强扭的瓜不甜”便同意了我大伯说相声。
“万人迷”看中了我大伯,愿教;我大伯相中“万人迷”,愿学。真是一拍即合。我大伯马桂元一方面拜“万人迷”李德钖为师,一方面接受父亲的家传,经过这样两位名师的亲传、调教和他自己的刻苦钻研,大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在京津两地崭露头角。而相声技艺对我大伯来说可算得上是“无不通晓”。
他说的相声最大的特点是含蓄,不论说什么“火爆”的段子,他总是那么温文尔雅,听众被逗得笑破肚皮他却没有纹丝笑意。这种风格本来是恩培(爷爷的岳父)和爷爷的相声传统特色,大伯不但继承了还有所发展。因为大伯有文化不仅能改编,还能自编自演,在台上潇洒自如得心应手。特别是对一些文学性较强的段子如《反八扇屏》、《文章会》等说的咬文嚼字耐人寻味,大伯说的单口《三近视》、《假行家》、对口《吃元宵》、《醋点灯》、《学四省话》不但精彩,而且脍炙人口同行折服。真可惜好景不长,我大伯马桂元在相声艺术上刚刚露了一点儿头角,口袋里开始有了点儿积蓄就落在旧社会这个黑染缸里,染上了吃喝玩乐的劣习。今天戒掉大烟,明天又抽上了白面,终于弄得贫病交迫。于1942年病死在天津,时年不到三十岁。
马桂元大伯的相声在圈内圈外都是有口皆碑的,他的死对相声界、对观众都是很大的损失,但最痛心的还是我爸爸。爸爸在失掉爷爷之后又失去了朝夕相伴的长兄,然而痛定思痛,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大伯又是一位反面教员,爸爸从大伯重蹈“万人迷”覆辙的教训中悟出了一条道理,那就是要成才,不仅是拼命钻研业务,更要不断的自我修身坚定意志,才能抵制黑色染缸的侵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