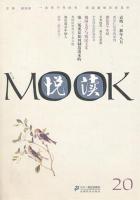雅与俗在现代文学中不只是一个审美品位的问题,更是一个历史、文化问题,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中,雅与俗会呈现出不同意义。徐、无名氏与现代主流文学的区别集中以雅与俗的对立表现出来,在这种对立的背后隐藏着的是深层的文化价值、审美观念的冲突。评价徐和无名氏的作品,雅与俗似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笔者不想用一个似乎是约定俗成的雅或俗的标准来对它们进行评判,而想首先考察的是雅与俗的二元对立在现代文学中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演变的?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中,“俗”意味着什么,而“雅”又究系何指?特别是在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性文化、文学格局中,什么会被划分到“雅”的一面,什么会被划分为“俗”的一面,雅与俗背后的新文学的价值等级系统是怎样的,而“新浪漫派”在这样的文化格局中又是如何进行自我定位的,他们的文化认同与其同时代的主流文学即“雅文学”或“纯文学”相比又有什么不同?这就需要对现代文学中雅与俗的观念的形成、演变历史作一个考察。
80年代末至9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对“现代性问题”讨论的展开,有的研究者发出了“捍卫现代文学”的呼吁,这说明关于“现代文学”的观念不只是一个指代某一时期的文学的时间观念,而是与某种构成“现代”的特定价值观念密切相关的。那么“现代”文学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学呢?文学上的雅与俗的划分与这种“现代”文学的观念又有什么关系?
对于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并不限于一时一地,而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拉美作家奥·帕斯在20世纪末反省近代世界文学所走过的“现代性”历程时这样说过:“现在我们正经历从一产生就构成现代的这两种思想的崩解,他们就是把时间看作向着日益美好的未来直线地持续延伸的观点和将变化作为时间的持续的首要形式的观念。这两种思想都已化作我们关于历史的走向进步的观念:社会在不停的变化,有时是以暴力的方式,而每一次变化都是一种前进。典型的时间已不再是过去及其虚幻的黄金时代;而实践以外的时间,天使与魔鬼、良知与罪孽的永恒都已让位于对进步的崇拜,希望之地属于未来。在政治活动的范畴变化表现为革命思想;在文学艺术领域则表现为新艺术概念,它建立在与最后的过去决裂的基础之上。今天未来已不再是一种吸引力,使其得以维持并获得证实的时间概念正渐渐消失。现代艺术是作为对法国大革命的回答而产生的既是回声也是反驳——,从而开创了现代派的先河:它的命运已经与革命是相融为一体。”奥·帕斯对现代性的这种论述也同样适用于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不过具体到中国,最能体现这种现代性追求特质的应该是“五四”提出的“新文学”的概念。由此把时段意义上的“现代文学”和“新文学”加以区分就很有必要了。“现代文学”作为一种步入现代社会的文化现象,具有包罗万象的性质,它可以把相互矛盾、抵牾的文学现象都纳入到它的研究视野,而不必有特定的价值取舍。而“新文学”的概念则不同,它有它的特定的价值关怀,它所追求的“现代”则是一种信念化、理想化的“现代”,它构成了一种属于未来的理想,一种值得追求的目标,它是以对凡俗化的日常生活的批判来确证自身,从而表现出一种再建生活价值、意义的努力,把一种“自然状态”导向“理想状态”的信仰。所以前者可以说是一种“泛义”上的现代性文学,后者则可以说是一种“特定意义”上的现代性文学,一种以反现代性的凡俗状态为特征的、将文化上的反叛与艺术上的创新融为一体的追求“现代”的文学。它突出的代表着人们去能动地创造历史、创造艺术的现代性倾向。
“五四”新文学的“文学理念”,是在一系列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中进行论证的,雅与俗的对立、新与旧的对立、人与非人的对立、传统与现代的对立等,都是搅合在一块,难以分开的,所以雅与俗已不只是一个美学品位的问题,更是一个历史、文化的问题。在梁启超等人发起的“小说界革命”中,小说是作为一种最佳的通俗教育工具而提到议事日程的,“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只不过在他们那里“有用”(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和“最好”(藏之名山的审美艺术价值)还没有划上等号,虽然他们提出“小说为文学最上乘”的口号,但他们心目中“雅”的文学的标准还是“古典”的,并没有像五四人那样真正体会到现代艺术超出功利之上的美感、意义。像梁启超对自己创作评价都是很低调的:“吾辈之为文,岂其欲藏之名山,俟诸百世之后也?应于时势发起胸中所欲言而已。然时事逝而不留者也,转瞬之间悉为刍狗。况今日天下大局日接日紧,如转巨石于危崖,变易之速,非言可喻。今日一年之变率,视前此一世纪犹或过之。古今之为文,只能以彼之报章,供一岁数月之遒铎而已,过期时,则以覆瓿焉可以。”梁启超虽然看到时代、历史对于文学的主宰性作用,但他并未将此视为是文学的“本质”,也就是说,他认为在文学的时代性、历史性之外,还有某种超时代、超历史的审美的特性,所谓“藏之名山”的价值也正在于此。
而到了“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对这种文学的时代性、历史性的强调则到了惊人的程度,一直到胡适直接将文学与历史合而为一,而倡导他的“历史的文学观念”,他的文学进化观的主要论点就是:“文学乃是人类生活状态的一种记载,人类生活随时代而变迁,故一代有一代的文学。”正是因为对文学的共时性审美特性的忽视,所以他的文学见解是非常肤浅、粗糙的,但正是这种文学与时代的联姻,使“新文学”具有了前所未有的使命感和历史意义。
“五四”文学革命之所以能完成梁启超们所未能完成的文学革命,在于作为一种“异质文化”以西方为参照的“新文化”和“新文学”的观念的确立。这就涉及了新旧文学的一大对立,即“人”与“非人”的对立。依周作人之见,“现代文学”是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的规范,所以它的取舍标准是非常严苛的,周作人几乎把所有的传统文学都否定掉了,都斥之为“非人的文学”。那么新文学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按照周作人的说法是:“用这人道主义为本(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这是从观念层面上而言,对新文学提出的要求。由此也就确立了新文学的现代“道统”——一种以人的道德为本的,人性解放主义的文学。与鲁迅一样,他心目中的“人”是对于现实的人的超越,他的人文主义是从未来吸取诗情的,人的启蒙是为了建成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第三种时代:“人的时代”。这种以未来为标准来衡量现代和过去的文学,把现实的人和凡俗化的社会作为批判对象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五四”新文学提倡者对于文学的世俗化采取的是一种批判性重造的态度,他们确定了平民在现代文学中的主体地位,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所倡导的就是“平易的抒情的平民文学”、“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明了通俗的社会文学”。而要打倒的则是“雕琢阿谀的贵族文学”、“陈腐铺张的古典文学”和“迂晦艰涩的山林文学”。这就构成了对古典的精英化文学的“雅、俗”观念的整体性颠覆。从儒道文化衍生的雅、正观念在新文学时代已失去了它的正面价值,而向以为“俗”的“平民”,被立为文学的主体,“平民文学”也被树为新文学的正宗。但这“平民文学”并非既有的满足平民审美需求的“通俗文学”,而是一种新的“精英文学”,一种以改造社会为目标的“严肃文学”,这使得以娱乐、消遣为旨趣的、丧失了精神超越向度的“俗文学”成为它的第一个改造对象。
“五四新文化运动”代表着20世纪中国一次社会群体心态的大变异,它集中表现为对既往的一切政治势力、政治努力的极度失望,希望通过全然与传统断裂的“西化”的“新文化”、“新青年”来彻底的改造社会。它不但要重建生活的价值体系,而且与时代激进的世界社会政治革命思潮实现了接轨。这种精英主义的社会改造目标的确立,造就五四“新文学”的一大特征,就是它将认识和教育功能置于文学的首位,而排斥文学的娱乐性,强调文学应承担严肃的社会责任和具有能动地创造历史的使命感。这种文学的“严肃性”首先就表现在它对于社会现实生活的关注和批判,从“文研会”时期对“鸳鸯蝴蝶派”和“黑幕小说”的批判中,就可以看到它不仅是要批判一种文学中的游戏消遣主义和拜金主义,而且要造就一种彻底的改变现状的“新人”、“新社会”,新文学运动是“改造国民性”的“现代性”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鲁迅的文学观是启蒙主义的,他认为文学“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的。“文研会”也强调“把文学等成高兴似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有时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同务农一样。”显然这里的“为人生”是要服务于人生的应然状态,而非人生的实然状态的。它追求的目标是人生的合理性。所以“为人生”的文学并不是一般性地表现现实的人生,而是要服务于它的改良人生的最终目的的。所以茅盾后来又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文学家所欲表现的人生,决不是一人一家的人生,乃是以社会一民族的人生,不过描写全社会的病根,而予以文学小说或剧本的形式出之,便不得不请出几个人来做代表。”周作人对此选择也是非常明确的,在《新文学的要求》一文中,他从历史的角度对历来的文学主张进行考察,将它归纳成两派:一是人生派,一是艺术派。他认为“这两派在文学发展上各有存在的理由,但在想从文艺上得到精神粮食的人却不能不决定趋向”,所以他选取了人生的艺术派。因为他认为“背负过去的历史,生在现今的境地自然地与唯美及快乐主义不能多有同情。这感情上的原因能使理性的批判更为坚实,所以相信人生的文学实在是现今中国唯一的需要。”
五四时期的“新文学”的划分标准主要还是新旧之分,因而尚有相当的包容性,新文学既包括了所谓“为人生而艺术”的“人生派”,也包括了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浪漫派、唯美派,甚至象征派,它是作为古典文学、通俗文学的对立面而出现的一种主要受西方文学影响的“新文学”。在五四时期,这种新文学是两种激进的文化思潮的纠结,一种是激进的社会政治思潮,一种是激进的审美主义文化思潮。前者的出现与其时代的激进的政治解放话语——法国大革命的理想、19世纪末西方盛行的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思潮的引进有关;后者的出现则是受了尼采、叔本华等非理性主义哲学和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前者着眼于社会的解放成为一种时代的主流话语,后者则着眼于对个体生存的价值和意义的探询,对人的感性生命的关注,成为一种个人主义的审美话语。这种新文学与西方文学建立起更为密切的关系,文学的世界性、现代性、创新性等成为新文学区别于旧文学的标志,也构成了现代文学中的“严肃”和“雅”的基本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