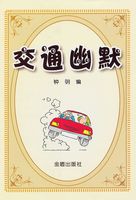德国文学史家奥伊巴哈对文学史上迄今存在过的叙事文学分成两大基本风格:一是侧重客观描写,符合亚里士多德的审美规范,根据模仿现实的原则进行创作的,上自“荷马史诗”下至“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也就是“写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都称为“荷马方式”;一类侧重主观表现,不符合亚里士多德的审美规范的,上自古希腊神话中的怪诞作品,下经中古时期带有宗教神秘色彩的文学,包括但丁的作品、文艺复兴时期的“哥特”小说,直至20世纪的现代主义作品,总之,凡是根据主观的感受和想象进行创作的,都称为“圣经方式”。当然,这种区分方式也不是绝对的,往往表现出的情形是两种方式的混合,其中某一种占据主导地位。无名氏的《无名书》明显地带有“圣经写作”的特点,若用“荷马写作”的要求来衡量它,显然是会不得要领。但它又不是单纯的“圣经写作”,它要写的是一部“精神史诗”式的作品,将其小说放在动荡时代的大的历史背景下,来表现主人公二十多年来的上下求索的心路历程,这就带有了“荷马写作”的因素、动机,使《无名书》的写作情况变得非常复杂。
写作《无名书》时,无名氏的年龄是27岁至43岁,假如没有外在环境的影响,他在30岁左右,就应该能完成全书了。(前三卷的写作、出版只用了四年的时间。)显然,无名氏与另一类主要靠观察和积累进行写作的作家不同,他的写作主要靠的是想象和灵感,这使他显然会选择“圣经方式”这样一种更能发挥作家的主观想象能力和创造性的方式进行写作,但是,为其时代的知识分子写一部“精神史诗”的意图,却使这种创造性、想象性只能在历史的背景中展开,这就增加了作品的难度。若按现实主义要求来写这样一部作品,显然无名氏的生活阅历、观察、积累明显不足。《无名书》的时间跨度极大,从1920年“北伐”前夜一直写到抗战胜利、解放战争时期,将近三十年的时间。无名氏让他小说中的主人公亲历了历次大的政治事件:“北伐战争”、“四一二大屠杀”、“九一八事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但它描绘出的都只是一个时代的剪影、侧面,生活实感、密度都非常薄弱、粗疏。如写到战争时亲临其境的感受,就是借小说中的人物韩慕韩之口,讲述他在苏联战争中的经历,来渲染战争气氛。
以现实主义的标准来衡量,小说中人物的概念化倾向很重,只能说是一些性格单一的“扁平人物”。如果要对无名氏的小说来一个大胆的还原的话,他小说中的人物原型大概有这么几位:一是他的朋友韩国光复军参谋长李范奭将军,李将军走南闯北、侠骨柔情的传奇式的人生经历,对无名氏有极大吸引力,他在《无名书》中以韩慕韩的面目出现。另一位是医师兼艺术家周善同,他的哀感顽艳的爱情经历、人生磨难,在小说里以唐境清的形象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再一个是风流潇洒而又姿肆妄为的投机商人汪祖继,他在小说中转化为“飘海商人”庄隐出现。另外就是无名氏与之有较多交往的“前卫派”艺术家,如后来成为世界著名的“抽象派”艺术大师的赵无极、探讨中西艺术融合之道的著名画家林凤眠以及“哲学家”罗吟圃等等,都是《无名书》中的重要人物。他们构成了无名氏生活的一个基本圈子,都是些文人墨客,江湖人物,这些人大都处于历史主流的边缘,与其说是历史的参与者,不如说是历史的卷入者、旁观者。小说通过这些人来感知时代、表现历史,显然有视野局限、力有未逮,所以在小说中也只作为主人公印蒂活动的背景、思想和行为的衬托者存在的。《无名书》真正的主角不是他们,而是纯虚构的人物,一种精神存在的抽象物。这种精神典型的创造,就不是“荷马方式”所能胜任的了。
《无名书》中写得最有光彩、最有魅力的人物形象有三位:一个男人和两位女子:即主角印蒂和女主人公瞿萦以及“地狱之花”萨卡罗。按照作家的解释,瞿萦“这个菩提树性的透明女人”代表的是人间情,是真善美的极致,她给予印蒂的是“光风霁月的欢乐、沉醉、诗与透明”。她荷印蒂的爱情代表着一种真正的“大地的爱情”、一种人间生活的理想。印蒂虽为体验“地狱境界”离开了瞿萦,但小说最后,印蒂又回到了瞿萦的身边,这时的他已经认识到:“没有真正的大地爱情,就没有真正的世间法和永恒道德。”对她,作者是以一种完全诗化的方式,在风景绝优的西湖岸边的湖光山色中加以表现、渲染的。另一位女主人公萨卡罗则是作为一种“负的哲学”的代表出现的,作家是把她放在当时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的“销金窟”里加以表现的。无名氏曾谈到塑造这个人物的目的在于:“我把萨写成一个高级妓女型的哲学家。她有一套魔鬼主义加炼狱精神的哲学,也可说人类精神历史上‘负的哲学’的某种结晶。”“魔鬼主义的凭藉,常常是精神因素中的那些幻觉的肉瘤和瘰疬,它的高峰,则来自精神结构的总解体。”精神结构的解体,必导致一种及时享乐的颓废主义的盛行,大动荡时代传统的价值观念已经崩溃,而新的价值观念尚未确立,人们沉沦于感官的、肉欲的放纵之中,以一种末日情绪来对抗将要到来的未可知的恐惧,这正是“魔鬼主义”盛行的时代原因。所以萨卡罗的魔鬼主义便是这个时代的典型的精神症候。正如小说中所说:“也许,‘伟大’还没有出现,笼罩着这个宇宙的,是伟大面前的最后的庸俗,最后的痛苦、混沌、黑暗,于是人们便缩到简单的蜗牛壳里。有时找寻复杂,却是‘复杂’的沉沦。反正要沉到海底了,喝最后一滴酒吧!和女人睡最后一夜吧!这份沉沦,是时代的玫瑰,知识分子衣襟上不插一朵,就不算真知识分子。”这样一种精神典型的出现是不依赖具体的原型的,她完全是作者凭着想象创造出来的一种“时代象征”。
严格地说,小说惟一的主人公应该是印蒂,其他人物都近乎是他的陪衬。他在小说中也完全是作为一种精神象征而存在的。小说以他的戏剧化的心路历程为主要内容,让他忽而投身革命、忽而坠入情网、忽而走私、嫖妓、忽而去当教士和和尚、忽而去当高山上的隐士、忽而去创办“地球农场”,使他完全成为作家思想的一种传声筒。虽然他的人生历程被充分戏剧化了,但他仍然主要是作为一个坐而论道的思想者而存在的,他的思想也主要是通过滔滔不绝的演说来直接传达的,这就影响到小说的可读性。在这一点上,它与时代盛行的理论先行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有相似性。即作家不仅要再现现实,而且要写出现实发展的未来趋势,亦即要对现实作理想化的改造,使之符合一种“本质真实”。这种“客观的理想主义”和无名氏“主观的理想主义”都是建立在对现实的加工和合目的性改造之上的。所以它与后来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结合”的理论也是相通的,都存在着根据主题需要去组织情节,结构作品、突出中心人物的特征。这种现象颇有吊诡意味,从中也可以看到时代对于文学的深刻影响,它使两种背道而驰的创作追求竟能殊途同归。无名氏过于高扬的浪漫主义救世精神,最终使小说成为主人公的长篇思想独白。
从“史”的角度来衡量,《无名书》表现出很多缺失,表现出一种过于主观化、内在化、心理化的倾向;但从“诗”的角度来说,它却是非常成功的,因为他写出了“时代”在人的心灵感受中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以“写实”和“表现”相结合的方式,抒发个人对于时代社会的体验和感受,是《无名书》写作的一种独特的尝试,这种探索勇气还是值得肯定的。
第六章 “不合时宜的优雅与浪漫”
那时濒于崩溃而又趋于疯狂的国统区,真不啻是一座失火的森林:济慈的‘夜莺’和雪莱的云雀早已飞走了,也见不到布莱克和里尔克的‘豹’,只剩下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嚎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绿原《胡风和我》
在任何时代,中间分子总尽了很大的贡献,他们往往是文化的保姆,假如有一个时代不容中间分子存在了,这就是文化倒退的时代。
——无名氏《淡水鱼的冥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