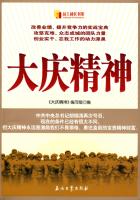《无名书》中的自然界是一个有机的世界,它由人来为之立言,又是人间世界的一个参照系统。正如主人公所说:“凡不先渗透宇宙,把它变成自己精神背景和自己生命的一部分的人,就不能最永恒、最绝对的容纳全人类。”所以在《无名书》对宇宙心灵的探寻,对自然的描写,成为其小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小说的灵魂所在,小说主人公印蒂的心灵探索过程就是与宇宙、自然达至和谐统一的过程。
《无名书》中有几个中心意象值得深入分析,因为其与全书的主旨密切相关。首先是“海”的意象,这个意象在小说中反复出现,每一次出现都是印蒂面临重大的精神危机之时,印蒂的第一次信仰危机发生在“四一二”大屠杀之后,他面临着一次重大的人生选择,在思想斗争最为剧烈的时候,他忙里偷闲来到海边。与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人世相比:“在海上,一切和平而蔚蓝。蓝色海像画似的开展着,把画轴埋隐在天际白色毛卷层云的波浪里……蓝色的天毡下,海水轻舐着淡棕色海岸,空阔中鸣起神秘和音,蓝色的和音。”印蒂躺在海滩上,整体崩溃了似的,痴望着海水,眼泪滴落下来。“海”这时对他是一种极古怪的存在,他似乎不相信人间还有这样宽广的东西:这样无比的和谐,无比的幽美。海的宽广,和谐,幽美以及包容一切的博大,与人世的争斗中,嘈杂、冷酷、偏狭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所以他说:“在目前这样的时代季节,在目前这样的精神背景下,海对人简直是一种最刻毒的讽刺。”在时代的历史真实与“海”的真实之间,他产生了疑问。海作为一种远高于人和历史的存在,质疑着他的理想和信仰,这是一种永恒的、无限的、和谐的、静穆的存在与一种短暂的、有限的、喧嚣、争斗着的存在的对比,在他眼中“海”化身为宇宙永恒的存在与他相逢。在《海艳》中,“海”是和平与美的象征,一种“天人合一”的空灵之境,“海”是印蒂当作《圣经》来读的一本大书。在人世争斗中他多年找不到的“绝对”,现在他在一秒钟的时间就求得了。在海的面前,再没有手段,怀疑,猜忌,阴谋,诬陷,卑劣,残忍,“这里只有一个绝对完整的表现:它诱惑人要无条件地活下去,召唤人绝对向永生走,向生命最深点走。这个时候,人不再感到生命的粗硬,人会用一种感激的情绪,来交出自己的一切。”印蒂完全被“海”所渗透,融化,实体化成了一片空灵,人、“海”契合无间。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能达到这种“空灵之境”的作品不多,原因在于主流文学多停留在一种政治,道德功利境界,感时忧国的传统、求治求善的参与精神,使他们紧跟时代,贴紧现实,对时代作一种即时性的参与、表现,鲜有兴趣关注社会现实之外的自然。再则在一个由政治功利主义建构起来的意义世界里,并没有给“自然”留出位置,“自然”只是作为一种可资利用的物质资源来存在的。对超现实、超功利的大自然的讴歌,有时会损及“凡俗存在”的至高无上的“神圣性”,郭小川的《望星空》、《致大海》等在五十年代的命运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他流露出一种与“大跃进”的“人定胜天”的时代氛围不协调“不健康”的情绪,虽然他认定“星空是死的,无生命的黑洞”,但毕竟意识到了一种比人更高的无限的宇宙的存在。从而表现出了对于“人间天堂”的宏大时代叙事一点瞬间的疑惑,就被认定是小资产阶级的有待改造的动摇性的不自觉流露,受到批判。
《无名书》中的另一个重要意象是“火”,它是一种生命原欲的象征,代表着一种强大的非理性的破坏力和创造力。“革命”就是这种被压抑的生命原欲的爆发。在《无名书》的第一卷里,对“火”有这样的描述:“火喷突着,飙旋着,燃烧着,古代恐龙似的冲驰着,冲破死夜,冲破黑暗,冲破空间。一道道硫磺火盘空腾涌,鼓怒煽炽,大簇大簇的,从一个黑暗扑到另一个黑暗,从一个空间扑到另一个空间。峻急的烟柱,汹然勃发,挟怒狂舞,蟒样的冲破火燎,印度女巫似的狂旋着,火苗一大丛,一大丛的闪起来,一大群一大群的红腥腥仿佛炎焰火中冲出来,赤腾腾地冲着,冲着,冲着……”
“火”与“炸药”、“野兽”、“火山”相联系,代表着动荡时代所释放出的人的原始欲望,它具有砸烂,冲毁一切的破坏力,同时也是创造新世界、新天地的热情和动力。它是盲目的,它的燃烧本身就代表了它的生命强度,它是非道德,非社会的人的欲望本能,是一种盲动的非理性的生命强力,(此生命力较近于西方生命哲学所指的生命力),而印蒂所要做的则要把这种沸腾的岩浆般的涌动着的生命之流熔铸到一种合乎理想的生命形式中去,使之摆脱它的盲目性,使之得到清明的理性的静化、引导,由此提高它的生命境界。由“自然”、“功利”、“道德”直到“天地境界”、“天人合一”,这正是印蒂的宗教性的救世情怀之所在。
《无名书》中的另一个重要意象是“山”,山在《无名书》中占有重要位置,它是乾坤流转中的一种不变的存在,它历尽沧海桑田之变,比人更古老,比历史更长久,它是一种永恒的化身和见证。“华山”是印蒂的悟道之源,其重要性自不待多言。这种由山派生出的“岩石哲学”在印蒂之父印修静那里被发挥到极致:他在临死之际把一块石头作为遗嘱送给儿子,这块捡自埃及金字塔下的风化岩石可以代他说明一切。这块石头并不美丽,但它却有一种令人颤栗的深邃。它不像红花绿叶那样使人易于接近,它却离人很远,很远,因为它上面已堆积了千万年的时间。所以,印蒂说:“有时候,一块石头比花朵还美,只因为它是一块石头。以前,我只懂得爱花。”印修静的“石头哲学”与《红楼梦》中“通灵宝王”颇有相通之处,它更质朴地标志着一种超人类、超历史的永恒的存在。正是因为有这种对时代、对人生、对宇宙的透彻的觉解,所以得此觉解的文弱儒生就有了一种超凡拔俗的勇气和达观,王阳明在以小舟而渡沧海的生死须臾之际,还赋诗道:“险夷原不滞心中,犹如浮云蔽太空,夜静海涛三千里,月明飞锡下天风!”是所谓“勇者无俱,仁者无忧!”无名氏的乐观和坚定亦来自于此,它与梁漱溟的“天生德于予”的自信以及表现出的那种“良知”的“傲慢”一脉相通。
《无名书》中充满了诗情画意,可以说是现代小说中写得最为优美、最为抒情的小说之一。小说中充满了一种诗的意境,特别是第二卷《海艳》,对于“空灵”之境的表现,是非常成功的。这也是作家在创作中的一种自觉追求。写作《海艳》时,他着重要传达的就是这种空灵之思、空灵之情、空灵之语和空灵格调。所谓空灵之境,也就是打破物我之界,与万物和谐交融。“它既涵蕴个人精神的绝对纯粹性,非凡纯洁性,甚至无比圣洁性,也涵蕴孩提的天真无邪的婴态,兼是宇宙浑然天成的静穆境界,自然也凝蓄一片美感的抒情和高贵的人格。这一切种种融合成一片超越的透明气象,这才真正创造出空灵境界。”
如《海艳》中写印蒂在西湖边的生活:
他爱平湖秋月的月夜。月亮起来了,他坐水榭围栏边,湖面铺满月色。湖水升得高高的,轻轻拍打着石砌,长长石阶,一部分浸入水中。风起处,湖水向上卷,在石阶上升高一级两级,水又轻轻落下去,像一片片绿叶从树上悄悄落下来。月光中,他最爱听的是那一阵阵湖水轻拍石器声,一种极空灵的声音。
印蒂认为大地上的人,至少也应该有这样一段生活,“把梦翻版一遍,并不是罪过。”再如,小说中写印蒂和瞿萦荡舟于西湖无边的月色中的情景:
这个月明之夜象一片妆台明镜,晃晃晶晶地照着他们,有似一袭没有分量的白色珠络纱,悄然披覆他们身上。夜已羽化了,又薄又亮。世界好像一下子突然涌现在面前,汹涌于明亮中。他们的情绪也因月明而晶明了,相互可以彻底捕捉对方。·
像此类优美的意境营造在小说中俯拾即是,《无名书》的写作在艺术上是一种前卫性和古典性的结合,它从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中吸取了很多营养,这使它带有很鲜明的民族色彩和东方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