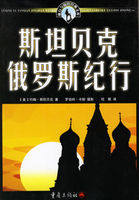天色从黄昏渐渐变得昏黑。小豆感到爷爷的模样也随着天色可怕起来,像一只蹲着的老虎,像一个瞎话里的大魔鬼。
“小豆。”爷爷忽然在那边叫了他一声。
这声音把他吓得跳了一下。因为他很久很久的不知不觉的思想集中在想着一些什么。他放下了大蚂蚱,他回应一声:“爷爷!”
那声音在他的前边已经跑到爷爷的身边去,而后他才离开了窗台。同时顽皮地用手拍了一下大蚂蚱的后腿,使它自动地跳开去。他才慢斯斯的一边回头看那蚂蚱一边走转向了祖父的面前去。
这孩子本来是一向不热情的,脸色永久是苍白的,笑的时节只露出两颗小牙齿,哭的时节,眼泪也并不怎样多,走路和小老人一样。虽然方才他兴奋一阵,但现在他仍恢复了原样。一步一步地斯斯稳稳地向着祖父那边走过去。
祖父拉了他一把,那苍白的小脸什么也没有表示地望着祖父的眼睛看了一下。他一点也想不到会有什么变化发生。从他有了记忆那天起,他们的小房里没有来过一个生人,没有发生过一件新鲜事。甚至于连一顶新的帽子也没有买过。炕上的那张席子原来可是新的,现在已有了个大洞。但那已经记不得是什么时候开始破的,就像是一开始就破了这么大一个洞,还有房顶空的蛛丝,连那蛛丝上的尘土也没有多,也没有少,其中长的蛛丝长得和湖边上倒垂的柳丝似的有十多挂,那短的罗罗索索地在胶糊着墙角。这一切都是有这个房子就有这些东西,什么也没有变更过,什么也没有多过,什么也没有少过。这一切都是从存在那一天起便是今天这个老样子。家里没有请过客人,吃饭的时候,桌子永久是摆着两双筷子。屋子里是凡有一些些声音就没有不是单调的。总之是单调惯了,很难说他们的生活过得单调不单调,或寂寞不寂寞。说话的声音反应在墙上而后那回响也是清清朗朗的。
比如爷爷喊着小豆,在小豆没有答应之前,他自己就先听到了自己音波的共震。在他烧饭时,偶尔把铁勺子掉到锅底上去,那响声会把小豆震得好像睡觉时做了一个恶梦那样的跳起。可见他家只站着四座墙了。也可见他家屋子是很大的。本来儿子活着时这屋子住着一家五口人的。墙上仍旧挂着那从前装过很多筷子的筷子笼,现在虽然变样了,但仍旧挂着。因为早就不用了,那筷子笼发霉了,几乎看不出来那是用柳条编的或是用的藤子,因为被油烟和尘土的粘腻已经变得毛毛的黑绿色的海藻似的了。但那里边依然装着一大把旧时用过的筷子。筷子已经脏得不像样子,看不出来那还是筷子了。但总算没有动过,让一年接一年地跟着过去。
连爷爷的胡子也一向就那么长,也一向就那么密重重的一堆。到现在仍旧是密得好像用人工栽上去的一样。
小豆抬起手来,触了一下爷爷的胡子梢,爷爷也就温柔地用胡子梢触了一下小豆头顶心的缨缨发。他想爷爷张嘴了,爷爷说什么话了吧。可是不然,爷爷只把嘴唇上下的吻合着吮了一下。
小豆似乎听到爷爷在咂舌了。
有什么变更了呢,小豆连想也不往这边想。他没看到过什么变更过。祖父夜里出去和白天睡,还照着老样子。他自己蹲在窗台上,一天蹲到晚,也是一惯的老样子。变更了什么,到底是变更了什么?那孩子关于这个连一些些儿预感也没有。
爷爷招呼他来,并不吩咐他什么。他对于这个,他完全习惯的,他不能明白的,他从来也不问。他不懂得的就让他不懂得。他能够看见的,他就看,看不见的也就算了。比方他总想去到那莲花池,他为着这个也是很久很久的和别的一般的孩子的脾气似的,对于他要求的达不到目的就放不下。他最后不去也就算了。
他的问题都是在没提出之前,在他自己心里搅闹得很不舒服,一提出来之后,也就马马虎虎的算了。他多半猜得到他要求的事情就没有一件成功的。所以关于爷爷招呼他来并不吩咐他这事,他并不去追问。他自己悠闲地闪着他不大明亮的小眼睛在四外的看着,他看到了墙上爬着一个多脚虫,还爬得口沙啦口沙啦地响。他一仰头又看到个小黑蜘蛛缀在它自己的网上。
天就要全黑,窗外的蓝天,开初是蓝得明蓝,透蓝。再就是蓝缎子似的,显出天空有无限深远。而现在这一刻,天气宁静了,像要凝结了似的,蓝得黑乎乎的了。
爷爷把他的手骨节一个一个地捏过,发出了脆骨折断了似的响声。爷爷仍旧什么也不说,把头仰起看一看房顶空,小豆也跟着看了看。
那蜘蛛沉重得和一块饱满的铅锤似的,时时有从网上掉落下来的可能。和蛛网平行的是一条房梁上挂下来的绳头,模糊中还看得出绳头还结着一个圈,同时还有墙角上的木格子。那木格子上从前摆着斧子,摆着墨斗,墨尺和墨线……那是儿子做木匠时亲手做起来的。老头忽然想起了他死去的儿子。那不是他学徒满期回来的第二天就开头做了个木格子吗?他不是说做手艺人,家伙要紧,怕是耗子给他咬了才做了这木格子。他想起了房梁上那垂着的绳子也是儿子结的。五月初一媳妇出去采了一大堆艾蒿,儿子亲手把它挂在房梁上,想起来这事情都在眼前,像是还可以嗅到那艾蒿的气味。可是房梁上的绳子却污黑了,好像生锈的沉重锁链垂在那里哀痛得一动也不动。老头子又看了那绳头子一眼,他的心脏立刻翻了一个面,脸开始发烧,接着就冒凉风。儿子死去也三四年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捉心的难过。
从前他自信,他有把握,他想他拼掉了自己最后的力量,孙儿是不会饿死的。只要爷爷多活几年,孙儿是不会饿死的。媳妇再嫁了,他想那也好的,年轻的人,让她也过这样的日子有什么意思,缺柴少米,家里又没有人手。但这都是他过去的想头,现在一切都悬了空。此后怎么能吃饭呢,他不知道了。孙儿到底是能够眼看着他长大或是不能,他都不能十分确定。一些过去的感伤的场面,一段连着一段,他的思路和海上遇了风那翻花的波浪似的。
从前无管怎样忧愁时也没有这样困疲过他的,现在来了。他昏迷,他心跳,他的血管暴涨,他的耳朵发热,他的喉咙发干。他摸自己的两手的骨节,那骨节又开始噼拍的发响。他觉得这骨节也像变大了,变得突出而讨厌了。他要站起来走动一下,摆脱了这一切。但像有什么东西锤着他,使他站不起来。
“这是干么?”
在他痛苦得不能支持,不能再作着那回想折磨下去时,他自己叫了一个口号,同时站起身来。
“小豆,醒醒,爷爷煮绿豆粥给你吃。”他想借着和孩子的谈话把自己平伏一下,“小豆,快别迷迷糊糊的……看跌倒了……你的大蝴蝶飞了没有?”
“爷爷,你说错啦,哪里是大蝴蝶,是大蚂蚱。”小豆离开爷爷的膝盖,努力睁开眼睛。抬起腿来想要跑,想把那大绿豆青拿给爷爷看。
原来爷爷连看也没有看那大绿豆青一眼,所以把蚂蚱当作蝴蝶了。他伸出手去拉住了要跑开的小豆。
“吃了饭爷爷再看。”
他伸手在自己的腰怀里取出一个小包包来,正在他取出来时,那纸包被撕破而漏了,扑拉拉地往地上落着豆粒。跟着绿豆的滚落,小豆就伏下身去,在地上拾着绿豆粒。那小手掌连掌心都和地上的灰土扣得伏贴贴的,地上好像有无数滚圆的小石子。
那孩子一边拾着还一边玩着,他用手心按住许多豆粒在地上轱辘着。
爷爷看了这样的情景,心上来了一阵激动的欢喜:
“这孩子怎么能够饿死?知道吃的中用了。”
爷爷心上又来了一阵酸楚。他想到这可怜的孩子,他父亲死的时候,他才刚刚会走路,虽然那时他已四岁了,但身体特别衰弱,外边若多少下一点雨,只怕几步路也要背在爷爷的背上。三天或五日就要生一次病。看他病的样子,实在可怜。他不哼,不叫,也不吃东西,也不要什么,只是隔了一会工夫便叫一声“爷”。
问他要水吗?
“不要。”
要吃的吗?
“不要。”
眼睛半开不开的又昏昏沉沉地睡了。
睡了三五天,起来了,好了。看见什么都表示欢喜。可是过不几天,就又病了。
“没有病死,还能饿死吗?”为了这个,晚上熄了灯之后,爷爷是烦扰着。
过去的事情又一件一件地向他涌来,他想媳妇出嫁的那天晚上,那个开着盖的描金柜……媳妇临出门时的那哭声。在他回想起来,比在当时还感动了他。他自己也奇怪,都是些过去的想他干么,但接着又想到他死去的儿子。
一切房里边的和外边的都黑掉了,莲花池也黑沉沉的看不见了,消磨得用手去摸也摸不到,用脚去踏也踏不到似的。莲花池也和那些平凡的大地一般平凡。
大绿豆青蚂蚱也早被孩子忘记了。那孩子睡得很平稳,和一条卷着的小虫似的。
但醒在他旁边的爷爷,从小豆的鼻孔里隔一会可以听到一声受了什么委屈似的叹息。
×××老头子从儿子死了之后,他就开始偷盗死人。这职业起初他不愿意干,不肯干。他想也袭用着儿子的斧子和锯,也去做一个木匠。他还可笑地在家里练习了三两天,但是毫无成绩。他利用了一块厚木板片,做了一个小方凳,但那是多么滑稽,四条腿一个比一个短。他想这也没有关系,用锯锯齐了就是了,在他锯时那锯齿无论怎样也不合用,锯了半天,把凳腿都锯乱了,可是还没有锯下来。更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他眼看着他自己做的木凳开始被锯得散花了。他知道木匠是当不成了,所以把儿子的家具该卖掉的都卖掉了。还有几样东西,他就用来盗墓子了。
从死人那里得来的,顶值钱的他盗得一对银杯,两副银耳环,一副带大头的,一副光圈。还有一个包金的戒指。还有铜水烟袋一个,锡花瓶一个,银扁簪一个,其余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衣裳鞋帽,或是陪葬的小花玻璃杯,铜方孔钱之类。还有铜烟袋嘴,铜烟袋锅,檀香木的大扇子,也都是不值钱的东西。
夜里他出去挖掘,白天便到小镇上旧货商人那里去兜卖。从日本人一来,他的货色常常被日本人扣劫,昨天晚上就是被查了回来的。白天有日本宪兵把守着从村子到镇上去的路,夜里有侦探穿着便衣在镇上走着,行路随时都要被检查。问那老头怀里是什么东西,那东西从哪里来的。他说不出是从哪里来的了。问他什么职业,他说不出他是什么职业。他的东西被没收了两三次,他并没有怕,昨天他在街上看到了一大队中国人被日本人抓去当兵。又听说没有职业的人,日本人都要抓的。
旧货商人告诉他,要想不让抓去当兵,那就赶快顺了日本人他若愿意顺了日本,那旧货商人就带着他去。昨天就把他送到了一个地方,也见过了日本人。
为着这个事,昨天晚上,他通夜没有睡。因为是盗墓子的人,夜里工作惯了,所以今天一起来精神并不特别坏,他又下到小地窖里去。他出来时,脸上划着一格一条的灰尘。
小豆站在墙角上静静地看着爷爷。
那老头把几张小铜片塞在帽头的顶上,把一些碎铁钉包在腰带头上,仓仓惶惶地拿着一条针在缝着,而后不知把什么发亮的小片片放在手心晃了几下。小豆没有看清楚这东西到底是放在什么地方。爷爷简直像变戏法一样神秘了,一根银牙签捏了半天才插进袖边里去。他一抬头看见小豆溜圆的眼睛和小钉似的盯着他。
“你看什么,你看爷爷吗?”
小豆没敢答言,兜着小嘴羞惭惭地回过头去了。
爷爷也红了脸,推开了独板门,又到旧货商人那里去了。
×××有这么一天,爷爷忽然喊着小豆,那喊声非常平静,平静到了哑的地步。
“孩子,来吧,跟爷去。”
他用手指尖搔着小豆头顶上的那摄毛毛发,搔了半天工夫。
那天他给孩子穿上那双青竹布的夹鞋,鞋后跟上钉着一条窄小的分带。祖父低下头去,用着粗大的呼吸给孙儿结了起来。
“爷爷,去看莲花池?”小豆和小绵羊似的站到爷爷的旁边。
“走吧,跟爷爷去……”
这一天爷爷并不带上他的刀子和剪子,并不像夜里出去的那样。也不走进小地窖去,也不去找他那些铜片和碎铁。只听爷爷说了好几次:
“走吧,跟爷爷去。”
跟爷爷到哪里去呢?小豆也就不问了,他一条小绵羊似的站到爷爷的旁边。
“就只这一回了,就再不去了……”
爷爷自己说着这样的话,小豆听着没有什么意思。或者去看姑母吗?或者去进庙会吗?小豆根本就不往这边想,他没有出门去看过一位亲戚。在他小的时候,外祖母是到他家里来看过他的,那时他还不记事,所以他不知道。镇上赶集的日子,他没有去过。正月十五看花灯,他没看过。八月节他连月饼都没有吃过。那好吃的东西,他认识都不认识。他没有见过的东西非常多,等一会走到小镇上,爷爷给他粽子时,他就不晓得怎样剥开吃。他没有看过驴皮影,他没有看过社戏。这回他将到哪里去呢?将看到一些什么,他无法想象了,他只打算跟着就走,越快越好,立刻就出发他更满意。
他觉得爷爷那是麻烦得很,给他穿上这个,穿上那个,还要给他戴一顶大帽子,说是怕太阳晒着头。那帽子太大了,爷爷还教给他,说风来时就用手先去拉住帽沿。给他洗了脸,又给他洗了手。洗脸时他才看到孙子的颈子是那么黑了,面巾打上去,立刻就起了和菜棵上黑包的一堆一堆的腻虫似的泥滚。正在擦耳朵,耳洞里就掉出一些白色的碎末来,看手指甲也像鸟爪那么长了。
爷爷还想给剪一剪,因为找剪刀而没有找到,他想从街上回来再好好地连头也得剪一剪。
小豆等得实在不耐烦了,爷爷找不到剪刀,他就嚷嚷着:“走吧!”
他们就出了门。
天是晴的,耀眼的,空气发散着从野草里边蒸腾出来的甜味。
地平线的四边都是绿色,绿得那么新鲜,翠绿,湛绿,油亮亮的绿。
地平线边沿上的绿,绿得冒烟了,绿得是那边下着小雨似的。而近处,就在半里路之内,都绿得全像玻璃。
好像有什么在迷了小豆的眼睛,对于这样大的太阳,他昏花了。这样清楚的天气,他想要看的什么都看不清了。比方那幻想了好久的莲花池,就一时找不到了。他好像土拨鼠被带到太阳下那样瞎了自己的眼睛,小豆实在是个小土拨鼠,他不但眼睛花,而腿也站不住,就像他只配自己永久蹲在土洞里。
“小豆!小豆!”爷爷在后边喊他。
“裤子露屁股了,快回去,换上再来。”爷爷已经转回身去向着家的方面。等他想起小豆只有一条裤子,他就又同孩子一同往前走了。
镇上是赶集的日子,爷爷就是带着孙儿来看看热闹,同时,一会就有钱了,可以给他买点什么。
“小豆要什么,什么他喜欢,带他自己来,让他选一选。”祖父一边走着一边想着。可是必得扯几尺布,做一条裤子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