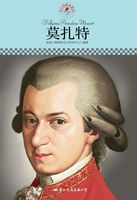在为芭蕾舞团工作的日日夜夜里,剧团里的一位女演员引起了毕加索的特别注意。在她白玉般的脸庞上,有一双明亮动人的黑眼睛,以及线条优美如同希腊女神般的鼻子,柔软的秀发飘拂在肩上,使她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上去,都是那么楚楚动人,她的名字叫奥尔佳·科克洛娃。
奥尔佳·科克洛娃的父亲是俄罗斯帝国军队的一位上校。达吉列夫把她留在团里,并非因为她的舞蹈专长,而是因为她的贵族血统能提高剧团的社会地位。
奥尔佳·科克洛娃1891年生于乌克兰的涅金。她从小就学习芭蕾舞,可直到1917年才在舞剧《贤良淑女》中有了精彩表演的机会,对于芭蕾舞演员来说,这显然为时已晚了。
起初,奥尔佳面对毕加索的追求有些惊慌失措。奥尔佳是个好姑娘,她待人接物十分谨慎。但毕加索艺术家的聪颖灵巧和深孚众望,很快就俘获了奥尔佳的芳心。
事实上,奥尔佳也早就注意到了毕加索。他虽然矮小,却很健壮。尤其是他的成就、声誉以及才气吸引了她,他们俩很快就交上了朋友,继而就形影不离了。
毕加索依照老习惯,把他的深情爱意倾诉在光滑的画布上。他用古典主义写实风格,逼真地描绘了他心上的美人——她头戴一块网状流苏型纱巾,黑玛瑙般的眼睛闪着敏锐的光泽,小巧平直的嘴微含笑意,好似一个坚定、刚强、富有个性的女子。
随后,毕加索又以奥尔佳为模特,继续采用古典写实的手法,绘制出了若干幅很成功的作品。
达吉列夫也答应了毕加索的要求,决定率芭蕾舞团赴西班牙去巡回演出一次,以便毕加索的家人能亲眼看一看奥尔佳。他们先到马德里,再到巴塞罗那。所到之处,剧团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热烈欢迎,不过,人们不是为演出叫好,而是他们引以为骄傲的毕加索回来了。
毕加索在家乡受到英雄般的欢迎,他的朋友和崇拜者还为他举办了一个特别宴会。这段时间,奥尔佳也过得很快乐,在宴会上,奥尔佳驾轻就熟,每天都快乐得像个天使。
在巴塞罗那,有奥尔佳的陪伴令毕加索生活得十分愉快,在这期间他给奥尔佳画了许多肖像。
1917年年末,毕加索返回了巴黎。在圣诞节前夕,毕加索描绘了一幅他想象中的俄罗斯雪夜:那皑皑的白雪,轻柔地覆盖着乡野大地,几颗明亮的星星在静寂的夜空中闪烁。毕加索把这幅画作为圣诞礼物送给了奥尔佳。
1918年的8月,毕加索和奥尔佳举行了婚礼。阿波林纳、科克蒂和麦克斯·杰克卜都来参加了。他们的蜜月是在离西班牙很近的比阿利兹度过的,他们就住在爱拉苏里夫人在那里的漂亮别墅里。这个地方远离战争。从他当时的画作可以看出,毕加索这时过得相当惬意。
别墅所在地清新的空气、旖旎的风光,使他精神爽快,干劲倍增。他用自己那支得心应手的炭笔,精心勾勒了海滩上的姑娘们。其中尤以那幅《十五位海滩裸女》最为著名。
那优美流畅的线条、十分妥帖的布局,把一群健美活泼的姑娘,潇洒自如地描绘出来,使这幅画成为毕加索线描的典范之作。在塑造这些穿着泳装的女人时,毕加索使用了完全不同的手法,沙滩上散布着一些出奇引人的石块,它们成为超现实主义画家们使用频繁的素材。
还有一幅名为《海水浴场里的少女》的油画,显露了画家对人体美的赞美,使人不能不惊叹毕加索构想的高超。
毕加索的日子过得逍遥自在、优哉游哉,爱拉苏里夫人有很多朋友和相识,毕加索为他们不少人画了像。因为战局有了好转,这些人的情绪比过去几年都活跃。
这年7月,曼金的坦克把德国人逼得节节败退,并且俘获了几万人;8月,英军席卷了西齐菲防线;9月,60万美军投入战场。血腥的战争就要结束了。毕加索对这些并不十分关心,不过,别人的快乐也增加了他的快乐。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停火。但是战争的乌云并没有马上消散,贫困、饥饿、混乱、萧条,毒气般笼罩在这块被炮火烧焦的土地上。
有一天,毕加索的电话铃声响了起来,他抓起话筒,听到的是阿波林纳死亡的消息。他一时惊呆了,说不出半句话,握着话筒的手也有气无力地松开了。他木雕似地愣了一会儿,抓起笔,在那张未完成的自画像上,又狠狠地抹上了几笔,以表达自己对死亡的憎恶和恐惧。
阿波林纳是毕加索忠实的老朋友,在事业上,阿波林纳一直给予他最真诚的鼓励、最有力的支持。不论是在他创立立体主义的时候,还是在他进行舞美设计的时候,都是如此。
毕加索在他一生的艺术实践中,受到过难以计数的困挫、责难、辱骂,毕加索都义无反顾地挺过来了,除了他天才的灵感和顽强的意志以外,那就是他总有为数不多的一些知音,他们在那个时代表现出来的卓越才华与优秀品质,给了毕加索以极大的信心。阿波林纳便是其中的代表。
毕加索清楚地记得,在《游行》首演时,部分观众由于不能理解剧中蕴含的奥妙,寻衅闹事时,是阿波林纳挺身而出。他头缠绷带,胸佩十字勋章,热情地向观众说明这个舞剧的新精神。
剧场一时安静下来,那些观众看到他是一位战斗英雄,又讲得头头是道,才慢慢平息了怒火。谁能料想,他竟在这如火的青春年华里死去。毕加索心里感到一阵阵刀绞般的疼痛。
阿波林纳死的时候,毕加索正好37岁。从这时开始,他就一再改变自己的绘画、素描和雕塑风格,不过这些都只是他个人的变革,因为他不可能再去打倒那些早就被他摧毁的传统了。
此时,毕加索的艺术创新包括了向新的巨大形式的进展,一种把人体扩展成巨大比例的独特作风,这些作品应并入他的新古典时期,不过目前他还是继续从事立体派的创作。
1919年初夏,毕加索偕同奥尔佳赴伦敦参加新舞剧《三角帽》的彩排。
《三角帽》讲叙的是一个西班牙老公爵,企图强占磨坊主年轻美丽妻子而未能得逞的故事。
俄国芭蕾舞团战后回到了欧洲,达吉列夫开始为1919年分外灿烂的一季做准备,其中一个节目就是《三角帽》,这出脚本是马提尼兹·西拉在他的祖国西班牙写的,同时音乐部分是安达鲁西亚的作曲家法雅谱的曲子,而毕加索成为设计布景和服装的最佳人选。
毕加索接受了这一工作,尽管他探索新方向的思路被打断了,他还是答应下来,并且马上投入到这出芭蕾舞剧的设计工作中。
这是一部短小精悍的舞剧。毕加索只要把他在温拉德或伯萨·韦尔等处展览的许多画作,还有“玫瑰时期”的作品,凑在一起就成了《三角帽》的动人布景。
毕加索设计的“斗牛场”布景,画面是:太阳在天空闪闪发亮,穿着披风的男人和戴着漂亮头巾的女人坐在斗牛场包厢里,被杀死的公牛正在被拖出场外。为了取悦观众,他采用西班牙的传统装束作为演员的服装。
1919年7月22日,《三角帽》在伦敦上演了,毕加索的布景受到全场的欢迎,舞剧演出极为顺利,当结束时观众的热情达到了顶点,鼓掌和欢呼声雷动,演员们都激动得流下泪来。
《三角帽》的演出大获成功。毕加索的舞美设计同在巴黎时一样,也得到了英格兰人的赞赏。谢幕时,毕加索迈着稳健的步子,面带着微笑,走上舞台。
他身穿一件晚礼服,腰系一根斗牛士皮带,向热情的观众鞠躬致意。那姿态既符合英国人的绅士标准,又略含西班牙人的风采,观众由衷地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
《三角帽》的演出成功,使毕加索认识了一大群喜欢举行宴会的人,他自己也较过去对宴会感兴趣,越来越多地参加这样的聚会。
毕加索事业上的成功,使他成为社交界引人瞩目的中心人物。他们夫妇俩被频频邀请参加各种豪华的聚会、高雅的舞会和隆重的首演式。在这些场合里,总是聚集着社会各界名流、富家商贾和才子佳人。
此时,他的新生活,宛如一曲曲华尔兹圆舞曲,时而快速旋转,时而滑步起伏,既令人陶醉,又令人迷茫。
实际上,毕加索对这种“名流世界”并不感兴趣。他采取的是若即若离的态度。因为,任何乐趣都不能与他孜孜求索中的艺术相媲美。他更不愿意因此困囿于其中,甚至是丧失自我。所以,他常常机敏地回避它。他坚定不移地固守着自己心中的艺术王国。
回到巴黎之后,保罗·卢森伯格为毕加索举行了一次展览,这是毕加索的首次大型个人展览。这次画展极为成功,不仅仅在于作品的出售上,更重要的是使许多人看到毕加索作品的各个不同面貌。
批评家以及来看画的公众都非常欣喜而且印象深刻。人们得到了一个概念,那就是发明立体主义的难解隐喻的手,同样可以造出立即可以看懂、而且使人陶醉的画作。
1920年6月的时候,奥尔佳怀孕了,当身孕越来越明显时,毕加索对“母性”题材的兴趣又恢复了。往日他曾经画过许多深刻的母与子的作品,常常都是年轻、脆弱的女人,美丽而出奇的优雅,大部分的画作中都带有对社会的批判。
然而,长久以来的明显批判已经消失了,他现在的思想是在另一个层面。现在的这些女人都是巨大的形体,不很年轻,有粗硬的大手和大脚,像神一般,超然独立。
几个月后,奥尔佳为毕加索生了一个儿子。毕加索有生以来第一次做了父亲。有了儿子,他欣喜若狂。他深知,这个孩子与他笔下塑造过的任何一个孩子都来得更真实、更可爱,这是自己的精血凝结而成的!
毕加索常常不惜时间地与儿子一起逗乐、一起玩耍。当儿子还在襁褓中时,他便迫不及待地以妻子和儿子为模特,精心绘制了著名的《母与子》连画。
做了母亲的奥尔佳,蜕去了女孩子的稚气,多了几分成熟女人的味道。画幅中,她的态度矜持,体态丰满,爱心盈溢。孩子则天真无邪、清纯可爱,洋溢着蓬勃的生命力。
为了能使妻儿过上舒适的生活,毕加索在巴黎的近郊找到了一所房子,他们在那儿度过了一段假期。那个地方相当大,足可让毕加索远离一个婴儿的哭喊和邋遢。不过这期间他尽可能耐着性子待在家里。他一次又一次地画着这幢别墅的内部,用一支特别细的铅笔,带着温和的嘲讽,画下每个微不足道的细节。
在那段时期,毕加索怀着一片童心,好奇地观察着儿子小保罗一天天地长大。他的画笔一直不停地描绘着自己的儿子。这一幅幅作品,俨然成了小保罗的成长日记。毕加索不但准确地记录了孩子惊人的变化,而且还细心地写下了作画的日期。
这段时日给毕加索带来了很多快乐,粗糙、真实、活泼、单纯,这是属于他自己的孩子,于是他不断重复地画着这个小家伙。惊人的创作活力是来自那个迷人的小天使。不过,更重要的是孩子成了他的一种作画动力。
要不是有这个亲骨肉,毕加索不可能画出一系列的母性作品,这些虽然与他新古典时期的女性题材有关,但儿子的出现却对其有一种特殊的影响。
由于孩子在婴儿期长得都很像,作品中吸着奶的小东西是不是小保罗就很难确定,也可能不是,因为画面里的这些母亲哪个都不是奥尔佳。奥尔佳比毕加索要矮一些,而画上的是些巨大而温和的女性,她们还带着简化的古典特质。
在以往的创作中,毕加索曾肆意地对他的描绘对象进行探险性的破坏,他肢解他们,分化他们,不管他们是男人或是女人,是模特或是妻子。而在画家的笔下,唯有一个人没有遭到此等“厄运”,这就是他的儿子小保罗。这是古典写实大师笔下的小保罗。他总是那么的纯真可爱,白白胖胖的小圆脸上,总挂着甜蜜的笑容。
有时,他满脸童真稚气地扮演哑剧小丑;有时,他手持拐杖和鲜花,扮演马戏团的丑角;还有的时候,他身穿镶金边的斗牛服,扮演着小小斗牛士。在这些画幅里,浸满了那种深沉的乃至神圣的父爱,这种父爱不仅仅在作画的那一刻出现过,而且还延续了几年、十几年。
有一次,毕加索同时画了两幅非常相似的大幅画作,都叫《三个乐师》。画中的这三个乐师,分别是白衣小丑、花衣小丑和天主教修士。他们各自戴着假面具,一个吹奏着单簧管,一个弹拨着吉他,另一个则手持着黑白分明的乐谱。这幅画被认为是合成立体主义的归纳与最高境界。
毕加索用他所喜爱的立体主义方法描绘了他们各自的形态,那三个硕大的身躯与那一双双蜘蛛般的手形成了强烈而有趣味的对比。色彩的配置,也很奇特,在暗褐色的背景中,有黑白的对比,有花格子的俏丽色面,更有雅致的蓝色穿梭其中。就在这些几何学的色面互相衔接交错之中,产生了音乐般的韵律和节奏感。
两幅画作都遵守着严格的立体派教条,空间是由平的、大致是直线所构成的一些面组成的;所用的色彩大致很鲜明,要不是用了很多严肃的蓝色的话,应当是相当欢愉的。
1921年,最重要的立体派作品就是这两幅《三个乐师》。有人认为它们是毕加索以往的成就和新古典人物画的分界线。
毕加索的大量立体派画作价格日益高涨,买了他的作品的人觉得自己应该认识一下作者,因而当毕加索回到巴黎后,他的社交活动日益繁忙起来。
1922年,经过科克蒂的介绍,毕加索结识了许多戏剧界及其他领域颇有来头的朋友。如果愿意的话,他每天晚上都可以去赴宴。由于精力过人,他常常乐此不疲。
夏季,毕加索常常携妻带子来到海滨。他平静地躺卧在沙滩,坦然地享受着身旁玩耍的妻儿带给他的幸福感。
这期间,毕加索画了几幅狄那的风景,还有一些女人和小孩儿。其中包括一幅特别温柔的母性作品。虽然画上的母亲仍旧硕大无比,却有着温和的粉红及灰色,有着“玫瑰时期”的温暖感觉。不再像是用大块石头刻出来的那样。他在这一时期的许多画作都存在这种风格。
毕加索在这个夏天创作最多的还是立体派的静物作品,这类作品有几十张,几乎都是传统立体派的玻璃杯、酒瓶、烟草或香烟盒等题材。颜色相当单调,几乎是单色的。这些画作有些用传统方法绘成,另外有些则是被称为斑马画法,也就是在一个颜色的平面上会覆盖着带状条纹。
说来有趣,一年夏天,毕加索度假返回巴黎后,当他打开衣柜,发现自己最好的一套毛料衣服被虫子全部蛀空了。那套衣服,除了接缝和麻衬依然如故外,其余的只剩下一个空壳——一个透明的轮廓。他可以清晰地看到口袋里装着的钥匙、烟斗、火柴盒。这个“透明体”引起了毕加索的兴趣,给了他一个启示。
于是,毕加索在作静物画时,采用了一个新的手法——在轮廓清晰的色块上,使用粗的直线和条纹,把光线“网”进画中,使之透出一种连锁式的透明。这就是他的静物画总给人一种鲜亮的感觉的原因之一。
而同时,大海也激发着毕加索的创作灵感,一幅幅撼人心魄的作品出世了——《在海滩上奔跑的少女》、《海边人家》、《泉边的女人》、《两个裸妇》、《读信》、《潘恩的竖笛》等。那丰满、壮实的巨大形体,那沉重地压在大地上的雕塑般的架构,充溢着蓬蓬勃勃的不可一世的生命力。
那劲健富丽的线条,构筑了形体的动态美。毕加索仿佛回到了意大利,回到了古罗马,他正在全身心地聆听古典大师的启示,他似乎发现了上帝的藏身之处。
面对着千变万化的世界,面对着追求时髦的美术界同事们的各种好奇心和虚荣心,毕加索仍然保持着自己的个性。他一方面以清醒的头脑看待各种新的文艺思想,另一方面不停地探索古典主义艺术宝库,继续从中汲取有价值的、宝贵的营养。
在20世纪20年代的毕加索作品中明显地体现出古典主义、立体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的高度结合。由于他坚持了自己的创作方向,他的绘画、版画和雕刻又有了新的发展。同当时艺术界的空虚、混乱和无所建树相反,毕加索在这一时期的作品显示了他的艺术的强大而持久的生命力。
在整个20年代,在巴黎和欧美各国的首都和其他大城市,先后举办过多次毕加索作品展览,这些展览表现出毕加索艺术创作的重大成果及其深远影响。因为毕加索画展举办之处,无不受到美术界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他那富有成果的作品犹如荒野上独放的鲜花,得到了人们的赞赏。
在这些作品中,那套名为《母与子》的连环画很重要。它表现了毕加索热爱生活、热爱和平、热爱自由的思想感情,表现出画家的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
在毕加索的形形色色和千变万化的图画、雕塑中,潜含着极其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促使毕加索关心在街头流浪的艺术,在外国各地漂泊露宿的朋友。
他的画笔不间断地描绘千千万万遭受苦难的人们的生活景象,绘声绘色地表现出他们的感情和意志,也强有力地表达出他们的控诉和抗议。正是这些宝贵的精神,使毕加索始终不停留在一点上,不断探索和创造,使他的艺术活动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