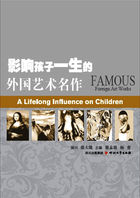对于城市意象的理解,我们不能停留在意象概念的界定与区分上,而应该深入意象的功能,探讨其在电视剧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城市意象的描述性功能
根据西方社会学家的区分,文化分为“大传统”与“小传统”余英时,内在超越之路,。“大传统”为上层社会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是社会的主流文化,它的背景是国家主流权力对意识形态的干预,所以,它常常以权力的面貌出现;“小传统”则是指民间流行的通俗文化传统,是社会的边缘文化,它的背景往往是远离国家控制或国家控制力薄弱的边缘地带。确实,中国电视文化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大多表现出“大传统”的总倾向,这与中国“文以载道”的文艺观有关,同时也与文艺实现现代化的历史情境密切相连。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制度性改革,加上电视剧作为当代中国“第一”叙事艺术体现了家庭通俗艺术的基本传统这一特性,都市日常生活空间由此逐渐成为电视文化的主要表达方式之一。在当代电视剧中,胡同、里弄、大杂院、筒子楼等城市意象空间成了创作家表现的重要对象。意象“是诗人主观印象、感觉亦即主观情思对客观具象的能动的胶合”由此可知,意象具有客观性特征和对外部世界的再现性因素。而这种客观性与再现性,就得之于意象的描述性功能。
中国经济的发展促成了中国市民阶层的崛起,同时也带来了日常生活叙事在中国当代电视剧中的兴盛。一部分电视剧开始从平民日常生活立场出发,采用民间叙事话语来界定日常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希望通过“讲述老百姓的故事”来表现中国社会的文化变迁以及普通平民的生存状态与精神境况。导演黄建新说得好,“每个人的行为、心理都是文化的反映,文化的根就在现在,就在每个人身上”。导演英达说:“情景喜剧是有它独有的规律和机制的,并不能依靠灵感在某一时间的突然到来……我有很多剧的蓝本是从国外刨过来的,但我得花很大工夫把它本土化,我得让它‘低’点,再‘低’点。老百姓才能懂,会笑。”这种将创作主体等同于老百姓的民间写作立场,其实就决定了影视艺术家们逐步弱化了精英主义的启蒙立场以及国家政治的宏大叙事观,将视角转向对个体的、现实主义的、世俗的生活追求上。日常生活并不需要依靠外在的思想拯救,它的价值不在任何理想化的超越之中,而是在于世俗性的日常本身: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柴米油盐、家庭人伦……这些烦琐的世俗性细节在现实生活中是无从缩减和省略的,它们构成了民间生存的个体赖以生存的基本形式。用阿格妮丝·赫勒的话来说,人在日常生活中具有“个人实用主义”的特征。这个“个人实用主义”不是哲学上的“实用主义”概念,它是人的“自在的”、类本质的表现,是人性的一部分。《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以出生在北京古旧胡同里的一个众生云集的大杂院为生活舞台,将张大民一家三代十几口人的生活与生存状态细腻地展示了出来。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狭小、僻陋得可以称得上是寒酸的生存居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里似乎没有任何私密的物和事可以保留,有的只是婚丧嫁娶,祸福凶吉,乃至柴米油盐、锅碗瓢盆等物化世界与精神生活的资源共享。在这种日常叙事中,《渴望》、《大哥》、《结婚一年间》、《孽债》、《儿女情长》、《婆婆媳妇小姑》、《田教授家的二十八个保姆》等剧作,表现的大都是普通市民生活中的家长里短、婆婆妈妈的日常琐事,诸如“姑嫂之争”、“邻里计较”,而正是这些日常琐事才真正构成了市民阶层的最真实记忆。英达导演的《我爱我家》、《中国餐馆》、《闲人马大姐》情景喜剧的风格非常贴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许多题材都取自老百姓的家长里短。这些电视剧以普通平民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琐事、小事为切入点,着重于贴近生活、反映生活,展现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世界,丰富了平民生活的日常表达。
知识精英“大写的人”的价值话语往往具有抽象性和概念化的特性,与之相比,自然滋长的平民精神则富有鲜活的人性血肉。在自足自律的日常生活空间里,人既不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符号,也不再接受启蒙话语的诱导与教化,人的生存是一种出于自然人性、自生自为的生存状态,这种生存状态蕴涵着踏实柔韧的世俗生存精神以及在平凡而艰辛的岁月中建立起来的普通而又深沉的情感。近年的一些电视剧中,就有不少作品在自觉地发掘着这种本真的民间精神元气。如电视剧《一地鸡毛》、《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以朴实的风格、平淡的节奏显示出普通市民日常的人生、日常的体验、日常的欢乐和痛苦。《大哥》承袭了《渴望》、《儿女情长》、《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平民剧一贯表现出的平民心态:承受、容忍和期待。这既是下层小人物的一种无奈选择,也是长期以来养成的生活韧性的体现。在物欲横流、心态失衡的现代社会,大哥不嫉妒、不贪婪,凭借辛勤努力,安享自己一份困窘而自尊的生活,将生命的意义放置在日常生活中,细细咀嚼休戚与共、相濡以沫的亲情和爱情,使平凡的生活呈现出温馨的亮色。诚如导演王栋、潘明光在导演阐述中所说,把视点聚焦在一个普通家庭,用一个个我们身边的故事反映当今社会伦理道德建设的迫切性。《我爱我家》中表现的完全是一个典型北京社区中的环境,鳞次栉比的居民住宅,楼下小区公园内的长凳、路灯,居委会的活动,晚上下棋的老头和拿着扇子乘凉的人,还有“我家”内的家具摆设,都留下了那个时代深深的烙印。这种社区生活让人充满了归属感、认同感和安全感。荧屏上那些熟悉的场景和同样稔熟的语言,都让观众感到无比的舒心和放松,观众也因为了解而喜爱,因为相似而兴趣盎然。平民题材的电视剧向观众传达着这样的信息:挫折、失败、苦难、灾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对生活的热爱,失去乐观向上的心态。热爱生活,这是浪漫的必备条件。只有乐观,才能实现对现实的超越,才会真实、具体和丰富,才能品味出生活中的浪漫。正如别林斯基所说:“每个民族都有两种哲理:一类是学究式的、书本的、郑重其事的、节庆才有的;另一类是日常的、家庭的、习见的,这两种哲理通常在某种程度上彼此接近,只要谁想描写一个社会,他就必须认识这两种哲理,尤其是必须研究后一种。”
二、城市意象的拟情性功能
其实,中国古人已认识到意象的主体性特点。刘熙载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雅人深致,正在借景言情,若舍景不言,不过曰春往冬来耳,有何意味?”如果将“情”赤裸裸地抒发出来,便容易令读者味同嚼蜡,美感丧失殆尽。因此,“借景言情”成为文艺美学的一条基本原则。黑格尔指出:“在艺术里,感性的东西是经过心灵化了,而心灵的东西也借感性化而显现出来了。”黑格尔认识到了审美过程中“心灵的东西”与“感性的东西”的辩证统一关系。所谓“心灵的东西”,就是经过理性思考的认识成果,而“感性的东西”,就是艺术家本人在审美活动中产生的审美情感,心灵的东西和感性的东西共同构成了意象的审美本质。
拟情性,也就是用拟人、比兴等手法将抽象的、不可见的情感具象化。它的作用是对情感进行化解、阐释,然后呈现可感、可触的景象与画面,化虚为实,化情为景,使不可捉摸的情感变得有声有形、有光有色,正如艾略特所说的:“艺术形式里表达情感的唯一方法是找到一种‘客观对应物’。”意象的创造源于创作者对客观世界独到深刻的认识、对自身情感的深沉体验和强烈感受,更源于对人类文化因子的广泛认同和诗性表达。因为人类的情感是一种丰富复杂的内在心理活动,要将其较真实地传达给别人,只凭单纯抽象的某些概念表述是不可能的,所以创作者在创作时往往运用具体可见的自然物解释抽象的情,最终使自己的内在情感为观众所体验。
每座城市都拥有本属于它的一方水土,自然环境特征往往是城市意象不可割舍的组成部分。在城市的历史进程中,人类总是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在满足必要的城市物质功能的前提下,利用它固有的地形地貌,创造出独特的城市意象。乌镇地处浙北,京杭大运河绕镇而行,镇内河网密布、港汊纵横。千百年来,民居临河而建,傍桥而市,迤洒千余米的古帮岸、水阁和廊棚,透出水乡的悠悠韵味,形成了典型的江南水乡风情。乌镇自古繁华,民风质朴,桐乡拳船、花鼓戏、皮影戏、香市等独特的民俗风情体现了当地浓郁的水乡情怀。此地钟灵毓秀,人才辈出。自梁昭明太子筑馆读书于此,至近代文学大师茅盾,留下了众多的人文胜迹。丽江的一切城市生活都融入了属于它的山山水水之中。“小桥、流水、青石板街道”、“沿河、依山、临街的建筑”、“迷宫式的巷弄……”构成了人们对丽江的记忆和意象,这也是它因借山水而天人合一的佐证。丽江古城充斥着来来往往、分分合合,每天都有故事在这里发生,有的延续了,有的随着丽江水流逝,但是玉龙雪山金顶的一米阳光可以作证,有一对男女用生命在这里镌刻爱情。电视剧《一米阳光》就发生在这秀美的丽江古城,在这纯洁的雪山之下,爱的山盟海誓将在今后平凡琐碎的生活中定格,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风浪,都能处变不惊,两手相携一直到天荒地老。如今,丽江不仅成为旅游胜地,也令不少影视剧要把它的美丽收入镜头里,特别是那些与丽江风情非常和谐的影视剧,如《玉观音》、《相思树》,张艺谋《印象·丽江》等影视剧。而杭州西湖更是一首诗、一幅天然图画、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不论是多年居住在这里的人还是匆匆而过的旅人,无不为这天下无双的美景所倾倒。阳春三月,草长莺飞。苏白两堤,桃柳夹岸。两边是水波潋滟,游船点点,远处是山色空蒙,青黛含翠。而《白蛇传》中那许仙和白娘子发生在西湖边上的传奇爱情故事更成了后来影视剧作家不断改编的经典,另外还有《一帘幽梦》、《地下铁》、《桂花雨》也都与西湖有关。
朱光潜在《诗论》中曾说过:“情景相生而且相契合无间,情恰能称景,景也恰能传情,这便是诗的境界。每个诗的境界都必有情趣(feeling)和意象(image)两个要素。”意象是作者主观情感和客观事物的互相融合,只有情和景的融合互渗才能开辟出诗的境界。电视连续剧《康定情歌》故事发生在藏族康定地区,在辽阔的蓝天、碧绿的草原、纯净的雪山、清澈的湖水等美景的衬托下,为观众娓娓道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几个家族、几对男女之间的恩怨和情感纠葛,让人不知不觉沉醉在这传奇迷人的故事中。一首民歌引出一个爱情幻想,一片草原发生一段传奇故事……《滇西往事》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滇西为背景,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引领滇西民众保家卫国的抗战故事,重点表现了普通民众在特定历史时期成为英雄群体的传奇经历,中间穿插了多国间谍之间的斗智斗勇、生死拼杀,辅以滇西秀美的自然风光,力图唤起一段直指心灵的战争记忆。“中国人遵循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很早就养成对自然景物的敏感,常常体验着自然物象的人间意义和诗学情趣。”自然意象常点缀在各种富有情感和含义的电视剧文本中。
三、城市意象的象征功能
城市意象表述功能的第三层次是意象的指意性,也即象征性。苏珊·朗格指出:“意象真正的功用是:它可作为抽象之物,可作为象征,即思想的荷载物。”“一个意象可以被转换成一个隐喻一次,但如果它作为呈现与再现不断重复,那就变成了一个象征,甚至是一个象征(或者神话)系统的一部分。”美国人类学家怀特认为:“人类行为是象征行为”,“象征是所有人类行为和文明的基本单位”。可见象征应用之广。他又说:“象征可以定义为一件其价值和意义由使用它的人加诸其上的东西。”也即象征是借助具体的“象”来表征意义的,具有指意性,既有本身所指,同时又有更广的指代意义。象征是被选出来表现某种抽象意义的具体事物,象征意象在中外诗歌创作中往往把思想隐藏在具体的物象背后,使其平中见奇、含而不露,并能使意义得到再生和扩大,使平常的物象焕发出异常的色彩。同样,在中国电视剧艺术建构过程中,象征也是艺术家对存在世界的艺术化发现,是将其内心世界进行隐秘呈示的独特方式。
1.符号象征与表意
城市是由各种都市符号组成的。在符号哲学代表恩斯特·卡西尔看来,整个人类都是“符号的动物”。黑格尔曾指出:“建筑一般只能用外在环境中的东西去暗示已经被移植到他里面去的意义。——所以这种建筑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表现形式上都是地道的象征艺术。”同时,黑格尔认为显证包含两个因素:“第一是意义,其次是意义的表现。”他还指出:“意义就是一种观念或对象,不管它的内容是什么,表现是一种感性存在或一种形象。”
电视剧《空镜子》(2001年),导演:杨亚洲。白塔是一个有着古老历史和文化传统的现代城市的标记。一般来说,展现真实生活的影视剧,都比较注重生活流和生活场景的描写,特别是剧中人物所处的客观环境的纪录式的视觉展现,如用大远景、鸟瞰式地交代大环境,用全景、中景描述具体环境和时代特色,然后再进入人物的生活空间……电视剧《空镜子》讲述的是发生在当代真实环境中的故事,是一个现实主义题材,但是创作者对外部大的环境关系和时代特色的交代,却运用了一种符号化的处理方式——虚化处理,这也是该剧的一大特色。在片中,观众对主人公孙燕家外景的认识就是那个伫立的白塔,还有一条车来车往的、路边有明显白色栏杆的、市内的拥挤街道。对于他们生活的城市的印象就是夕阳、暖冬、广告还有灯光如织的城市夜景。那个像见证人似的静静的白塔,是一个有着古老历史和文化传统的现代城市的标记,它象征着传统文化、道德与价值观念。这个象征标记的反复出现,表现了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念与现代物质世界中的现实生活逻辑的差异。还有经常出现的残枝斜阳和广告牌,这些景观都是可以在城市里经常看到的,但是这些影像的反复出现就不再是承担介绍环境的作用,而是一种人生体验感悟和生命哲理阐释的视觉外化。这种虚化的、符号化的对外部现实环境的处理有着主题和节奏上的考虑:在主题方面,近景系列的美学含义是十分主观化的处理,强调的是情感的表露,而全剧没有留下理性思考的空间是不行的,这些符号的出现在客观上除了能够代表一定的时间进程以外,主要是意象化的处理,从一种浸入式的审美中剥离出一块理性思考的生存空间;在节奏方面,这些符号式的影像与表现人物的知觉认识产生了落差,形成了镜语的对比和反差。
室内电视剧《半边楼》对西安及城市风貌的直接描写并不多,但我们依然可以清楚地感觉到那种熟悉的味道,有五个家庭居住的半边楼完全可以看成是西安这座城市的微缩图景。半边楼是辉煌的,因为里面居住的绝大多数是高级知识分子,是这个时代的精英,这种辉煌不是表面的光鲜,而是内心的充实和自豪。半边楼是厚重的,尽管也有过矛盾和苦恼,但在面临取舍的时候,无论老年、中年还是青年人,他们都有一股义无反顾的大气。如果说某一个人这样做是和他的修养有关,那么大多数人都这样做,似乎就应该将他们和他们生活的环境联系起来思考,因为城市给了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潜移默化的熏陶和教化。但半边楼确实是暗淡的,因为是“拆了一半的半边楼,还有一半就拆到了头”。嘈杂的环境、拥挤的过道、艰苦的生活条件、略带灰暗的光线、狭小的书桌、残旧的炉子……这些无一不在告诉观众半边楼的暗淡,甚至是破败。与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比较,半边楼确实已经落伍了。与光鲜亮丽的色彩比较,半边楼显得有些灰头土脸。半边楼还是萎缩的,不仅仅在于它的一半已经拆掉,而剩下的这一半也快拆掉了,更是体现在居住其中的人身上。范耘和黄耕的黄昏恋,让观众渴盼但也一步步为其揪心和叹息;呼延也是在经历了诸多曲折之后,才接受了何娜对他的真情。保守、胆小粘贴在人物身上,要用很大力气才能摆脱得掉。有人说,这是知识分子的通病,但也许可以这样认为,在这座城市里这种通病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人生活在城中,城的性格会折射在人身上。剧作家对这座楼、这座城进行了仔细观察和描摹,也给予了无限的期待,剧中多次出现的雪景,不由得让人们联想到“瑞雪兆丰年”,还有“冬天已经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2.从符号的分类看城市形态的象征性
近代符号学权威索绪尔认为应该把事物和其名称分开。各种符号系统虽然采用的手段不同(如声音、光线、颜色、气味、姿势等),复杂程度不同,但其目的相同,都是为了传递信息。无论是用简单的手段还是复杂的手段,传递简单的信息还是复杂的信息,交际结构的基本单位都是符号。一切符号都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部分是标记,即索绪尔所说的“符征”;另一部分是指称对象,即索绪尔所说的“符旨”,指称对象是标记代表的真实事物。
一切符号之所以能传递信息是因为它们与意义相联系。意义是符号的内涵,是符号在使用该系统的人的头脑中激发的概念。皮尔斯的分类方法比索绪尔精细,他提出三种分类方法:其一,按符号本身性质,可分为性质符号、实事符号和通用符号;其二,按符号同其对象的关系,可分为图形符号、标志符号、象征符号;其三,按符号在解释活动中的状态,可分为词类符号、命题符号和论辩符号。
就城市形态符号而言,采用皮尔斯的第二种分类方法更能够对城市形态符码加以分析。美国艺术史学者米切尔森对此做了以下解说:
图像:图像是使对象有意义的符号,这是它的特性,因此形态相像是图像的最基本特征,相像的形象就属于图像。图像存在相似程度的高低之分。
标志:标志是代表无题的或可见对象的特征的符号,如果它所标志的对象不在了,它便丧失了符号特征。
象征:如果说图像是通过相似与对象关联,标志是通过物理性质与对象关联,那么象征是通过从事象征的心灵的观念与对象关联。
为了进一步说明,我们还可以引用英国学者奥格登和瑞恰滋的观点。他们的观点对符号学理论影响最大的是“语义三角”。很显然,奥格登和瑞恰滋对索绪尔的观点做了修正,强调象征与思想内容之间存在的实质关系,思想内容和指涉物之间也是同样的,因此用实线相连,但在象征和指涉物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关系,故用虚线表示。如下图所示。
奥格登和瑞恰滋的“语义三角”模型表明,所指与事物之间要以能指为中介,它们并没有直接联系,正是在这里蕴涵着话语建构的多种可能。《大清徽商》、《大祠堂》、《徽娘宛心》中的牌坊、祠堂、古桥等孕育着徽州文化中所包含的拼搏奋进、百折不挠、吃苦耐劳的“徽骆驼”精神;山高水深、钟灵毓秀的山东文化源远流长,孔子的学说泽被中国文化数千年;《大染坊》里的陈寿亭目不识丁却聪明机智,他之所以能在尔虞我诈的商场中游刃有余、出奇制胜,靠的就是齐鲁文化中最珍贵的主动创造性;《尘埃落定》中藏区的高原湖泊、蓝天白雪以及天葬水葬等原汁原味的异域风情和神秘的宗教氛围向世人展示了藏族文明和文化的变迁……中国电视剧对地域文化的凝练和升华,超越了浮光掠影般的表象展现,渗透到情节演进中,成为烘托环境、强化叙事效果的深刻因素,而且渗透到人物性格中,成为感染观众、主导全剧的隐性因子。也正是对这些具有象征和标志性的地域文化的生动性表述和阐释,使剧作具有深沉的文化意蕴和文化品格。
同样,如果把城市意象要表达的概念设定为“现代化”,那么表达现代化的可以有高层建筑、地铁、高速公路等多种符号,城市建构就可以从这些能指系列中选取合适的词语。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广东电视连续剧先后出现了《公关小姐》、《商界》、《外来妹》、《情满珠江》、《英雄无悔》和《和平年代》,这些激动着亿万群众心灵的现代题材剧目,都是反映广东地区改革开放、新人新事、价值冲突和社会问题的故事。鲜明的时代气息和地方特色,激烈的矛盾冲突和丰富的人生百态,成为广州吸引全国观众的原因。与此同时,有关广州的一系列标志性城市形象也陆续出现在当代荧屏上,如珠江两岸、西关风情、天河体育中心、中信广场、珠江新城。具有广东地区特色的电视剧《永不瞑目》、《浮华背后》、《义假情真》、《功夫足球》也一次次赢得了观众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