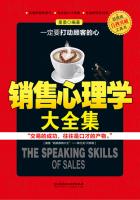“我的生活从来不是由我自己而是由历史进程决定的。”阿尔弗里德·克虏伯这样评论自己的命运,他把一个人弄到自己身边,这个人不应该是历史的牺牲品,而是历史的创造者。
所有参与克虏伯公司及康采恩命运的人,总是羡慕阿尔弗里德·克虏伯和贝托尔特·拜茨这一对搭挡。1961年,《探索》杂志认为:“克虏伯——拜茨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很好的小说题材。”“他们两个人实在太不同了。克虏伯几乎是一个悲剧性人物,他是一个懦弱的继承人,他继承了一个已历五代的沉重的传统。他生性腼腆,而他所受的教育又过于严格,有点类似一个王储所受的教育,两次婚姻都失败了,他因在纳粹时期的恶劣行为(他主要是象征性地应对此负责),蹲过6年监狱,他知道,他的几百万同胞都带着仇恨的目光看他,所有这一切都加重了他的羞怯,他深居简出,很敏感,他已经习惯了被伤害,但他太骄傲了,以至于他不会还击,他喜欢独自坐在他的唱机旁,听巴赫的音乐。拜茨是人民的一个坚强的孩子,他白手起家,有一种几乎不可阻挡的自信,他外向,感情奔放,他喜欢开玩笑,喜欢斗争,热衷于与人建立密切的个人关系,这些对他的上司(阿尔弗里德)都是最讨厌的事。他很直截了当、粗鲁,有时候举止失礼,令人震惊,有时候又心肠好得令人感动,落落大方,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他们两个人的不同点还可以继续列下去。拜茨有幸福的婚姻,阿尔弗里德则没有。拜茨喜欢在公众面前表现自己,阿尔弗里德认为那是沉重的义务。拜茨追求社会的承认,阿尔弗里德自然地拥有了社会的承认,这对他什么意思都没有。
在评价他们自己的成果时,他们也用不同的标尺来衡量。拜茨衡量的标准是看得见的成功,是在公众中的荣誉。
这给他自信和社会地位,把他从压力中解放出来。这对阿尔弗里德没有任何意义。他衡量自己成就的标尺是满足公司和传统向他提出的要求,只有这个算数,其它所有的东西与这相比,都毫无意义。
阿尔弗里德不会表达自己的感情。贝托尔特·拜茨则从不害怕表示感情。为庆祝他70岁寿辰,拍摄了一部电视片。他让人拍摄了一个场景:他把从卡姆盆亲手采摘的杜鹃花放到阿尔弗里德坟前,这不仅表达了他对阿尔弗里德的敬意,同时也表达了对北海济耳特岛的热爱,济耳特岛是他们两个人都喜欢的地方。但这个举动在阿尔弗里德那里是无法想象的。
许多人把这种不同点看作矛盾。我认为这更是一种补充,一枚金牌的正反面,一只双头鹰,双面肖像。这两个人中每一个人都是那种另一个人不是的人,每个人都有另一个人所没有的性格。这种格局可以使他们成为敌人或者成为朋友。因为阿尔弗里德想要友谊,他们成了朋友;他们两个一起是一个整体,他们共同使天平保持平衡。
“我知道,阿尔弗里德·克虏伯对贝托尔特·拜茨怀有极大的信任,这从许多角度看都是重要的,有道理的。”赫尔曼·约瑟夫·阿波斯在写给我的信中,就是这样确定这两个男人之间的友谊基础。“阿尔弗里德的本性使他在所有谈判中都非常拘谨,他所有的愿望就是,能够代替他的父亲完成他应完成的任务,即在战后发生巨大的政治困难的情况下,在经历过财产的没收和充公之后,保护他得到的遗产。与此相反,贝托尔特·拜茨有一种勇往直前、积极进取的精神,这经常给他力量,使他能够大胆地战胜一切困难。我曾经把他们俩的性格对比了一下,然后加在一起,除以二。这两位先生有多方面的性格……正好100,并且永远都很多。”后来,阿尔弗里德不愿再全部承担他对公司的那部分重担,这时,他破坏了这种平衡。阿恩特认为:“他回到了自己的世界,他喜欢寂寞,不喜欢周围有任何人。”不久,贝托尔特·拜茨就几乎成了他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纽带。拜茨没有阻止这种发展势态,他坚决否认,曾经推动它的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发展迅速扩大了他的权力基础。
阿尔弗里德从日常工作中退了出来,拜茨把缰绳紧紧地抓在了自己手里。阿尔弗里德自愿地往后台退得越深,拜茨获得的地盘越多。两个人的统治变成了一个人的独裁。
现在,拜茨独自统治克虏伯已经20多年了。他仍然没有把公司的事情安排停当,这个公司情况并不特别好,应该进行改革,进行彻底更新。因为,克虏伯早就存在的弱点仍然困扰着它:它供应的产品品种过于繁多,它的效率和组织仍有问题,亏损企业比例过高,特别是,康采恩的效益不令人满意,自有资本太少,这一问题福格桑早在1967年就指出来了,但他又没有机会解决这个问题。
但谁应该改变这一切呢?难道不应该由一个新人来做吗?经常有人向贝托尔特·拜茨提出这个问题,公开地或私下里,直接地或间接地。他反击了,讽刺说:“每个人都问我,我身体好吗?他们希望我回答:不好。但我总是回答,我重76公斤,我很健康,我还能去打猎。我觉得我处于最佳状态”。然后,他又不由自主地想到,他自己年轻时候的感觉,他想了想,“我原来是这样想的,他都75岁了,他应该走了。但我觉得我有责任,执行阿尔弗里德的愿望。”在我们上一次谈话中,我也向他提出了这个必问的问题,他是否愿意从克虏伯公司的领导职位上退下来。是的,他说,他原则上是想退下来,他谨慎地说,因为,与所有其他人一样,他也有一些退休以后的打算。但在这之前还得把一些事情处理好。
他说:“特别是董事会、总公司监事会和基金会理事会的人员要适应未来的要求。”他认为,这方面的工作是他的责任,在最近一段时间,他没有可能推卸。
“第二个更重要的工作是寻找一个机会,使克虏伯能够有必要的资金活动余地,这对未来的事业是必要的。”紧跟着问:“您是指要转变成股份公司?”他微笑,“这是您说的。”’
但他也不反驳。这个谜的谜底只能留待读者去想象。
另外,他还想确定克虏伯的正确发展方向,使克虏伯为1992年、为欧共体统一大市场做好准备。他已经开始对康采恩进行必要的组织更新。他参阅克虏伯1987年与麦克·
金塞共同制定的新方案,这个方案应该对康采恩进行改组。
这是继他与阿尔弗里德共同制定的组织结构计划之后的第二次尝试,这意味着,要废除旧的中央集权的结构,建立分权组织。他如何评价自己最近20年在康采恩中的作用?
“我努力坚持并发扬克虏伯公司以社会福利为特色的企业管理传统。”他解释,“我试图把对阿尔弗里德的怀念具体化。如果我不在的话,没有人会比我做得更多。”我问他,现在克虏伯在联邦德国大公司排行榜中仅占第23位,他是否认为这是一种失败,他反对这种说法。克虏伯难道已经开始微不足道了吗?不,他不这样看。克虏伯是第一大公司的时代,也是整个重工业位列前茅的时代。
目前,一些行业如化学工业和汽车制造业已经占据了领导地位,克虏伯目前正在解决一个混合康采恩的一些典型问题。
1988年9月26日,贝托尔特·拜茨75岁了。他老了,但他在权力面前一点都不觉得累,这样就无法对他在克虏伯的作用做定论。让我们看这个画面:阿尔弗里德和拜茨一起,是整整100分。而拜茨一个人则是:100分,除以二。
这到底是多少,历史将会证明,最后的裁决仍需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