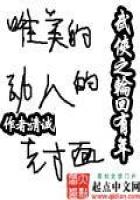释李辅光墓志铭中“旌宠殊勋”
崔元略《唐故兴元元从、正议大夫、行内侍省内侍、知省事、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特进、左武卫大将军李公墓志铭(并序)》云:“公讳辅光,字君肃,其先京兆泾阳人也又属太原军帅李自良薨于镇,监军使王定远为乱兵所害,甲士十万,露刃相守,公驰命安抚,下车乃定,便充监军使。前后三易节制,军府晏如。十五年间,去由始至。遂特恩遥授内给事,又有金章紫绶之赐。元和初,皇帝践祚,旌宠殊勋,复迁内常侍兼供奉官。”
此志中“旌宠殊勋”四字,非寻常谀墓之词,实永贞内禅之重要史料。韩愈《顺宗实录》卷四云:“(贞元二十一年六月)癸丑,韦皋上表请皇太子监国,又上皇太子笺。寻而裴均、严绶表继至,悉与皋同。”时韦皋为剑南西川节度使,裴均为荆南节度使,严绶为河东节度使,三镇相距遥远,缘何不约而同?肯定幕后有操纵者。
据《旧唐书?德宗纪下》,贞元十一年五月河东节度使李自良卒后,继任者为李说、郑儋、严绶。崔元略所云“前后三易节制”指此。同书《裴传》云:“严绶在太原,其政事一出监军李辅光,绶但拱手而已。”贞元二十一年六月严绶请皇太子监国疑亦拱手听命于李辅光,但无显文露书,揭发其事,李辅光墓志“旌宠殊勋”四字,等于不打自招。
李淳(纯)已立为皇太子,是唐顺宗的合法继承人,如果确因顺宗患病,权由李纯监国,别无政治目的,乃是名正言顺之事,何须严绶远道上表?如果严绶上表,是出于己意,怎能把功劳归之于李辅光?既然崔元略以“殊勋”颂扬李辅光,表明幕前是严绶上表,幕后是李辅光操纵。否则李辅光无“殊勋”可言。
崔元略自诩投靠李辅光,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说:“(李辅光)门吏晋州司法参军巨雅,以元略长兄,尝宾于北府,以元略又从事中都,俱饱内侍之德,将命录实,见托为志,勒之贞石,且无愧词。”他声明李辅光墓志是录实,那么志中所云李辅光操纵严绶上表请皇太子监国的“殊勋”,是无可怀疑的了。
章士钊将拙文载入《柳文指要》,并云:“如此觅证,在逻辑谓之钢叉论法,百不失一。孝萱既从联锁中获得良证,而吾于子厚所云外连强暴之一大疑团,立为销蚀无余,诚不得谓非一大快事。”
释西门珍墓志铭中“密近翼戴之绩”
西门元佐《大唐故朝议郎、行宫闱令、充威远军监军、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西门大夫墓志铭(并序)》云:“公讳珍,京兆云阳人也,至德之初,释褐从仕顺宗嗣位,爰选耆德,以辅储皇,转为少阳院五品。永贞元年,属今上龙飞,公以密近翼戴之绩,赐紫金鱼袋,充会仙院使。元和元年,改充十王宅使。”
此志中“密近翼戴之绩”六字,亦非寻常谀墓之词,与李辅光墓志铭中“旌宠殊勋”四字,均为永贞内禅之重要史料。
据《顺宗实录》卷四:“外有韦皋、裴均、严绶等笺表,而中官刘光奇、俱文珍、薛盈珍、尚演、解玉等皆先朝任使旧人,同心怨猜,屡以启上,”西门珍于至德初已从仕,经历肃、代、德三朝,至顺宗时,足称“耆”。他不仅与刘光奇等俱为“先朝任使旧人”,又居皇太子身边,在永贞内禅事件中,是重要的角色。《顺宗实录》中没有提到西门珍,不意味着西门珍对永贞内禅未起作用。所谓“屡以启上”者,实际是刘光奇等逼迫顺宗让位给太子,这只是顺宗的一方面。还有太子的一方面。“密近翼戴”者,说白了,就是西门珍在太子与刘光奇等之间,沟通消息,一致行动。刘光奇等与西门珍合演了这出戏,二者缺一不可。
西门元佐是西门珍之从侄。他能了解西门珍的秘事,又自诩“(西门珍子)以元佐性无饰伪,文好直词,爰命纪能,庶旌实录”。与崔元略撰李辅光墓志铭的态度相同。西门元佐颂扬西门珍对宪宗的“密近翼戴之绩”,也是“实录”,无可怀疑的。
章士钊将拙文载入《柳文指要》,并云:“在永贞逆案中增加西门珍一”,“亦自可喜”。
《顺宗实录》诋毁王叔文集团
(一)
唐贞元十九年九月,韦执谊向德宗密诉张正一朋党。现存的《顺宗实录》《旧唐书》《资治通鉴》等记载略异,先录《旧唐书?韦执谊传》:
初,贞元十九年,补阙张正一因上书言事得召见。王仲舒、韦成季、刘伯刍、裴?、常仲孺、吕洞等以尝同官相善,以正一得召见,偕往贺之。或告执谊曰:“正一等上疏论君与王叔文朋党事。”执谊信然之。因召对,奏曰:“韦成季等朋聚觊望。”德宗令金吾伺之,得其相过从饮食数度,于是尽逐成季等六七人,当时莫测其由。
再比较《旧唐书》与《顺宗实录》《通鉴》之异同:
(1)“张正一”:《顺宗实录》作张正买。据《资治通鉴考异》,从《德宗实录》,作张正一。可见《旧唐书》亦从《德宗实录》。
(2)“或告执谊”:《顺宗实录》卷五作“有与之不善者,告叔文、执谊”。《通鉴》无此句,可见《德宗实录》无此句。王叔文阻止太子向德宗言“宫市事”,认为:“太子职当侍膳问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顺宗实录》卷一)贞元末年,太子尚且“不宜言外事”,小小的“侍太子棋”王叔文,怎敢在外招摇?又怎么会有人知道王叔文与韦执谊联手?王叔文绝无向德宗密诉之可能,与张正买“不善者”“告叔文”又有什么用?《顺宗实录》加“叔文”名,非是。《通鉴》作“叔文之党疑正一言己阴事,令执谊……”,《考异》未述史源。
(3)《顺宗实录》删“德宗令金吾伺之,得其相过从饮食数度”,非是。所谓朋党,不是公开宣布的,“过从”“饮食”可视为朋党的一种迹象,故德宗认为张正一等“朋聚觊望”而逐之。白居易说过:“贞元之末,时政严急,人家不敢欢宴,朝士不敢过从,众心无,以为不可。”(《白居易集》卷六《论左降独孤朗等状》)即为明证。德宗既然侦察到张正一等“相过从饮食数度”,也就相信了韦执谊的密诉。
比较文献记载的异同之后,可以看出韩愈对韦执谊、王叔文的非常厌恶。他用“告叔文、执谊”二人是为了说明韦、王在贞元末就已联手乱政;他删去“德宗令金吾伺之”两句,是为了突出德宗不做调查而偏信韦执谊,韦执谊只手遮天。总之,是为了加重韦、王之罪恶。
(二)
《实录》中虽记载“永贞革新”的善政,却诋毁施行善政的革新派。《实录》在记“罢翰林阴阳星卜医相覆棋诸待诏三十二人”之后,紧接写“初,王叔文以棋待诏,既用事,恶其与己侪类相乱,罢之”,表示这一举措是出于私心。可是,王叔文的私心,韩愈怎能知道呢?《实录》在载顺宗授王叔文度支盐铁副使制之后,紧接写“初,叔文既专内外之政,与其党谋曰:‘判度支则国赋在手,可以厚结诸用事人,取兵士心,以固其权。’……”表示《制》中称赞王叔文“精识瑰材,寡徒少欲,质直无隐,沈深有谋,其忠也,尽致君之大方;其言也,达为政之要道:凡所询访,皆合大猷”(《顺宗实录》卷一、二)皆是虚假的。可是,王叔文与其党的私议,韩愈怎么知道的呢?这都是曲笔。《实录》虽不像《忆昨行和张十一》骂二王、韦为“三奸”,也没有像《永贞行》强加“小人乘时偷国柄”以及“董贤三公谁复惜,侯景九锡行可叹”等罪名,从《进顺宗皇帝实录表状》中自诩“忠良奸佞,莫不备书”,可见韩愈撰《实录》时仍是把王叔文等当做“奸佞”批判的。突出表现在记载王叔文集团夺宦官兵权的重大措施上。《实录》一则云:“既知内外厌毒,虑见摧败,即谋兵权,欲以自固,而人情益疑惧,不测其所为,朝夕伺候。”(《顺宗实录》卷四)再则云:“日引其党,屏人切切细语,谋夺宦者兵,以制四海之命。”(同书卷五)颠倒是非,与《水贞行》“北军百万虎与貔,天子自将非他师。一朝夺印付私党,懔懔朝士何能为”(上引韩愈诗文据《韩愈全集校注》)腔调一样。这是违心之论,是最大的曲笔,后世学者对韩愈多有批评。
《实录》中既有直笔,又有曲笔,反映出韩愈政治思想的复杂性。对《实录》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一笔抹煞,应区别其精华与糟粕。据《旧唐书?路随传》云:“韩愈撰《顺宗实录》,说禁中事颇切直,内官恶之,往往于上前言其不实,累朝有诏改修。”宦官所谓的“不实”,正是韩愈的直笔。宦官所要删削的,正是《实录》中的精华。
韩愈有大名,后世史书皆据《实录》。如《旧唐书?王叔文传论》:“执谊、叔文,乘时多僻,而欲斡运六合,斟酌万几;刘、柳诸生,逐臭市利,何狂之甚也!”《新唐书?王叔文传论》:“叔文沾沾小人,窃天下权柄”,“《春秋》书为盗无以异”。皆明显承袭《实录》而来。可见《实录》中糟粕之处的不良影响,不能忽视。
总之,从韩愈《实录》赞扬“永贞革新”的某些善政,而诋毁主持革新的人(因是小官,一向没有声望),反映出他的政治思想,既有进步性,又有保守性。
从《册府元龟》看王叔文集团正义
(一)
《册府元龟?邦计部?俸禄三》云:“唐顺宗以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制又诏停内侍郭忠政等十九人正员官俸钱。”
这条记载,不见于《顺宗实录》、新旧两《唐书》。我抄寄章士钊,他认为“颇足珍异”,载入《柳文指要》。
《顺宗实录》卷二云:“(贞元二十一年二月)旧事:宫中有要市外物,令官吏主之,与人为市,随给其直。贞元末,以宦者为使,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复行文书,置‘白望’数百人于两市并要闹坊,阅人所卖物,但称‘宫市’,即敛手付与,真伪不复可辨,无敢问所从来,其〔?与〕论价之高下者。率用百钱物买人直数千钱物,仍索进奉门户并脚价钱。将物诣市,至有空手而归者。名为‘宫市’,而实夺之上初登位,禁之。至大赦,又明禁。”罢“宫市”是王叔文集团执政时的一项善政,“永贞革新”的一项措施,与宦官斗争的一个例证,治史者多乐道之,而“诏停内侍郭忠政等十九人正员官俸钱”尚无人注意。
一举而停十九个宦官之俸钱,为中唐绝无仅有之大事,王叔文集团与宦官斗争之坚决,于此得一强证。
被停俸之十九个宦官,或与“宫市”等弊政有关。如或不然,此十九人亦必宦官中之罪大恶极、声名狼藉者。
《顺宗实录》有韦处厚本(三卷)、韩愈本。韩愈本又分详、略二本(皆五卷)。今本为韩愈本之略本。“诏停内侍郭忠政等十九人正员官俸钱”这条记载,当是《册府元龟》采自《顺宗实录》韦本或韩本之详本。
(二)
《册府元龟?内臣部五?朋党》云:“薛盈珍,宪宗时为中贵人,有权力于元和初。薛謇为代北营田水运使,善畜牧,有良马,时以赂朝权及中贵人,以族人附进,盈珍颇延誉以助之,故自泗州刺史迁福建观察使。”(同书《邦计部?交结》同)这条记载,不见于新旧两《唐书》。《旧唐书?宪宗纪下》仅云“(元和八年十一月)丁卯,以泗州刺史薛謇为福建观察使”。我将此条抄寄章士钊,他载入《柳文指要》,云:“卞孝萱勤探史迹,时具只眼。”
唐代士大夫依附宦官,本为习见之事,但这条记载,不同于寻常。薛盈珍者,与王叔文集团敌对、逼迫顺宗让位给太子之大?;薛謇者,王叔文集团骨干刘禹锡之岳父也。
据刘禹锡《唐故福建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使、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赠左散骑常侍薛公神道碑》:“初公治粟于朔陲,愚方冠惠文冠,察行马外事,聆风相厚,谓可妻也,以元女归之。明年,愚人尚书为郎,职隶计司,因白计相,召公来会府。行有日矣,遇内禅惟新,愚以缘坐左贬,间关外役,竟不克面。”可见薛謇是刘禹锡的未见过面的岳父。
从薛謇碑看出,薛謇“贞元中”至“元和十年”的官职是:代北营田水运使―殿内史―淮南军司马―泗州刺史―福建观察使。李翱《故东川节度使卢公传》云:“泗州刺史薛謇为代北水运使时,畜马四百匹,有异马不以献者。事下度支,乃使巡官往验之。未反,上迟之,使品官刘泰昕按其事。坦上陈,以为‘陛下既使有司验之,又使品官往,岂大臣不足信于品官乎?臣请先罢免。’疏三奏,上是之,遂追刘泰昕。”(《新唐书?卢坦传》《资治通鉴?唐纪五十四》元和六年四月庚午条,均载其事)薛謇当时以“良马”赂朝权及宦官,是他后来被劾不以“异马”上献的根由。
薛謇以女婿刘禹锡之累,本不为唐宪宗及宦官之所喜,然“附进”于薛盈珍,竟得其“助”,不但不受元和六年被劾不上献异马之影响,元和八年还能升官,擢至福建观察使。倘刘禹锡因薛謇以附于薛盈珍,则亦未尝不能复用,然而终宪宗之世,刘未离谪籍,其不附宦官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