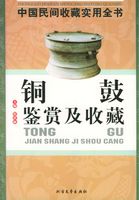羊年谈“洋”,顺理成章;羊年谈“土”,不合时调。我这里抬出的三位大爷,虽说几十年来一直被视作鼓吹“洋腔洋调”的洋老爷;可我横过来竖过去看他们,却个个都是可敬可爱,毕其一生在中国这块贫瘠的黄土地上播撒乐种的“土”老头。
几年前,在上海音乐学院郁郁葱葱的草坪上,竖了尊铜像——那是1927年创办学校的萧友梅博士。在中国,竖铜像可是件非同小可的事。因为这么一竖,不是将这位鼓吹“洋乐”的“洋博士”,连同他那“唯西洋是崇”的“学院派堡垒”都给一块儿竖起来了吗?
最近读了新出版的《萧友梅音乐文集》,白纸黑字皆为证。心中不禁怦然跳出三个字:“冤枉啊!”
且不说这位在辛亥革命前就参加了同盟会、担任过孙中山的秘书的萧友梅,是如何含辛茹苦地创建这中国第一所音乐学院和如何呕心沥血地办校——临终前还在关心学生琴房漏风的窗户是否封好……就以他的论著而言,也足以昭揭其振兴中华新乐之心迹了!早在1916年学生时代,他向莱比锡大学哲学系提交的博士论文就是洋洋九万言的《17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历史的研究》。即使在七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也还没见过有第二部如此系统地论述我国古代乐器史的专著。他多次提出学西乐不是“以夷变夏”,不是要“我们同胞做巴哈、莫扎特、贝多芬的干儿”,而是要“学得其法,借以参考”,创造出一种足以代表中华民族的特色而与其他各民族音乐有分别的“国民乐派”。对于“旧乐”,他一方面充分重视,亲自讲授“旧乐沿革”,并规定本科每人都要兼学一件民族乐器;同时,又主张“采取其精英,剔去其渣滓,并且用新形式表出之。”真是先驱者的真知灼见呀!
1930年5月26日晚,在上海美国妇女俱乐部举行的国立音专第一届学生音乐会的节目单上,有一档令人注目的节目,那就是丁善德的琵琶独奏《五三纪念》。演出后,《时事新报》对他的评论是:“悲歌慷慨,感人良深”。人所皆知,丁善德是气势磅礴的《长征》交响乐的作者,殊不知这位八十年前出生在昆山小城里的老爷子,在投考音专时的专业竟是琵琶、三弦和笛子,是被萧友梅伯乐识马,破格录取,后来才转了钢琴主科的。1935年,丁善德在举行钢琴独奏毕业音乐会时,节目单上唯一的中国曲目是贺绿汀的《牧童短笛》和《摇篮曲》。这件事对他的触动很大。他强烈地意识到:“中国应该有自己的钢琴作品。”于是,他变卖了自己心爱的钢琴,到巴黎去学习作曲。回国后,创作了一系列既有新颖的音乐语汇、又有浓郁的民族风格的好作品。“土→洋→土”的两次飞跃,使他鸟枪换炮,一身新装!
贺绿汀是中国音乐界第一号倔老头,也是第一号“洋靶子”。可谁也否认不了,中国最著名的钢琴曲、1934年就荣获“中国风味钢琴曲”首奖的《牧童短笛》就是他写的。他见势不趋,见威不惕,你骂你的“洋”,我照样竖萧友梅的铜像!对于比他小一岁的恩师黄自,更是赞不绝口:“他是系统地、全面地向国内学子传授欧美近代专业作曲理论,并且有着建立中国民族乐派的抱负的音乐教育家。”他还列举了黄自创作的两个“第一”:中国第一部交响乐作品《怀旧》和第一首抗日救亡合唱曲《抗敌歌》……你看,这老头儿有多可爱!
1956年全国音乐周期间,毛主席找了贺绿汀、马思聪、吕骥等少数几个音乐界的头头,畅谈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当时贺老就坐在主席身畔,他亲耳听到主席有关中西关系的两个精到的创见——“西医学中医”和“使两个半瓶醋变成两个一瓶醋”。主席还满腔热情地说:“你们是学西洋的东西,是‘西医’,是宝贝,要重视你们,依靠你们。请吹鼓手来办音乐专门学校是不行的,这些事还是要靠你们办。”
亲爱的老爷子们,想想此一番话,你们也该宽宽心了——因为,你们在七十年前就开始探索与追求的,今天已经成绩斐然,硕果累累。你们——你们呀,真是中国的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