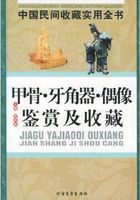我想,一个节目主持人应具备一些音乐素养。
任何艺术操作都处于一种“状态”之中,主持人也是;而音乐状态——即“乐境”,是一种最富于情感、韵律和色彩的境地,主持人进入“音乐状态”,就是“步入乐境”。
对于音乐家来说,不仅在创作、演奏音乐时是一种“音乐状态”,甚至在生活中也是。罗曼·罗兰说:“真正的音乐家是生活在音响的宇宙中,他的岁月就等于音乐的浪潮,他的心灵本身就是音乐,他所爱、所憎、所苦、所惧、所希望,‘无一不是音乐’。一颗音乐的心灵发现一个美丽的肉体时,就把那肉体看作音乐,使他着迷的眼睛,非蓝、非灰、非褐,而是音乐,心灵看到它们,仿佛一个美妙绝伦的和弦。”
作家和艺术家常在音乐状态中操作。
托尔斯泰说:“我喜爱音乐胜过其他一切艺术。”他从1852年初登文坛写的中篇《童年》开始,直到身后1912年出版的《哈基·穆拉塔》为止,在他的创作世界中就有被他称之为音乐的某种伟大力量的不断透视、变化和成长。
音乐的“状态”,可包括情态、动态、声态与形态。
1.情态
音乐是一种最情绪化的艺术。《乐记》曰:“情动于中故形于声。”托尔斯泰则将它称之为“感情的速记”。英国著名的小提琴家梅纽因则称音乐为“可以穿透人们的层层设防”,并说:“在某种特殊的场合演奏音乐,可以产生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他在一次葬礼中听阿马迪厄斯重奏团演奏了舒伯特的《五重奏》中的慢乐章后,对这段音乐有了全新的了解:“在这以前,我只是粗略地了解这段音乐的含义和它感人的地方。现在我感到,它既可表达出,又能容纳下无限宽广与深远的感情。”我自己也有过几次难忘的音乐体验,远的不说,就说1981年,我在纽约大教堂里听帕瓦罗蒂唱《圣母颂》的情景吧:那天晚上,教堂里挤满了听众,我站在最后面。帕瓦罗蒂的歌声如幽幽细丝,远远袭来。由于哥特式大教堂的石质隔离面吸收高音,对中音和低音的反射又十分强烈,使无方位的声源像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天堂的声音”,绕梁三周,袅袅不绝……
过了十多年,我在北京出席了“二十世纪华人音乐经典”的开幕庆典。音乐会的压轴大曲是《黄河大合唱》。黄河之水天上来!舞台的背景突然变成了一幅巨大的油画——滚滚黄河,湍湍急流,而急流刹那间化成了人海。十一个数百人的大合唱团像中流砥柱般地鼎立在台中央,而两侧则是朵朵鲜花——我们楚楚动人的童声合唱团。突然,在掌声的浪尖上闪出了白发苍苍的严良堃,只见他手一抬,黄河之水就从他指端奔泻而下……
这哪里是一首大合唱,它是一本重甸甸的历史,它是一阕响当当的宣言。它,就像叶选平说的:“要让青年们通过历史的教育懂得‘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这句话的含义。”一位台湾朋友说:“听了《黄河》,我才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中国人!”
我想,这些都是真正的“音乐状态”,都是充沛饱满的“情态”。希望我们的节目主持人在主持节目时都要有这样的状态,而不要像一个冷冰冰的在作解剖操作的外科医生。
但是,在某些时候也不能完全处于感情状态,而需要非情感化的处理,甚至要用“间隔效果”(“间隔”,Alienation)。布莱希特反对传统戏剧把剧院当作“迷惑观众的场所”,使他们“沉溺于一种现实的幻觉之中”;他用“间隔”使观众免于感情的卷入,让他们带着批评的眼光去观赏,从而调动观众的思想,唤醒其理智的好奇心。布莱希特的戏剧断断续续,每个片断主题明确,片断之间或插入歌曲、叙述,或用直观道具等间离手法以示区别。
我想,在我们主持节目时的整体把握中,应充满“情态”;但在间歇、转换、对比的部分,也可用“冷处理”,如点评、调侃、离题而言他等(类似作曲中的“离调”——即在“主调”构架稳固的前提下,在中间部分暂时离开主调游移至他调)。
2.动态
音乐即过程,是一种运动的艺术。我们观赏绘画时,可以一览无余;但聆听音乐时,必须从第一个音听到最后一个音,才能作出情感指向与价值判断。比如听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时,只听开始的“命运在敲门”的动机就“下车伊始,咿哩哇啦”,是不懂音乐的外行;只有在听完乐曲的全部“历程”——呈示、发展和再现之后,才能感知音乐的真义。我想,我们的节目主持人在主持节目时要有音乐的动态——有韵律、有起伏、有高潮,还要掌握语言的态势与张力。主持节目时还应该像乐曲布局那样,在运动中掌握点、线、面的安排——“点”,通篇的高点、低点、转折点、爆破点,特别是经常处于“黄金分割点”的高潮点;“线”,运动的线条起伏,抑扬顿挫;“面”,某一段落的强调和渲染、弱化和隐退。
但有时要动静相济,善于在适当的时候作静态处理。
莫里哀、梅特林克和一些法国象征主义作家在19世纪九十年代倡导过“静态戏剧”(Static Drama),亦称“无声剧”。静态戏剧力图避免典型的19世纪情节剧所特有的喧闹和活动,将目的放在激发悲剧的精髓——心灵深处神秘莫测的、秘密的活动上。梅特林克在一篇题为“日常生活中的悲剧性”(1896年)的文章中对静态戏剧的概念作了阐述。他说:“我渐渐开始相信,有一位老人,端坐在椅子上,身旁放着一盏灯,正耐心等待着;他对房子四周统辖万物的永恒规律充耳不闻,对门窗的无声无息,对光发出的颤巍巍的声音,尽管不理解,仍力图作出解释,他垂下脑袋,屈服于灵魂和命运……尽管他纹丝不动,但比起扼死情妇的恋人,沙场上获胜的指挥官,为自己的名誉雪耻的丈夫,他实际上要活得更深沉、更富于人情味,更有普遍意义。”
音乐中也有“无声音乐”。庄子曰:“大音希声”。美国先锋派音乐的领袖人物约翰·凯奇说:“我喜欢的音乐,无论自己的还是别人的,是我们保持安静时听到的声音。”1952年8月29日,在纽约市郊伍德托克的马瓦里大厅(Woodstock Maverick Hall)的舞台上演出凯奇的惊世名作《4·33》。钢琴家大卫·图德(David Tudon)走到前台,坐到琴边四分钟零三十三秒之久,没有弹出一个音,然后起身谢幕。这首作品的“音乐”,就是在这四分三十三秒期间剧场中不时从剧场外传来的声音。《4·33》体现了凯奇对有声音乐与无声音乐问题的探讨。他企图打破有声音乐与无声音乐的界限。
“无声”有时确实胜“有声”。
所以我想,就像音乐中用得好的休止是音乐的继续一样,节目主持人有时也可以静态的主持来反映动态的内容。
3.声态
音乐的物质基础是“声音状态”——“声态”或“声景”(Soundscape),类似英文中的“景色”(Landscape),它基本上由大自然的声音、人的声音及工具、机器发出的声音所构成。它们在声响环境总体所占的比重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会发生变化,且可能对音乐发生影响。沙费尔对不同时代这种变迁列表说明如下:
从上表可见,自然声响在声响环境中的比重在逐渐减少,而噪音则不断提高,甚至在声境中占主导地位。对于这一点,马克·德斯蒙德在《人在新的声响环境中处于紧张状态》(奥地利维也纳,1977年版)中这样写道:“在工业前的乡村声响世界中,噪音通常只是个别现象,到处是一片深深的寂静,甚至连最微小的声响都能引起乡村居民的关注”,而技术高度发展的社会声境则是“多余和干扰占主导地位”。
20世纪前的音乐是以自然环境的反映为出发点的,如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而20世纪的音乐则是工业社会的反映,如奥涅格的《太平洋231号》是对一个火车头的管弦乐描述,而新版的《1812序曲》中则用了大炮声。“声境”的变化使声源与听众的“听觉阀”都产生了变化,测定结果表明,1934~1955年间,在所谓“安静”的城市住宅中噪声从大约20分贝提高到大约50分贝。菲里波特(Philippot)推测:环境噪声的增强将促使人们大大提高音乐的响度,以使其压倒环境噪声。
“声境”的进一步变化是由于录放技术的革命。采用技术手段进行的音乐传播与自然的音乐传播不同,从扩音器里出来的音乐作品和艺术家手下的作品相比已是面目全非,不仅音乐信息的接收者要接受这种作为“音乐交际的第二途径”的“转播音乐”,而且表演者(特别是娱乐性音乐)的原始存在状态即寓于唱片和磁带的电声录音信号之中。故法国的研究者称之为“迪斯科形态”(Discomorphose——即唱片形态)。娱乐音乐的歌唱者常通过电使噪音得到强化(特别是对低频率进行强化)。
充满音乐状态的主持人应根据不同场景来创造声景。在运用充满表情意义的乐声外,可有目的、有选择地使用噪声,使它的“干扰”成为一种补充,使它的“无信息量”的声响成为有意义的细胞,来扩大声景,丰富表现力。
现代广播常通过电话参与来造成节目的新闻效应,这也是一种声源的“间隔法”,而有时在音乐节目中使用非音乐的声源也可扩大节目的表现力。如东方台新辟的“银海乐波”在开播时用了开盘带的转动声造成“开播”的音响形象,而在播放王洛宾的专题节目——当叙述三毛离开王洛宾,她的“家”时,节目制作人以无伴奏合唱《半个月亮爬上来》为背景,同时混录了雨声的效果,表现了凄风苦雨中的离愁。当主持人插播“1991年1月5日的凌晨,三毛自杀了。这个震惊全世界华人的悲剧消息,猝然击倒了王洛宾”时,雨声又突然变成了雷声。立体化的音乐造型,幻化成电影画面,更推出了电影音乐的震撼波与作曲家的生命张力!
4.形态
各种艺术都有它特有的结构形态。音乐的结构形态有两个方面:一是“内在形态”——即它的内涵的“无限性”,结构的“空框性”(即听众欣赏音乐作品时投入的不同的三度创造);二是它的“外化结构”(即它的结构形式)。现代的小说、电影、绘画常借用音乐的结构形态。如传统的文学是按时间顺序叙述的“线形结构”,传统的音乐则是首尾同主调同主音的“环形结构”;而意识流小说家则常在小说中运用音乐结构——如将音乐中的主导动机转化为一种暗示、一再出现的人物或场景,并创造出一种循环往复气氛的小说技巧,甚至按照曲式原理构筑作品的结构框架(如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运用主导动机,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运用了奏鸣曲与赋格曲的结构)。在影视中,也可以运用声画对位,即画面与声音不同步,形成对位关系。声画同步,表现的是同一时空,而声画对位则是将两个不同时空联系在一起,它可以扩大画面的表现空间。如经典名片《魂断蓝桥》的开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罗依来到滑铁卢桥头,吉祥符的特写。
(玛拉的画外音)“这给你。”
(罗依的画外音)“吉祥符!”
(玛拉的画外音)“它会给你带来运气,会带来,我希望它会带来!”
(罗依的画外音)“你真是太好了!”
这里用了声音的回忆,一下子将观众的思绪拉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连接了两个不同的时空。这样可以充分表现人物复杂的思想感情,扩大画面的容量。
主持人在主持音乐节目时,在没有画面的条件下,也可运用“声音对位”,用与音乐对比的声音使节目有立体多面的效果。
另外,节目主持人还应有亲切大方、机智灵活、有智慧、有内涵、有个性、有品位的仪表风范,而且应该是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上海的形象化身!主持人应该是庄重大方,语言规范,而不要去模仿洋腔洋调,既然是主持人,所“持”就须有“主”,要有主心骨,有主流文化的概念。
一个文化大国必定有代表文化传统与时代风貌的主流文化,一个健全的社会应该有各种声音,但首先是自己的声音。主持人,特别是主持主持人的人——文化领导部门,在政策上应有所倾斜,在导向上应有所指向。而前一段时期,主流文化萎缩衰退的状况是令人忧虑的——电台、电视台充斥了一些平庸低俗的节目,猛“炒”港台歌星、影星。多年前我去重庆参加“二十世纪华人音乐经典”的演出,那里正好才开完刘德华演唱会,票价竟然炒到1000元一张,有的中学生没钱买票,就去卖血——这真叫“大出血”了!我问那些孩子,刘德华的演唱好在哪里她们说:“他的皮肤很好!”我又问:“那么,你又怎么知道他的皮肤很好?”她骄傲地把头一扬说:“因为我亲了他一下!”这真令人心痛,也令人啼笑皆非!当然,我们不应过多地责怪那些天真无邪的“十六岁花季”,她们在课业重压与业余生活贫乏单调的情况下,憧憬着自己的青春偶像和白马王子,希望能通过浅层次的“快餐文化”来得到娱乐、消遣与情感的宣泄,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需要的;但是,我们应让她们有更高的追求,让她们有更多的选择,不能单向地灌注那些艺术上的二手货,将一尊尊“天王”树为她们顶礼膜拜的偶像。伴随着历史上所有伟人成长的,必定是传统和同时代的优秀文化。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说,他发现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是受他家乡巴伐利亚民歌《和谐曲》的启示。爱因斯坦说:“我的科学成就,许多是受音乐的启发而得来的。”我们的传播媒介的辐射力宛如原子弹,费城交响乐团在上海体育馆演出一百场还抵不上一场电视转播和一次电台实播,我们负有对青少年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个责任呼唤我们的主持人和主持主持人的人一定要有文化良知,一个现代化的文化大国必须有一个强大的文化支撑点,这就是我们的主流文化。同样在重庆,同样在这个可以容纳四千多听众的剧场,我们演出了交响音乐,演出了《黄河》和《梁祝》,受到了听众热烈和真诚的欢迎;而这些听众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青年听众。这充分证明,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文化导向、合理的文化布局、高雅的文化品位和良好的文化氛围,只要我们的“原子弹”放射的是优秀的精神食粮,我们的受众——观众和听众是会拍手欢迎的。希望我们的传播媒介发出时代的最强音,用最新最美的旋律谱写我们21世纪的新乐章!
(注:这是在上海戏剧学院的一次演讲,后发表于1993年《广播电视研究》第四期,并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