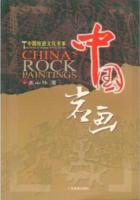“你的弓不会只有一根弦的,只要你愿意去找到那根弦。”卡耐基如是说。他还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有一次,世界最有名的小提琴家欧利·布尔在巴黎举行了一次音乐会,他那把小提琴上的A弦突然断了,可是欧利·布尔就用另外三根弦演奏完了那支曲子。”卡耐基意味深长地说:“这不仅是生活,这比生活更可贵——这是一次生命的胜利!”
人生是一曲长歌,它是由弓弦相撞、迸发而生的生命火花编织成的乐章。通常,人们只惯于运弓演奏自己熟悉的那根“A弦”——作家爬格子,作曲家爬五线谱。我爬了几十年的五线谱,长歌短吟,驰骋万里;但在逢遇“弦外之音”想要抒发时,却又觉得五线谱不够用了——那就得另找几张稿纸来爬格子。不过,对于我来说,“格子”如同“六线谱”——一张加了线的五线谱;行文也宛似作曲,即在文学中寻找音乐的对应……
情是艺术的命根子,无情不成曲,无情不成书;艺术家又大凡都是些多情、痴情的情种。1981年访美时,我特地送给小提琴大师斯特恩一幅摘自《乐记》经典名言的条幅:“情动于中故形于声。”音乐如此,文学当也如此。对于我来说,“文”与“曲”都不是“作”出来,而是流出来、倒出来、喊出来、哭出来和爆发出来的——它们全是情感所驱、兴感所至的产儿,就像刘鄂说的:“灵性生感情,感情生哭泣。”和郁达夫说的:“总要把热情渗入,不能达到忘情忘我的境地”那样,情是艺的命脉与灵魂。文学,是我音乐的补充,也是我那根“A弦”之外的另一根发出奇声绝响的弦。这根弦斑斓绚丽,丰富多彩;它不仅可以像用音符倾诉心曲那样,用语言文字载述那些真实又揪心的往事,展现生活的波澜,就像一首首抒情的浪漫曲和激越的交响曲;也可像谐谑曲一般,嬉笑怒骂,变调夸张。在这根弦上,我发现了一个与音乐同样宽广的表情天地,此时,“格子”似乎霍地破纸而出,跳上了五线谱,谱写出一曲曲“无音歌”,发出那咯咯作响的“文字音响”……
行文如作曲。乐曲是感情流的波影,而“随笔只凭兴感的联络求得。”(许钦文)我写文章纯属“无序操作”和“无规则游戏”——偶有所感,就兴笔乱涂。先是将最想写的、不吐不快的萌动和触机记下,然后顺势而下,铺陈展开,一遍遍地写,一遍遍地改。其实,此法乃取自日本作家小泉八云也!他一再强调:“最要紧的是先写最得意的部分。层次无关宏旨而且碍事。得意的部分写得好,无形中便得到许多鼓励,其他连属部分的意思也就自然逐一就绪了。”他还说:“这样的工作都是自生自长的。如果第一次我就要想做得车成马就,结果必定不同。我只想思想自己去生发,去结晶。”我非常欣赏他提倡的“自生自长”和“自己去生发,去结晶。”当然,结构、节奏和色彩还是要讲究的。我常温习“散文不散”,头尾要“夺目勾魂”(李渔),用字遣句要“冗繁削尽留清瘦”(郑板桥)的古训;更牢记我们作曲时常循的法规——由“点”而及“线”与“面”。我这是“点睛画龙”,而不是“画龙点睛”;是作为文学票友的作曲家的“文章作法”。
最后,特别要感谢先父的挚友——丁聪叔叔为我的书名题画。他真是“永远的小丁”——从那从不涂颜料而闪闪发亮的一头黑发,到那八十未泯的童心与笑舞天下的画笔,都是“小丁”的写照。一次在黄苗子、郁风、冯亦代、黄宗英诸位大家面前,他向他们介绍我说:“此人写得一手好文章——促狭!”此番话真是羞煞我也!论文章,我只能跻身于“票友”行列;评为人,我倒还是挺厚道的。只是耳朵比别人多了一只——不论是古典音乐、流行音乐还是现代音乐,只要是好音乐我就全爱听!这叫“三只耳朵听音乐”。同样,我的“弦”也比别人多几根,即或我那根作曲的“A弦”不断,我也照常会将心曲按在“文学弦”上奏鸣。因为,“这不仅是生活,这比生活更可贵——这是一次生命的胜利!”
1996年3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