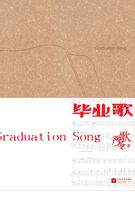“你和我喝过酒的,你知道我根本没有喝多,但我心里有一点醉的感觉。我知道我想要醉,你要知道我的心意,我就是想要你知道我的心意……你看我,我不象小雪吗,都说我象小雪的,我也知道小雪从小就和你很好,你对小雪也很好,我听到小狗子说到你和小雪的感情,我就知道你的心里是爱小雪的。这点我是一个女人,我懂。不是说我是再世的小雪吗,大概我就是吧,我上一世没有懂,这一世就懂了。我是不想成为小雪的,我为什么要是另一个女人呢,但我为了你,很想自己就是小雪。小雪上一世欠了你的情,这一世,我来还你,你就把我当小雪吧……”
白小坛已经把身子完全凑到了我的面前,我都感觉到了她的呼吸。我只听着她的嘴里一声声的小雪。她的身姿带有着一种习惯了似的女性的意味,是我从来就没有感受过的,她身上的那种很难说得清楚的气息,让我有一点不自持,借着酒来摇晃着我的感觉。那一声声的小雪也来摇晃着我,存着了多少年前的感觉,都涌上来。然而,也正是那一声声的小雪,让小雪的形象仿佛很清晰地在我的眼前闪了闪。我想张口叫一下,就这时我看清了面前的白小坛,她的脸色由红转着黑,眼角明显地挤着了皱纹,整个形象显得有点胖得虚浮着。不知是什么缘故,在小雪那形象的映显下,白小坛的样子是那样粗俗显见,情欲显见。这时,她正把我的手拉着了,放在了她的挺得高高的软软的胸脯上,并且使劲地往里按着。
我一下子夺过了手,我的动作大了一点,强了一点,我嘴里也喝了一声。她猛一下,也有点发怔了,一双眼睛直楞楞地看着我。似乎是从来没有遇见过的样子。
我这才想到了小狗子告诉过我的话。这话刚才已经隐隐地浮在我的心里了。要不是小狗子说过的话,也许我还不会这样反应猛烈,我也许会缓和一点。小狗子曾经告诉我,说这个白小坛整个就是一个荡妇,见到哪个男人都会上床崐脱裤子的。甚至他说,她有一次对他也有所表示,说是愿意象过去的小雪那样报答他过去的情意。那时小狗子对我说这些时,因为他言词的强烈,反而让我感到有点不可信。我还是见过白小坛的神情的,虽然我心里多少有点反感,但我一直认为,那是她象小雪而又不是小雪所带来的。我万万没有想到,她竟真是这样的一个女人。我一时为秦泰春感到有点心痛。我也想到小狗子为什么会那样急急地离开我回到小城去。他原来为了一个象小雪的女人留在这里的。他肯定看到了她和许多男人的事。他是最容易探到许多的事情的。
白小坛怔了一会,慢慢地站起来,她往外走。她的神情中仿佛还带着一点满不在乎,看着她这随随便便的样子,比刚才还要深深地剌着我的感觉。我猛喝了一声:
“站住!”
她回过身来,头扭转来,一看我,身子颤一颤。我的叫声和脸色肯定显着一种官威。她这时有点心虚似地,惊慌了,她的身子有一点颤动,害怕的感觉上了她的脸。她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怯怯地看着我。那一瞬间,我的心软了一软,声音也缓和了些。
“你坐下。”
白小坛顺从地在我的对面坐了下来。后来她抬起头来,看着我,她的目光中变得直视着我,清清纯纯的,黑眼眸直朝着我,很象小雪的神情了。
“泰春他对你还不好吗?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白小坛的黑眸子动了一动,便又带着一点斜睨,活活地瞥来。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不就是因为你……”
我的手挥了一下,我讨厌她的神情中的那种女人说谎时的神情,我怕她把那我已经了解到的谎说完了。
“你,跟我老实一点,泰春他被你欺骗,是他被你迷住了,他是个聪明人,愿意被你迷,也是他喜欢你。你以为我也是那么好受骗的么?”
我想白小坛被我这一下又会打得发怔了。女人毕竟是柔弱的,她也许会哭起来。然而,她却一下子扬起脸来,那种女性怯弱的神情消失了,她迎着了我的眼光,毫不示弱地。好象横下一条心了。
“好吧,你知道,你当然能知道。你这样的大干部,想知道什么就能知道什么。我也没想瞒你的。你是不是说我搞过许多男人和许多男人好着。你说秦泰春他对我这么好,我为什么还要和别的男人乱来。那么,你当然也知道秦泰春他当年,也搞过多少女人。男人搞女人就是天经地义的了?你也为小雪做过什么事么?叫过屈喊过冤么?在你心里,男人可以做,女人却不可以做。是么?我就不信。新社会男女平等。你们男人都一样,一边自己搞女人,一边骂女人。不要摆你是干部的架子,我见过的许多都是干部,也有不小的干部。他们并没有象你这样,他们外表很正经,脱衣服扑上来的时候,还不是……”
“够了,少说这些没廉耻的。泰春他以前是怎么,那是以前的事,自从他救了你,把你救出来,和你成家后,至少没有对不起你。你莫非一点不讲良心么?你怎么对得住他?”
“怎么?你这样的共产党干部也讲良心这个词?亲不亲,阶级分。我现在看你这个干部也是没有阶级性的,我清楚你一直包庇秦泰春,你的思想也不对头,总有一天你会倒霉的。秦泰春当然对不住我。他假仁假义地救了我,是有他的目的的,我只是他的那种良心的牺牲品,一种可以宽慰他良心的东西,假的东西,可以让他自欺欺人的自己骗自己的东西。这也是他不尊重人的本性,把女人当替代物的本性。我这样一个年轻也漂亮的女人就只能听着他,把自己变着另一个女人来满足他。那就是你说的良心了吧。不,我不是小雪,也只有小雪那种出身在地主家庭的女人,才会心甘情愿做一个受害者。有一段时间,我认为把我当做小雪很气愤,后来我明白地想到,小雪她也是受害者。她也是希望有人为她报仇的……”
白小坛一下子在我面前显出她的伶牙利齿来。我这才发现我是低估了这个原来出身很穷苦的女人了。她接受了不只是从秦泰春那里教的文化,也接受了不知哪里来的一些理论。不知是哪个男人教会了她的理论。也许这种的理论的实质,我同样也在说。
“你根本不懂小雪……”
我说了这一句话,心中有一点感伤泛了上心来。小雪过去的形象一下子闪崐动在我的意念中。她最早的那种活泼,后来的那种坚定,最后的那种沉静和迷惑,象很活的镜头闪现着。她悲哀的神情,她痛苦的神情,她清纯的神情,她木然的神情。而眼前正对着我的白小坛,辨争起来显着了一种无所谓的形象,正映衬着小雪那虚幻的神情。让我一时觉得那是一个复仇的女性形象。
“……她是很爱秦泰春的。”我想到了小雪一切的做法,包括她的死。她绝不会怨着秦泰春,绝不可能对秦泰春复仇的。
“只有阶级的爱,也只有地主家庭出身的小雪才会爱那么一个当过反动军官的旧知识份子,他有什么用?他的那些聪明才干,都用在了什么地方?都在一些废书堆里,除此之外,他又有什么用?一次次的社会活动中,一次次使我看到了他的无用和渺小,他的被人瞧不起,他的挨批判。他走不进新社会,他满脑子的旧思想,右派思想,我清楚,要不是你帮助他他早倒霉了。肯定是你帮助他,他是一个十足的右派份子。你要我去爱那么一个人人都可以批判的旧知识份子?我为什么要那样?我为什么不能去爱一个穷苦出身的人,为什么不能去爱一个革命的人,为什么不能去爱一个真正有用的人,为什么不能去爱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想到在家对着一个反动的旧知识份子,想着这样的男人是我的丈夫,我的心里就腻歪,我就想出去,我想献身给一个好男人……你别以为,我是一个荡妇,我是一个不正经的女人,你别以为我是一个性欲狂,是一个什么男人都要的女人,告诉你,我很正常。你也许应该清楚,秦泰春他作为男人,在床上所给我的,他有着那么丰富的经验,以他旧社会获得的罪恶的经验,在许多受苦女人身上,在许多受害女人身上获得的经验比哪一个男人都多。他大概也就是在这一方面是最能的了。不象许多男人都被一种假正经弄得都不行了,心里要,但不行,就越发地假正经……”
白小坛突然停了口,眼光朝我看来,那眼光中带着一点轻视的,隐隐暧昧的意味。我敏感着那种意味。她所说着的所暗示着的正是指我没有女人在身边,一直两地分居着。我这种居然没有女人的生活,是不是有着男性的隐讳。她的眼光中的那点暧昧,有一瞬间真让我很想冲上去,揍她一下,甚至在她身上表现一下我的男性的力量。但几十年的风雨血火的生涯,使我具有了一种难耐的定力。我应该让她看到一个真正的男性的力量,一个革命者忍耐的力量。我用眼盯着眼前这个女人,慢慢地,我感到她眼中的亮光减弱了,想避开去。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和他离婚?”
问着这一句话的时候,我感到了一点悲哀,一点为秦泰春的悲哀。我居然无法反驳这样一个女人的话,无法在她的面前为他辩护,举说他的才,举说他的德,举说他的力量,举说他的优点,举说他的内心。我明知道,他为这个女人做着许多的事,做着许多的牺牲,他给她烧饭,他给她做菜,他把她服侍得比父母都好,他为她做着一切。但他却一步步地在她面前,失落了那可以重视的一切,可以正眼对待的一切。我知道这一切很荒诞,但用白小坛的话来说,她却说得都有一定的道理,合着一种社会的理论标准。
“我是可怜他。我要是离了他,还有谁会来做他的老婆,这个半老头子,又是旧知识份子,又是个内定右派。早先还是一个风流反动军官,搞女人把前妻都弄死了的。这一顶顶帽子还不够吓着人家的吗?我做这样的事,你说他会不知道吗,他心里不清楚吗?你说他那么聪明的的人,他又是在女人里混过这么长的时间,他能不清楚吗,我也并没有想瞒他。他只是装聋作哑,他不提,我也就不想对他明说,照顾他一点面子,我并不怕他知道。说他是黑暗,那么,我便是朝向着光明。你说,他离得开我吗?你看他那样子,能离得开我吗?我要一离,他准活不了多长时间,你相信不相信?当然,也不是完全是可怜他。我也是想到过离婚的,要是他真正地成了一个右派份子,我当然会打消可怜的念头,彻底和他划清界线的。但他还是被拉进人民内部矛盾中了,还称他是同志。就象红妹说过的,要改造他,我也就有改造他的义务。我也只有牺牲自己,背着个这样男人的老婆的名声。我知道我有好多次能够做职务高一点的工作的。我的工作比任何人都积极,但都是因为了他而耽搁了,因为有这样一个丈夫的关系而耽搁了。有时我真恨我下不了决心。”
我实在无话可说了,我所能做到的,只能是对白小坛表示一点缓和气氛的神态,然后客客气气地把她送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