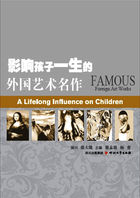在台湾、香港的商业类型片运作里,的确存在着某些迎合时尚的媚俗或者低俗的问题和倾向,如《色·戒》、《投名状》或《大灌篮》(篮球场上竟也来他个少林寺式的拳打脚踢),都给内地市场带来了恶劣的文化影响。内地与台湾、香港电影的再一轮文化整合,无疑应是互取所长,而不应是唯票房马首是瞻地、目光如豆地专取对方所短,将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践踏成一地的碎片。试看2007年曾经轰动大陆市场的《疯狂的石头》,作为低端的小投资格局的商业喜、闹剧片,居然一度取得了众多小片所难以望其项背的票房纪录,然而,当这部“疯狂”的影片回到启动其制片运作的原地香港或输入进台湾时,竟然是“门可罗雀”,票房几近于零。何以然?简单得很,在港台,这一类“搞笑的无厘头类型”早已被人们看得滥熟而不屑一顾了。以海峡两岸三地的电影环境而论,香港以其弹丸之地如果不是靠“CEPA”(即关于内地和香港间紧密经济关系之安排)政策的支持而北进内地,早就岌岌可危了;台湾的电影工业事实上也早就滑落到近乎“死点”的地步了。诚如台湾著名的电影学者焦雄屏2008年元旦在北京万达广场单向街书店一个“读者见面会”上所坦诚道出的真相(笔者则陪同她一起作“对话”):“中国台湾曾经有过非常辉煌的电影新浪潮,而在电影市场逐渐向好莱坞‘开放’后,随之的1991、1992、1993那几年,台湾的电影就消沉了,陷于文化的谷底,一路垮到现在。我们的市场全部被好莱坞电影吞噬,台湾本土市场的占有率只剩下不到1%。就是说,台湾出品的电影,放到影院里头基本上是没人看的。”焦雄屏、黄式宪:《电影产业的发展与文化品位的提升》(对话录),《艺术评论》2008年第3期。前车之鉴,岂能不认真面对并牢牢地记取?!
2005年10月17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31届会议上正式通过了一项决议,即《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宣言中指出:“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并强调说,“尊重文化多样性、宽容、对话及合作,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佳保障之一。”转引自赵军:《〈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对中国电影的意义》,《中国电影报(产业周刊)》第42期,2005年11月3日。对抗好莱坞的单边化以及文化趋同性的危机,唯一之途就是要坚持“和而不同”的文化准则,要尊重并坚持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着眼于文化在新世纪的发展前景,在东西方之间,对话性必将取代对抗性,21世纪不会固守不移地依然徘徊在“东方从属于西方”或者“东方以自身的边缘性而环绕着西方文化中心”的历史误区里。事实上,文化全球化并非像经济全球化那样必然导致各民族/国家的文化走向同质性,反倒可能带来全球文化多样性的良性互动。试看亚洲各国新电影风潮的兴起,或许正是暗合了“和而不同”这一共识,从而才呈现出各自文化的特色及其无可替代的魅力来的。华语电影的未来势必也将履行这一“和而不同”的共识,以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张力,平等而有尊严地自立于世界诸国民族电影之林。
华语大片与中国电影工业
饶曙光饶曙光,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
一新中国电影事业体制与电影工业布局
早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非常重视电影工作,在各方面条件都还不具备的情况下,就建立了“延安电影团”。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1948年12月,中共中央就当时电影工作的主要问题作出三条指示:其一,电影事业领导与统一问题;其二,在北平的国民党电影机构接收问题;其三,全国电影领导机构的建立问题。“指示”明确地规定:“平津攻下后,电影事业的领导机关应设在北平。”1949年3月,袁牧之应召来到北平,根据党中央指示,进行全国电影领导机关筹建工作,并于1949年4月在北平正式成立中央电影事业管理局,在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下,担负领导全国电影工作的任务,由袁牧之任局长。干部方面,各地方和部队都以干部支援电影工作。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解放区的文艺骨干如成荫、沙蒙、水华、凌子风、林农、严寄洲、崔嵬、陈怀皑、吕班、郭维等先后进入电影界,他们的创作也很快成为新中国电影的主流。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中央电影局改属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领导,称“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局”。中央电影局作为全国电影事业统一的领导机关,其首要任务是对旧电影的接管改造和对新电影的建设发展,作出步调一致的全面布局。
经过清除好莱坞电影运动饶曙光:《新中国电影的第一个运动:清除好莱坞》,《当代电影》2006年第5期,页119—126。,批评电影《武训传》的运动以及对私营电影公司出品的电影的批判,新中国迅速在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层面确立了“工农兵电影”的方向。由延安电影传统发展出来的“工农兵电影”开始在中国电影中占据绝对统治和主导的地位,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合力的推动下形成了与其他任何电影形态都不一样的新中国电影范式。饶曙光:《中国喜剧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页152—153。由于解放前的中国电影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美国电影的影响,社会主义性质的新中国电影范式事实上就暗含了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电影整体性对抗。简而言之,新中国电影其标志性的影像是北方/农村/革命,而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因此,上海电影及其传统注定了要被改造乃至抛弃。
新中国在外交上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方针,新中国电影也相应采取了全方位“向苏联学习”的方针,并在具体操作上通过“请进来”和“走出去”加以落实和实施。“总之,可以这样说,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不仅从美学思想方面受到前苏联电影的深刻影响,而且从管理体制上也照搬了当时前苏联的那一套。”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1949—1959》,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年,页6。在前苏联专家帮助下,我国制订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电影管理计划,统一由国家预算拨款和专项拨款维持其建设、生产和流通。其中,对制片厂实行行政指令性管理,制片厂根据上级对数量及题材的严格计划接受影片拍摄任务。在发行方面,把中国影片经理公司改组为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将各大区公司建制为各省、市发行机构,并建立完善了发行放映经营管理的各种规章制度,在电影局设立了电影放映管理处,各省、市、自治区文化管理部门亦成立相应的各级机构,有一级政府就有一级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加强放映工作的统一管理。这一整套设施的建立,都是以行政化机制为依据和功能目标的,而市场效应和市场运转则作为辅助的手段,因此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垂直管理的政企合一的电影发行体制。作为全国发行放映总代理的中影公司负责收购影片,之后通过等级分明的各个发行放映公司以业务和行政相结合的手段从省、市、县往放映单位发放拷贝。除了1958年和1976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发生过几次动荡外,到1993年电影机制改革以前,其基本架构和内部经济关系未有任何本质上的变化。
为电影事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贯彻执行,1953年12月,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电影制片工作的决定》和《关于建立电影放映网与电影工业的决定》。依据电影事业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加强电影制片工作的决定,在电影制片事业的建设上,新建了北京、珠江、西安、峨眉以及部队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原北京电影制片厂改为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还充分利用旧有基地分别建立了科学教育、美术和译制片厂,基本做到布局合理、片种齐全。在制片事业建设过程中,同时完成了对私营电影制片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建立了现代化的影片洗印工厂——北京电影洗印厂,扩建与改建了南京、哈尔滨、上海三个电影机械厂,基本解决了发展放映网所需机器和影片拷贝的自给,对制片设备的自给达到80%。政务院《关于建立电影放映网和电影工业的决定》强调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要求,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电影放映事业,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电影放映网。放映事业发展方针是“首先面向工矿地区,然后面向农村;在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则以发展流动放映队为主”政务院:《关于建立电影放映网和电影工业的决定》,《人民日报》,1954年1月12日,第1版。。可以说,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电影放映网是新中国电影事业体制最突出的特点,为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按照建立电影放映网的决定和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结果,到1957年底,全国电影放映单位发展到9965个,为1952年的4.4倍;其中35毫米电影院发展到1030家,为1952年的1.4倍,16毫米电影放映队发展到4707个,为1952年的9倍多。随着电影放映单位的发展,全年电影观众达到17.5亿人次,为1952年的3.13倍;全年电影发行总收入达到6119万元,为1952年的3.8倍;发行利润达到2384万元,为1952年的26.3倍。在电影发行放映事业的经营上,从1951到1957年,国家拨给电影发行放映企业的基本建设投资是343.5万元,中影公司上缴国家财政的利润是3858.2万元。”《电影经济》编辑室:《电影事业三十五年》,《电影经济》1984年第4期,页1—3。到了1965年底,“全国放映单位已达到20363个,为1949年的31.5倍。其中,城市电影院2500余座,电影俱乐部2300余座,电影放映队1.4万个。全年放映电影655万多场,观众观众46.3亿人次,发行收入131亿元”陈荒煤:《当代中国电影》(下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页273—274。。
二新时期与中国电影工业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基本路线,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新的发展时期。1979年,电影创作开始摆脱“文革”电影的阴影,突破了传统的“高、大、全”模式,其标志性的作品是《小花》、《苦恼人的笑》、《生活的颤音》和《归心似箭》。其后,1979—1987年,“第四代”和“第五代”导演推动了中国电影的创新浪潮,完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空前绝后的一次电影语言的现代化革命,并形成了以精英话语(启蒙意识、艺术至上)为主导话语的电影新观念。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第四代”的电影还是陈凯歌的《黄土地》、张艺谋的《红高粱》等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第五代”的电影,其投资都来自计划经济下的国营电影制片厂。正是这种计划经济下的国营电影制片体制给“第五代”导演的“探索片”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和空间。倪震先生就指出:“电影厂对于自己生产的影片没有销售经营权,在这种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下,电影厂不必过于关心自己生产的电影被卖的拷贝数,更不用去关心影院放映的实际票房数额。这种经济关系显然不利于常规的商业娱乐型电影的发展成熟……尤其在当时‘思想解放’、人们关注历史反思和文化哲理探索的社会思潮背景下,它无形中为探索片和‘第五代’的出现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经济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五代’是旧电影经济体制的受益者,是社会意识形态已经嬗变而旧电影经济体制依然基本保留这一特定时期、特定气候土壤中的一枝奇葩。”倪震:《改革与中国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年,页198。换句话说,1979—1987年对于电影创作来说是空前绝后的,艺术家较少受到政治的限制,也几乎可以不考虑经济回报,所以取得了空前的创作自由。正如何群所说:“从导演和创作手法上来说,我们也的确没有考虑去迎合观众的趣味,而是更想通过影像来表达思想和追求。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电影整体都是这种情况,那就是对艺术的追求和创新要远远大于对市场的欲望。”何群:《电影是集体的艺术》,《大众电影》2008年第2期,页42—45。事实上,计划经济下的国营电影制片体制电影决定了电影制片厂不必过于关心自己生产的电影被卖的拷贝数,更不用去关心影院放映的实际票房数额;也决定了电影创作“对艺术的追求和创新要远远大于对市场的欲望”。只要有对“对艺术的追求和创新”,而不管是否有观众、有市场,都会得到主流精英话语的肯定和推崇。“对艺术的追求和创新”走向“极致”,最终使得“探索电影”成为西方观众观影视域下的“寓言电影”而失去了当下观众和本土电影市场,如《猎场扎撒》是一个拷贝,《盗马贼》也只有七个拷贝。田壮壮豪迈地放言:我是“为21世纪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