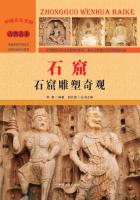当然,20世纪末重新浮出的全球化问题由于语境的变化而发生了一定的变异。对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来说,全球化是现代性内在的特质,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参见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TheConsequencesofModernity),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1年。“全球化”是“在场”与“缺席”的交合并存,是“距离化了的”社会事件、社会关系的当地化和情境化。而另一位英国学者约翰·汤林森(JohnTomlinson)则基本承继了吉登斯的主要观点,认为全球化以“复杂的相关性”为特征,是定义现代生活的急速发展和日益缜密的交互关系和相互依赖的网络;内在于“复杂相关性”之中的乃是“全球空间的相邻”和大卫·哈维(DavidHarvey)所称的“时空的压缩”。国际旅行的便利、卫星电视、互联网、跨国体育赛事转播、国际政治与跨国公司活动的日益频繁、卫生健康与环保问题的跨国性、技术与劳动移民的跨国流动以及由数字技术发展而出现的各种跨国传播手段等,都是“全球空间相邻性”的具体表现。具体到文化层面,全球化并不会导致文化的普遍同一,而只可能是文化融合与差异的并存。以互联网为例,尽管网络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们传统的时空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全球“同一城市”(Unicity)的出现,但它同样为过去散布在世界各个角落的鲜为人知的文化和利益团体吸引公众注意力提供了机缘。在汤林森看来,本土经验和本土文化试图在全球化时代被理解,就必须提升到“单一世界”的层面;“本土实践和生活方式日益需要放置在全球影响的语境下加以检视和估价”;这一对人类存在共同因素的强调会促使汤林森所提出的“良性普适主义”(gooduniversalism)的形成。参见约翰·汤林森:《文化与全球化》(GlobalizationandCulture),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9年。
全球化理论的另一代表人物、社会理论学家阿帕杜莱(ArjunAppadurai)在其影响深远的著作《泛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面向》中,借鉴法国理论家列斐弗尔(HenryLefebre)“空间的生产”(theproductionofspace)观念,提出了他所称的“地域的生产”(theproductionoflocality)理论。在他看来,媒体技术的发展和各种民族散居社群(Diaspora)的形成解构了传统民族国家和地域观念,赋予原来具有明晰疆界、相对固定的地域和民族国家以前所未有的“流动性”(flow)。在此情形下,关于当代全球化现象的理解必须超越过去受限于民族国家或固定地域的思维定势,转而以“去地域化”(deterritorialized)或“跨地域性”(translocalities)的视野透视当代文化的转型与契合。参见阿帕杜莱:《泛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面向》(ModernityatLarge:CulturalDimensionsofGlobalization),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6年,页192。所谓“去地域化”,一方面是指文化产品的全球消费打破了特定地域和文化消费者原来所享有的与该地域和文化所形成的自然关系(如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的传播),另一方面也要求文化产品在制作和传播的过程中不拘泥于原文化原地域限制,力求以“当地化”、“情境化”的姿态满足不同文化或国度消费者对产品的不同需求(如好莱坞的中国化)。汤林森在《文化与全球化》一书中对此也多有涉及。与此相应,民族志学家过去所坚持的地域性根基也应被“跨地域性”所取代,因为“跨地域性”直接影响和作用于“亲历的、本土的经验”。阿帕杜莱:《论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面向》,页52。在“去地域化”和“跨地域性”语境中,想象变成了一种具有生产能力的社会力量,成为自我认识、身份定位、意识形态和观念建构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想象不再仅仅以抽象形态作用于人的思维,而且更成为具体实践的一环,具有了理论意义上的可触摸性。
本文以吉登斯、汤林森和阿帕杜莱等关于全球化问题的思考为关照,考察了近年来渐成气候的“华语大片”现象。文章认为,“华语大片”的跨境生产、发行以及传播和消费主要通过作者所称的“无地域空间”生产(theproductionofnonlocality)达成。在文化理论中,地域(locality)、地点(place)与空间(space)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地域和地点一般指较为具体且具有其特殊性的地理存在,而空间则指较为抽象并含有价值与意义的社会建构。很多学者认为,全球现代性乃至后现代性趋势的加剧,正重新定义和组合着我们关于地域和地点的认识;甚至有学者认为,全球化过程实际上意味着具体地域、地点的消失,取而代之的乃是普在化、普遍化的全球“空间”。本文将“地域”与“空间”并提,一方面是照顾到中文行文习惯,另一方面也意在凸显具体地域被全球“空间”取代的转型过程。所谓“无地域空间”,指的是某些超越文化和地域特质(translocal),或被抽去原地域或文化因素的空间符号(delocalized)和人性母题,它至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涉及可触可感的物质、生活空间,在电影中表现为无显在地域特征的具体场景和影像空间的营造;第二层则涉及经由各种话语和想象所建构的主题空间,在电影中一般呈现为对某些人类“普适”(universal)议题的关怀。在空间之前冠以“无”的修饰词,并非指其子虚乌有,不能被感知、触摸或体验,而是意在显示此类空间的无名性、去地域性、普在性。此类空间的突出特征乃是其“可移植性”,既在某种程度上形成对原空间滑动和隐喻的指涉,又能够超越与原空间的含混指说关系,经“移植”后被异地域文化所消费。之所以用“无地域空间”而不用“跨地域空间”(translocality)来指称这一现象,是因为在作者看来,“跨地域空间”的命题仍然存在着“本地”和“异地”二分区割的嫌疑,它首先设定了一个本源体,然后才通过“跨”(trans)境实践传播或影响异文化领域;而“无地域空间”则或能超越以上二分区割,有助于在全球背景下理解各种文化现象之间日益频繁与紧密的流动、消费和交互指涉。同样,“无地域空间”与“去地域空间”既有联系亦有区别,后者在作者看来更强调对既有存在的动作性去除,而前者则凸现某种既成的状态,是对业已存在的现象的描述与分析。
“无地域空间”的生产与资本的全球扩张
空间观念在后现代文化和社会批判理论中的重要位置已被很多学者所强调,在此不必赘述。从列斐弗尔到爱德华·索亚(EdwardSoja)、从福柯到杰姆逊,空间或成为其理论关注的焦点,或被用做其理论铺展的起点。正是由于这些理论家的思辨性阐发,我们对空间的认识日趋复杂与成熟。空间不再是一种独立于主体之外、仅仅供主体厕身其间的无生命存在,而更是一种汇聚了“主体性与客体性、抽象与具象、真实与想象、可知与不可知、重复与差异、精神与肉体、意识与无意识”的复杂体。参见爱德华·索亚:《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ThirdSpace:JourneystoLosAngelesandOtherRealandImaginedPlaces)中文版译序,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页13。在列斐弗尔看来,战后资本主义秩序得以维持、存活乃至进一步强化,端赖他所提出的“空间的生产”:高速公路网的纵横交错、大型购物中心的普及、郊区化社区的大量复制和生产、整齐划一的空间布局,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一整套规则等,所有这一切都为资本主义体系的强固提供了关键保障。
“无地域空间”的生产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密不可分。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与殖民从空间意义上说也就是对非西方国家空间“他性”的改写与同一化。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代主义风格的摩天大楼不仅塑造了纽约、芝加哥等西方城市的性格,而且也改写了上海、东京等东方都市的城际线,突显了不同历史、文化国度空间的无名性和去地域特质。如果说“无地域空间”的生产是现代性某一面向的话,那么,晚期资本主义发展和经济全球化速率的加剧则使“无地域空间”演变为无所不在、遍布世界每一角落的存在,构成后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如果我们以某一城市为始发地环游世界,跨越历史积淀所形成的民族国家疆界和语言边界,我们也许会有这样的体验,即看似遥远、过去仅仅是地理学名词的彼城市似乎并不陌生,恍惚中很容易被体认为记忆中某座熟悉的城市:同样繁忙靓丽的国际机场,同样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网,同样闪烁炫目的玻璃幕墙大楼,同样方便迅捷的地铁网,也同样张扬夸饰的巨幅广告牌。麦当劳、星巴克、肯德基、迪斯尼、购物中心等不仅改写了世界不同文化、不同国家内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而且也在空间意义上重新定义了熟悉与陌生、地域与去地域化。
再以香港资本在内地的扩张为例。在全球资本重绘中国地域空间的角力中,香港资本无疑占据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位置。这不仅因为港资历年以排头兵姿态润滑了中国内地经济发展的引擎,而且也因为香港资本背后与内地纠缠交错的政治、文化与历史关系。惟其如此,香港资本对中国内地地域空间的重写亦即“无地域空间”的生产,不仅表现为在内地城市建造了众多令消费者徜徉其间而不知身处何地的“香港广场”和港式购物中心以及餐饮娱乐中心,而且也表现为貌似依循本地空间逻辑、实际却掏空其内里的“无地域空间”的生产。这一空间生产逻辑可以从香港瑞安集团的“新天地”系列窥见一斑。上海“新天地”成功转型为中外游客必至的上海新地标,依赖的乃是地域空间(locality)与“无地域空间”(nonlocality)之间的互动逻辑。一方面,“新天地”这片六万多平方米的石库门建筑空间被相对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原石库门建筑的外形、砖墙、屋瓦和风格得到了尊重;但另一方面,附着于石库门建筑空间的上海人近现代日常生活却被掏空,填充其间的是典型形态的“无地域空间”或“跨地域空间”:连锁餐馆、品牌酒吧、时尚休闲场所和购物中心。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原来与石库门建筑空间密不可分的上海人日常生活却被资本的力量剥离出来,成为“屋里厢”(上海话“家里”的意思)博物馆供展示观赏的对象。这种将日常生活和地域文化“博物馆化”的背后,正是资本重绘后现代地域版图、改造地域空间的力量。在这一改写过程中,空间真正演变为一种漂浮的能指和可供任意附着和阐释的符号。无怪乎雄心勃勃的瑞安集团,已经或正准备克隆上海“新天地”的成功模式,将这一曲折复杂化了的“无地域空间”生产搬运移植到杭州“西湖天地”、重庆“新天地”、武汉“新天地”、成都“新天地”项目中,大规模改写内地都市空间的内核。
韩国、日本“大片”的跨境传播与消费
华语“大片”的兴起固然与中国内地的开放和两岸三地文化之间日益频繁的互动整合密切相关,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韩国新电影和以动画为主导构成的日本电影在区域和全球范围所取得的突破也不能不是重要的外在诱因。韩、日电影人得以在民族电影的固有领域即国际电影节和艺术电影院线之外另辟跨境商业影院展示渠道的成就,无疑助益了华语“大片”意识的形成,并一定程度缓解了中国内地电影人因90年代中期向好莱坞大片有限开放市场而生发的焦虑感。
韩国新电影对华语特别是中国内地电影的最大启示也许并不在于林权泽对“韩国性”的重新思考与再定义,也不在于金基德、李沧东等人的影片在国际电影节和艺术影片市场屡受青睐(因为内地第五代、台湾新电影和香港新浪潮自1980年代中期始已蔚成气候,广为国际电影社群所瞩目),而在于韩国电影自1986年《电影法》第六次修正版废止进口片配额、引入国产片银幕配额制度后,经过数年国产电影市场份额和产量下滑的危机,最终得以在本国跨国公司和风险投资资金以及国家电影促进政策的辅佐下,重新占据过半市场份额、在市场有限开放的背景中成功展开与好莱坞商业影片竞争的积极态势,使华语特别是中国大陆电影人体味到了与“狼”快乐共舞的可能性。
与许多国家一样,韩国电影市场也呈现为美国影片与国产影片两相抗衡的态势,二者之和超过全部市场的95%(韩国电影委员会KOFIC数据,2005年)。自进口配额制废止、好莱坞影片公司得以在韩国建立直接发行渠道以来,韩国国产电影市场份额逐步缩减,而美国影片的市场份额则一度扩展到了70%至80%。面对这一情势,韩国政府在积极策动全球化(“世界化”)进程的前提下,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振兴国产电影的举措,包括以《电影促进法》替代《电影法》(1996年;其中最重要的是引入分级制度,以此取代颇多诟病的审查制度)、设立重点为推动亚洲电影区域整合与交流的釜山国际电影节(1996年)和资助国产电影创作的“电影促进基金”、组建韩国电影委员会(1999年)以及通过《文化产业促进法》(1999年)等。详见达希·帕奎特(DarcyPaquet):《1992年至今的韩国电影业》(TheKoreanFilmIndustry:1992tothePresent),载朱莉安·斯特林吉(JulianStringer)等编:《韩国新电影》(NewKoreanCinema),纽约大学出版社,2005年,页32—50。同时,韩国政府还积极鼓励本国跨国公司介入电影创作与电影市场,使韩国新电影从一开始就迥异于过分注重艺术探索和作者电影、忽略电影商业效益和电影工业机制培育的台湾新电影。韩国跨国公司和风险基金介入电影市场的效用不仅表现为促使国产影片制作水准的大幅提升,而且也催育了韩国式大电影或娱乐公司如CJ娱乐、CinemaService和Showbox的出现与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