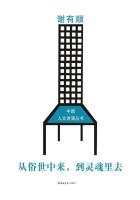从江南来到东北大兴安岭,一切都使人感到那么新奇:山是白的,路是白的,树也是白的,整个山野都被冰雪覆盖着。我们的国家真大呀,同是一个季节,南方是春水融融水秀山青,这里则是冰封千里白雪覆地。望着这北国风光,不由得使我想起幼年时的一件事。
那时我刚上幼儿班,记得一天早上醒来,看到窗上出现冰花便惊叫道:“快打开窗子吧,准是外边天冷,花跟树也想到屋里来取暖,让玻璃给挡住啦!”
阿姨听了一笑,告诉我们这是冰花。
“多美的冰花呀!”我和小朋友们赞叹着,把脸贴近玻璃窗瞧着,瞧着瞧着冰花模糊了,不见了,多么让人失望!
阿姨说寒冷才会出冰花!
回想起来这已是十几年前的事了。从那时起,在我幼小心灵里就对冰雪产生一种神秘感。今天来到这冰雪之乡,想到将在这里生活,心里既高兴又有些惧怕,谁知明天将走向何处?
我欣赏着林海雪景缓缓往前走着,从密林深处飞出一驾马拉爬犁,在我身边兜了个圈子停住了,问着:“是到女子采伐队去的吗?”听话音是个女同志,可是一看打扮就难以辨认了:大皮靴,大皮袄,长毛茸茸的皮帽子把脸都给遮住了。直到正冠时才看出她是个女性,留的是“朝天撅”。
我上了爬犁还没坐稳,只听她一声吆喝,马就四蹄踏雪跑了起来。爬犁就如同箭一般在银山玉树间穿行着,随着山的起伏任其飘落。
穿过一条条林带,越过一道道冰河,爬犁停了下来,催我说:“下来吧,若是喜欢坐爬犁的话,赶明儿我就把这差事交给你啦!”
她把我带进帐篷,又往地灶里塞了几块劈柴瓣子,说:“说话水就热,是喝是洗全由你。”说完就走了。
我一个人留在帐篷,便细心观察起这个家来。这里的陈设也别具一格,大联铺是架在伐木留下的树墩上的,有的树墩劈下一半,用乌拉草一围就成了沙发。让人不解的是把鞋全吊在靠近篷顶的地方,风摇帐篷晃,鞋也跟着悠荡。出于对姐妹们的关心,我便把鞋全解下来放在铺底下。锅里的水冒着热气,帐篷里温暖如春。这会儿身上虽然感到舒适,而暖过来的手脚却像狗咬一般。我打了盆水刚要去洗,姐妹们回来了,这个问寒,那个问暖;有的解行李,有的摊铺盖,有的还拿出当地的特产蘑菇猴头去炖狍子肉。
“瞧,当家的回来啦!”
话音未落,人已挑开棉帘站在了面前。原来当家的就是那个驾爬犁的姑娘。她拉我刚刚坐下,一眼就看到那些放在铺下的鞋子,喊道:“谁这样有眼力件儿,怕大伙儿不穿冰疙瘩咋的?临走我把鞋挂起来的,咋就跑到铺底下去啦?”可是一听这鞋是我放的,她不光是笑出了泪花,还抱住我又捶又打。这才知道她是个“老插”,否则手不会这样重。她还说帐篷里有三带气候:地面是寒带,中间是温带,靠蓬顶的地方是热带。
风雪兴安岭的第一天就是这样度过的。
林区的早晨是在伐木声中醒来的,透过枝叶的缝隙射进一道道阳光,投在青松、红枫、白桦、紫椴,以及黄菠萝等各种树干上,经过雪的映衬,斧锯的反照,条条光线交织在一起,绚丽多彩!姐妹们有的用锯伐,锯来锯往层层锯末儿阵阵飘香。有的用斧砍,一棵棵参天大树就在人呼山应中倒了下去。我便跑上前去用步子丈量树的身段,数着树的年轮,计算一架栋梁之材要经过多少个春秋才能长成。数着数着便问:“为啥年轮有软硬之分?”
队长边干边说:“松木节赛如铁,硬的年轮是冬天长的。”
我又问:“不是说树木落叶是冬眠状态吗?”
“从外表上看像是冬眠,可是里边的筋脉还在活动。冬天树木虽然长得慢,但木质坚硬。”她像是喃喃自语,又像是对我说:“不要以为大雪一盖万物就没有了生机,其实树木仍然在长,冰下的水也仍然在流。”
听了“老插”这番话,顿时感到天宽地阔,我爱上了这激流勇进的生活。
天渐渐暖了,一种报春的小鸟在林间鸣啭,雪也在悄悄地融化,我心里也像涌出一股春水,如同江南的溪流那么欢畅,便想跟姐妹们一块儿去踏春。偏偏天骤冷起来,刚化的雪水又结成冰。
一天早上,“老插”从外边跑回来,非要拉我去开眼界不可。我说天太冷。她说:“植树盼天暖,伐木愿天寒,天不冷谁帮咱们义务劳动?”硬把我拉出了帐篷。
穿过一道道林带,抬头一看愣住了:人来人往,正忙着往山上担水,再将水泼在槽状的山道上,汇成瀑布,结成一条沿山起落的冰坡。
“窜—坡—喽—!”喊声在山中交响着,一根根堆在山头的林木从那里飞出,沿冰雪滑道往下滑,撞得冰裂雪飞响声震天,就像那发射的鱼雷,而且是越滑越快,每当遇到障碍借着冲力又鱼跃而起,向另一座小山飞去……“障碍面前产生了飞跃!”我在心中默念着。
在我们归来途中,无意中看到一种不被人注意的小花,在谷底雪窝里默默地开着。姐妹们告诉我,这就是冰凌花。
这种花只有扣子那么大小,颜色也极为一般的小花,对我这个来自江南的人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可是当我走近仔细一看,却被它给惊呆了:这种花不光是开在风雪的山坡上,根还扎在冰凌上,仅有薄薄的一层土,就会长出挺拔的筋骨;只有初春一点热,就会绽开鲜花朵朵。
“多么奇妙的花儿呀!严寒的大兴安岭才会有这种花。”我心里感叹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