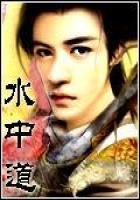连福本人也感到很不自在,要是过去,每天他都会来这里坐一坐,哄孩子玩儿,抽叶子烟,东拉西扯,等到把炕坐热了也就到了看马的时候了。可是今天他却感到无话可说,尤其是当着两个孩子的面,他能说些啥呢?直至看到梅嫂的手指被针扎破流血时,他才找到了话说,但却是对两个孩子说的:“快拿嘴给你妈嘬嘬!”
梅嫂听了这话虽然感到可笑,但很亲切,要是外人是不会说这种话的。便对孩子说:“你们不是爱听讲故事吗?那就听大叔给你们讲吧,到时候别说困就行。”
这话是对两个孩子说的,也是给连福听的。今天之所以这样留他,则是因为一些传闻搅动了她的心。
有人说夜里让连福看马是王大拿设下的圈套。也有人说那是陷阱。当时她听了一笑。心里说那圈呀套呀的到处都有,猪圈周围画着白圈,羊栏外边挂着柳条圈,那是吓唬狼的。各种套子就更多了,马尾套是套雁的,绳套是套马的。她还听人说过绳套还能套人,往脖子上一套背起来就走,东北那地方跟这叫“背死狗”。陷阱她没有见过,但是听人说过,那是给狼准备的。地上挖个坑,上边盖个门板,人在里边学羊叫,狼从人预留的洞孔里来掏羊,抓住狼腿拿尖刀一别,连门带狼一块儿背回家。她还听人说过,夜里闹狼是人招来的,怎么招法她不清楚,但知道狼爪的厉害,先扒膛,后掏心,狼爪子一挠三道血印。
当时连福也在想事,他想的是怎么摆脱这种局面,于是便讲起故事来,讲的还是那些老掉牙的故事。讲那种事一是说起来顺嘴,就是说走了嘴也听不出来。而且他讲得很快,就跟从竹筒里往外倒豆子一样。结果是他说的越快两个孩子越得伸着耳朵听。听着听着就到“且听下回分解”的时候了。当时要不是两个孩子拦着不让他下炕,就会急着守夜看马去了。
在灯下做活的梅嫂也在留他:“马累了还知道歇蹄,如今天也凉了,你也该在家睡个塌实觉了,到时候会有人替你顶班。你说是不是呀?”她用眼睛瞄着他。一听这话,连福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了。因为听话听音儿,她说的那个家不就是留他在这儿住吗?这可是让人戳脊梁骨的事。连福心里是这样想的,可是面对那双乞求的眼睛又难以驳她,只说了这么一句:“这是哪门子的事呀?”
两个孩子一看连福叔没有走,心里非常高兴,还说睡觉也挨着大叔睡。并且为睡觉的事还争了起来。英子说挨着大叔睡觉睡得踏实,不作恶梦,大叔过去当过兵。小宝则说连福叔是男的,男的跟男的睡一个被窝。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决定,就连面对机枪扫射都无所畏惧的谢连福,一听这话当时就蒙了。这可咋说哪?走吧?那会伤她的心。留吧?又不近情理,今后两个孩子跟他叫叔还是叫爸?他,既没有说走,也没有说留。却又给俩孩子讲起那些故事来了,讲这讲那,说来说去还是那些有关龙呀蛇呀神呀鬼呀的事,听的两个孩子不知是因为犯困还是害怕,往炕上一躺就睡着了。
看到两个孩子入睡,连福却拘束起来了。他觉得走也不是,留也不是,仍在没完没了巴嗒他那旱烟袋。直至听到了鼾声才说话:“这俩孩子觉睡得还挺沉,一边做梦还一边打呼噜,‘呼——呼——’跟小猫似的。”
梅嫂听了一笑,便将横躺竖卧的两个孩子往炕的一头推了推,说:“咱俩也睡吧,有啥话放到明天再说。”就把小油灯给吹灭了。
这会儿夜静极了,只能听到窗外的秋虫在鸣唱,那秋虫好像也不知疲倦,一阵高一阵低唱个没完。甚至把小河流水的声音也给压了下去。有时还能听到一两声雁的鸣叫,那是更雁在报警,别的声音就再也听不到了,直到夜里起风的时候这些声音才逐渐消逝。留在窗上的月影这时也变得模糊起来,接着狼嗥的声音也随风而至,“呜——呜——”像哭。
听到这鬼哭狼嗥的声音,连福“嗵”一下就坐了起来,然后便穿衣下炕,跌跌撞撞就从门里走了出去。望着窗上摇动的月影,梅嫂开始后悔了,当时怎么就没有拉他呢?哪怕是拉到他的裤带,或是抓到他一只鞋,或是……。其实刚才这一切一切都是由她精心安排的,只要能拴住他夜里不去看马,就是跟他明铺夜盖她也认可。都到了这份儿上还顾什么脸面?可是后悔已经晚了,只能是两眼凝视着窗外心里这么想着:怎么老天爷也不长眼,一到夜里就起风?
可是连福却不顾刚才这一切,提着那杆轰狼的鞭子就向村外走去了。当时他是顶着风走的,再加上肚里少食脚下没根,走起路来总是磕磕绊绊。可是他心里却这样给自己做着解脱:咱可是那打过江山的人,哪能听到几声狼嗥就不出热被窝?
说来也巧,当他来到看马的地点时,那狼嗥的声却没了。心里说狼也怕人。于是他又跟往日一样,抱着鞭子找个背风的地方一靠,又一袋接一袋抽他那叶子烟。
这时已经过了深秋季节,可是一到深夜还能听到雁的叫声,“咯儿嘎咯儿嘎”叫着从头上往南飞。叫出的声音很凄凉,是离群的雁在呼唤它的伙伴。
就在这时候,又传来狼嗥的声音。接着就看到马群拥挤着往一块儿靠拢,缩成一团挤成个蛋蛋。看来今天夜里这狼来了不少。若是三、五只狼,这么大的马群是不怕狼的,因为马群自身有一个防御体系。可是现在来的却是一群前来偷袭的恶狼,一下就把马群给冲散了。
在夜间放牧,马炸群的事倒是经常发生,比如头上突然响起一声炸雷,或是身边有一匹马突然受惊,都会使所有的马匹炸群,然后就毫无去向地四处乱跑,就跟夏天那跑马云似的。但他却从未见过马炸群像今天这样,一眨眼的工夫就都跑得无影无踪。到了这会儿,马跑远了,马群也散了,留在这荒野上的只有他连福一个人,心里也就越发惊慌,手里拿的轰马的鞭子打狼的棍子,在刚才追马的时候也给跑丢了,拿什么家伙去对付群狼?他紧张得不知如何是好,就连点火驱狼那常用的办法他也给忘了用了。幸亏那些狼都去追马,才使他捡了一条命。
就为这看马的事,梅嫂可没少为他担惊受怕,因为那是人家设下的圈套,是想让狼扒了他。这话梅嫂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向他讲的。可是连福却说:“人心都是肉长的,他能这样吗?”有关那个人是谁梅嫂她不便明说,也不能说,说了就会更伤他的心。她只能是夜夜等待,等待他平安归来。
连福又何曾不恋这个家?就是为他们娘儿仨,他才去看马的呀!
马群也是一个家族。这个家族只有在闹狼的时候才能显示出它的威力。每当到了这会儿,所有的马便自动散开各就各位。小马驹、病马和怀上驹的骒马被圈在马群的最里边。往外是骒马。骒马也是马群保护的对象。最外的一圈是骟马。尽管“骟马”这种马少了原有的那种雄性,但毕竟还是公马,到时候它们也会结成一道防线,头朝里屁股朝外,用马蹄来对付狼的进攻。而真正能起到护群作用的还得靠那些儿马蛋子,若是狼来攻击马群,它们就会扎起长鬃“咴咴”叫着冲上前去连踢带咬。只有这种占有欲极强的“儿马”才是马群的卫士。从小生活在草原上的谢连福,过去对待这霸群的儿马一向是以鞭子对待的,直到今天他才认识到儿马的作用。儿马护群靠的是连狼也惧怕的那种虎胆,那胆不在别处,就在它那两个“蛋蛋”里。人若是连那点儿胆量都没有,还算个男人吗?
就这样,他又以马为伴去熬那漫漫长夜。让人最难熬的是在天快亮那段时间,当地人跟那段时间叫“鬼呲牙”,天又冷再加上人到了这时候的困乏,那是最不好熬的。后来他又熬过了那个马缺草人缺粮的日子,牲口人都饿得一走三晃,连福仍旧在看马。不光是夜里不离马群,就连白天他也跟马群寸步不离。因为饥饿也会把人变成了饿狼,偷队里牲口的事也时有发生。谢连福作为村里的马倌,岂能眼看着那盗马贼不管?就这样,好多日子他也没顾得回村。
后来终于盼来相聚的日子。由于他相见心切,连自己的家都没顾得看一眼就去了梅嫂家,就如同是鹊桥相会。实心眼的谢连福他哪里知道?那扇门虽然同过去一样朝他开着,可是人却不知去向,只留下那口做饭的锅。
直到这时他才知道,梅嫂带着两个孩子已经离开了这里,回山西老家去了。得知这一消息时连福一下就蒙了,久久站在那儿发愣,怎么也没想到她会不辞而别。然后便望着梅嫂去的方向在心里嘀咕着:“人那还不如那大雁,大雁临飞的时候还叫两声呢!”他哪里知道梅嫂的不辞而别正是为他而走,常言说,一个槽上不拴二马。
从那以后连福就再也不去看马了,而且是成天在想,怎么才会使他们娘儿仨回到他的身边。想来想去他想到“龙盘蘑”。若是能得到这种宝物,梅嫂就会跟候鸟一样回到翠花宫的,这里才是你的家!想着想着眼前便出现一堆干柴,干柴又变成烈火,火里又出现一口被烧红了的锅,锅里还扣着一个大蘑菇和一条蛇。那条蛇被烤得无处可逃,最后便盘在蘑菇上了。于是那梦寐以求的龙盘蘑便出现在他眼前,如同乌龙盘柱那样活灵活现。
想到这里,连福就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揭下那口锅往背上一扣就走了,到处去找那能改变他命运的龙盘蘑……泥鳅看瓜河北省乐亭县,是革命先辈李大钊的故乡。从前打日本鬼子的时候,这里曾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
在乐亭县城北靠滦河的东岸,有个张家庄,是抗日根据地的边沿区。张家庄的抗日组织、民兵、妇救会、儿童团,多在夜晚活动。白天敌人来了就“跑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