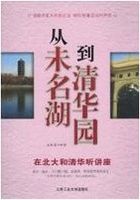礼拜天一大清早儿,北京城里那些以捕鱼为乐的人们,又骑着自行车驾着摩托车,远离闹市到北郊沙河撒网捕鱼了。一到河边,便听到从雾蒙蒙的河湾里传来振奋人心的喊叫:
“瞧咱网里这个儿!金翅大鲤鱼还是红尾巴的!”
立即有人呼应:“慢点儿拉网,别让它跑了。”
“跑不了,已经装进我的鱼护啦!”
接着便有人扯着嗓子大喊:“二头他妈—快拿大盆来呀!”
于是喊声四起一片欢腾。
其实并没有鱼。那是有人瞎咋呼呢!一惊一诈是渔人共有的毛病。同时也是感情交流的一种方式。渔人见面不说您早您好,那是客套。因此,一听到这喊叫声就倍感亲切,这声音在别的地方那是听不到的。
这里的景色也的确是迷人,河水缓缓地流着,水面笼罩着一层乳白色的雾。潜入水底的鱼在泥里找食吃,拱起的水泡泡像细小的珍珠。那些浮鱼更是悠然自得,身披霞光在水皮儿上漫游,荡起层层金色的涟漪。不时还有鲤鱼跃出水面,打个挺儿亮一下身段,银鳞一闪再扎入水中……这时扫来一阵小风,掀开蒙在河上的雾幔,显现出捕鱼的阵势。河里下着一道道守株待兔的粘网和用苇箔插的迷魂阵。迷魂阵的阵形如八卦回曲婉转,很像北边山上的长城。这时从上游漂来几个渔筏,一字排开正沿着河筒往下放,一边撒网一边赶鱼。其中有个叫“大黑李”的网片最大,只要一拧身网就出手,铺天盖地。这时他看到有个熟人在河边撒网,网很小,便说:“喝?小盖帘儿一个!”
此人是个眼镜先生,渔友们都叫他秀才。谁知他听了这话不但不恼,还笑笑说:“我哪儿能跟你大黑李比呀?我是给你轰鱼来的!”
就在两个人见面逗贫的时候,秀才就把网理顺好了,一转身一拧腰,网就朝渔筏飞了去,出手时网还是个死疙瘩,可是一接近水面“唰”一下就绽开了,把大黑李吓了一跳,差点从渔筏上栽下去。
秀才的话也来了,并拿腔拿调学着他师傅张老头的话说:“在我们白洋淀那地方,都这样儿撒网,过去撒网讲究穿一身白裤褂儿,打鱼回来还不许见到泥点儿,像你这撒网的可好,把扒上来的那点儿臭泥全糊在了身上,一点儿没有糟蹋!”
他说的那个张老头,在北京那成千上万的渔人里,可称得上是“祖”字辈儿的。在刚解放那年月他就以捕鱼为生。他没有自行车,不管出城打鱼路有多远,小扁担一挑—腿儿着。一头担着渔网,一头担着渔篓,逮回鱼来就沿街叫卖:“活蹦乱跳的新鲜鱼!”大黑李被秀才刚才这番话说得无言以对,便说你这知识份子改造得不错,会挖苦人啦!
北京人捕鱼是从三年灾荒那年月兴起来的。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捕鱼的人就更多了,上至政治绞杀场上的失意者,下至将被殃及池鱼的平民百姓,很多人都加入到这个行列。而被称作秀才的渔人,尽管他在教学和写作上曾有过一段辉煌,但却够不上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才得以幸免。后来便成了这渔人大军中的一员。其实这也在受批判之列,当时有个口号叫“抓游鱼”。
他们一边撒网一边逗着,开心极了,逮鱼开心两不误,不知不觉便来到了沙河湾。话才暂告一段。因为到了卧鱼的地方,得来真格的啦!打鱼的口头禅是:有鱼没鱼三千六百网。到处回荡着渔人的高声喊叫。就连秀才那块小网也扣上了一条大鱼。网刚落到底就“咕嘟咕嘟”向上翻花,跟开了锅似的。这可是一条大鲤鱼,正在网里“栽桩子”呢!
“栽桩子”是大鲤鱼独有的一种绝技,只要是被扣在网里就往泥里扎。等网过去之后,再从泥里钻出来溜之大吉。因此,鲤鱼被称作“鱼中之贼”。可就怕遇到“渔鹰子”那种人,扎到河底去抓它。而秀才却没有这能耐,只能是站在河边干着急。
按说渔人是很注重友情的,比如今天谁没逮到鱼,不用张嘴就会有人送上几条。绝不会让你空手回家挨老婆骂。可是一到出鱼的时候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因为河边没大小,职位无高低,谁逮得鱼多谁受尊敬。
为此,每次逮完鱼都要把鱼摆放在一块儿,看看谁逮得鱼多,逮得多的自然高兴,没逮着的也有话说;“我本来扣上了一条大鱼,一大意让它跑了。放了放了吧,等哪天想吃鱼的时候再来拿它。”
渔人大都有爱吹的毛病,而且逮起鱼来贪得无厌,逮了一条想着一兜儿,逮了一兜儿想着一篓儿,有人说把这河里的鱼全归你行了吧?那也不行,逮完河里的还有海里的呢!因此,一看到秀才网里有鱼便都围了上来,一个个驾着网在一旁瞧着,等待捕捉那条漏网之鱼。
就在这时候从对岸游过一个人来,嘴里喊着:“这条大鱼可归我啦!”
此人的外号叫“迷糊”。迷糊是个爱凑热闹的主儿,凡是有热闹的地方少不了他。别看他网撒的不咋样,可是个热心肠,常爱下水帮人抱个鱼啥的。今天他是不请自到。用的是笨法子,连网带鱼一块儿往上抱。终于将一条大鲤鱼抱上了岸。
秀才很受感动,“兄弟,咱没的说,晚上到我家喝酒,谢谢啦!”
“甭卸(谢)啦,还是套着喂吧!”迷糊说完这话,又学着“狗刨儿”在众人面前游了起来。两脚在“噗咚噗咚”打水,水溅得老高。
“迷糊!你积点德好不好?”大黑李嘴里这样说着,手里的网就撒出去了,同时又赶上迷糊戏水往前一蹿,正好把他扣在网里。大黑李便喊了起来:“瞧我网里这条大鱼,一百多斤!”
众人也在跟着起哄:“快往筏子上拉,别让他跑了。”
迷糊听了这话不但不恼,还来了情绪,忽而来个鲤鱼打挺,忽而来个虾米伸腰。当渔网快把他扣在里边时,他又来个蛤蟆入水往下一扎,便金蝉脱壳游了出去,一个猛子又扎到别的水域跟人凑热闹去了。难怪每次打鱼回来老婆骂他:“你就犯迷糊吧,起大早出去打一天鱼,这鱼都到哪儿去啦?”
这天鱼逮得顺,到了晌午便相继上岸,吃干粮,侃大山。他们这些渔人是最会享受的了,大家围坐在松软的河滩上,或是开着小黄花的草地上,各自拿出带有家乡味儿的食品供大家品尝,他们跟这个叫“共产主义生活”。
大黑李拿出一瓶二锅头,用牙启开盖儿,自已先张了个喇叭,然后巴嗒着嘴说:“别看咱们这些臭打鱼的浑身上下带着腥味儿,可是谁能跟咱们这样自在?水上一漂,酒一喝,鱼再一撞网,给个县太爷也不换。”
秀才也深有同感地说:“不招灾,不惹祸,逍遥自在渔人乐!”
秀才在家里是从不喝酒的,他怕这烈性酒伤害他的大脑神经。今天他是见酒就馋,而且诗兴大发,真是酒不醉人人自醉。
这沙河湾的景色也的确是令人陶醉,他头枕着湿漉漉的渔网往河边一躺,便高枕无忧欣赏起这里的风光。与北海、昆明湖相比,这里的景色虽算不上美,但满眼一片绿色:远处的山是绿的,水是绿的,河堤上的树也是绿的。小风从庄稼地里吹来凉爽得很,还带着花香。同时还传来布谷鸟的叫声,那声音好听极了,像是对着瓶子口儿叫,声声带着水音儿。
随着渔人上岸,河水也渐渐变得清澈,隐匿一时的山影又浮了上来,那沿山起伏的长城也清晰可见,时而浮上水面,时而又沉入水中。如果把长城比作龙的话,这条龙只有在这里才有了生命。
水中的景物在他眼里也很奇妙,一切都是倒着的:就连河边的蒲草堤上的树,也是根朝上头朝下。河面就如同是个巨大能包罗万象的魔镜,使一切都在变幻。就连身边的那些渔友,到了这会儿也变得让他难以辨认,就如同在哈哈镜里看到的一样,会使人变瘦,变胖,变长,变短,变成己非己像非像,似像非像的怪模样……而大多数渔人却没有这种感受,女人才是他们下酒的作料。河边的话恕不奉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