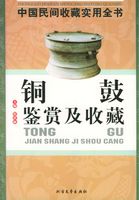2006年6月,上海国际电影节以“合拍片”为主题展开了一系列活动。一方面显示了上海国际电影节对“国际”身份的强调,同时也回应了当下中国电影市场中“合拍片”壮大的事实。中国电影合作制作公司总经理喇培康介绍道,在中国方面,对合拍片给予了一系列的政策优惠。合拍影片拿到了放映许可之后,就可以像中国的国产片一样在中国市场上发行放映,而不需要像进口片一样通过进口渠道进入中国市场。在中国市场上,合拍影片发行的票房分账比例要远远高于进口大片,另外,合拍影片有资格参与政府华表奖的评选,而且合拍片的片方在中国市场上获得的票房,只需要交纳10%的外国企业所得税,税率从20%降到了10%。孙轶玮:《合拍片成中国电影“新宠”》,《瞭望东方周刊》2006年7月。喇培康还介绍说:“2004年,中国市场票房排行前三位的影片都是合拍片;2005年,中国市场上票房排位前四位的影片有三部是合拍片;合拍片以10%到30%的数量创造了30%到40%的票房。”同上。
合拍片是在WTO规则直接影响下的制度设计。它来源于中国经济领域中对海外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的预期,是一种典型的新自由主义的产业观念。“市场无国界”的全球化观念也是合拍片制度设计的观念前提。当然,其中还潜藏着一种“以市场换文化”的民族主义意图。制度设计者还希望中国电影可以从中学会国际化操作规则,成功开拓国外市场,增强自身的产能和市场容量。一个民族国家在电影产业上,迅速开放边界,允许合拍片,而且以让税的方式鼓励合拍片,这在后WTO时代外国电影引进数量逐年递增的情况下,意味着中国电影的开放已经是全方位的。借由合拍片在劳务、场景、故事、投资、发行等方面的合作,中国电影放弃了对边界的固守,借助国际市场,把中国电影输出海外,进一步融入到“世界主流文化”中去。作为一种能让各方面都得利的方式,“合拍片”获得了道义与利益的双重支撑,并正以一种强势的姿态,进入到中国电影工业的结构中。
但这种一厢情愿的产业设想并没有在现实中产生理想的结果。当下中国电影的票房大跃进只能在国内票房上做文章。中国电影海推公司总经理周铁东认为,中国电影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海外市场。去年,有47部影片走向了海外,其中,有46部是合拍片,海外销售和票房达到35.17亿元,但这些收入,对于中国电影产业并无太大帮助,因为大多数的收入,并不能回到中国电影的口袋里——拿成龙主演的《功夫梦》为例,这部电影在国内票房平平,但是在美国,却实现了超过1.4亿美金的票房,但根据国际合拍的通常规则,这1.4亿美金都进入了美国人的腰包。周铁东表示,目前中国电影的海外市场发展水平也跟美国1970年代类似,那时,美国电影的海外票房也只有国内票房的1/3。他认为,是时候加强华语电影在海外市场的拓展了。《周铁东:电影的合拍与海外市场定位》,文资网http://www.ccizone.com/ccizone/2010/1123/166.html。
这种结果恐怕让政策设计者始料未及。本来也许可以令政策设计者警觉政策设计视野的盲区,调整下一步政策设计的方向和目标,但是,一种华语电影的概念已经充分发酵,并制约了政策设计者的想象力和对客观情况的判断。当下政策设计者的唯一参照是好莱坞电影工业,当初合拍片的设计就脱胎于对好莱坞电影工业模型有计划的移植,所以,遇到问题,仍旧执著于美国电影工业的样板,把问题限定在“加强华语电影在海外市场的拓展”之上。
“合拍片”制度设计的基础是一系列抽象的原则和价值,而“合拍片”的对象可欧美、可日韩、可港台等,而这些选择秉持的原则和价值,由于文化因素的糅合,实际效果截然不同。这正是“华语电影”概念在产业上真正传播与产生效用的时机。与欧美发达电影国之间的合拍经验,如上所述并不成功,基本上没有达到像《卧虎藏龙》那样兼具商业与文化影响力的效果。以中美合拍片为例,基本上都是“形式合拍”,而未见融汇合作双方制作理念、文化诉求、发行双赢策略等方面的“实质合拍”。有些合拍片如《面纱》等,基本上只是徒具合拍片的外形,从编、导、演等电影各色内部分工,到影片的市场定位和文化诉求,无一不是美国公司决策,中方元素一般只提供东方主义化的“老中国”外景,和一些装饰性定型化的配角功能。也有一些合拍片如《伯爵夫人》等,名义上达到了双方的共商、共享,中方依旧处于被支配的地位,更不用说分享不到一个商业和文化的主体地位。中方的合作方一般是在价值观和历史观都缺乏主体性、趋附对方价值观和历史观的一群影人,因而常可以看到一些以二战为背景的故事题材,如《庭院里的女人》、《黄石的孩子》等,中国的形象都显得单调而漂浮,没有历史质感。
中美合拍片的经验是否是“华语电影”概念的“膨化剂”,有待进一步研究。“华语电影”概念借由一个虚构的主体,却能发挥强大的动员能力。此动员能力来自概念中的民族主义的驱动力。在“大中华”内部寻求共同的文化价值认同,比趋附一个缥缈的全球化的“普世价值”,可操作性要强得多。“华语电影”观念是民族主义的“价值理性”与“合拍片”的“工具理性”的结合。因而,在适当的时机开始被传播,并在传播过程中耦合多重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势力,到如今已经蔚为大观。根据电影家协会编的2010年出版的产业报告,截止2009年底,中影在这一年中,合拍公司共受理合拍片、协拍片立项申请77部,获电影局批准立项的合拍片、协拍片共67部。立项的影片包括9个国家和3个地区的合作伙伴,其中与港澳台合作数量最大,有48部之多,且占据了票房排行榜的前列。可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港台与大陆间的合拍片将占据中国合拍片的主体。而其中,香港作为早年的强势电影地区具有更多与内地合拍的机会中国电影家协会产业研究中心编:《2010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中国电影出版社,2010年,页37。。
早在2003年,《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即CEPA规定:纯港片在内地发行将不再受配额限制;香港与内地的合拍片可视为国产片在内地发行;合拍片允许港方人员增加所占比例,但内地主要演员的比例不得少于影片主要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故事不限于发生在中国内地境内,但情节或主要任务必须与内地有关。合拍片在内地与香港之间受到坦然的鼓励,合拍片在这里承担着文化统战与为香港经济输血的双重功能。
“华语电影”是大陆、香港、台湾学术界的创造。本来,学术界开始关注“跨”、“泛”叙事,来源于一种“去民族主义”的文化动机,但是“华语电影”意图跨越的是先前历史叙述中无所不在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壁垒,它暗合了“大国崛起”式的民族主义想象图景。这看似有点儿矛盾,其实正是以规避政治歧见即“去边界”的方式实现对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重构。而对于香港电影而言,民族主义话语更多是一种伪装,实质上可能正吞食着民族主义主体的民族主义的基础。政策制定者虽然明白香港电影人民族主义信念的实用主义面向,但仍旧希望借由商业的联合,达到文化的逐渐融合。
这是一个吊诡的方式,“华语电影”作为一个“免检”的概念,需要从工业与文化的双重视角中得到检视。当政策设计者从中美合拍片的后殖民主义视角移开的时候,“华语电影”的合拍片似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替代。“华语电影”轻易地擦除了“民族电影”的边界,意欲以一个想象中的文化概念覆盖原来民族国家电影工业的清晰所指。实际上,“华语电影”借助已经渐趋主流的新自由主义观念使自身合法化,掩盖了事实上难以视而不见的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利益输送关系。CEPA之后,香港电影成为大陆电影市场的熟面孔,在大言玄玄的旌表文字上,香港电影在大陆的票房也计入国产电影的票房。一个原来国产电影的“他者”,忽然变成“主体”的一部分,期间文化的差异及某种程度的融合已经进入到中国电影研究的视野。香港电影的“伤城意识”是1997回归后,一直以来不绝如缕的文化表述,虽因市场融合出现松动,但根底似乎未变。如《十月围城》中对“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想象性叙述,折射出香港1997后对“母体文化”的婉转期待。潜藏的“中国历史”观似乎并未随合拍片实践而稍有改变。而像《单身男女》这类合拍片中常见的轻喜剧,对大陆的文化想象始终没有摆脱香港的“主体”精神,并成为复活与扩张香港“主体”精神的有力载体。从香港电影可以窥见所谓“华语电影”概念的某种意识形态前提。
“华语电影”工业还可能从另一个方面成为好莱坞文化的中介。“意识形态的终结”并没有像语言一样成为各方共识。在这种情况下,“华语电影”成为好莱坞工业及其文化的缓冲地带,甚至是好莱坞工业及其文化在中国本土化的工具。电影工业的“去边界”怎么与现实政治中的“重置边界”不生冲突呢?即便是在“华语电影”的观念推广几近成功的时刻,电影工业中的不同利益主体关系仍然变得越来越显豁。在外围经济环境开始注重扩大内需的时候,中国电影是否也存在减少外部依赖、扩大内需的问题呢?
民族性/香港性的南下北上:(新)少林寺电影的启示
陈家乐,香港浸会大学博士。
一少林电影的寻钩
据《少林寺电影备忘录》一文法兰西胶片等:《少林寺电影备忘录》,《香港电影》2010年12月第37期,页32—39。少林寺最初呈现在电影中,可能是已失传的默片《火烧红莲寺》(张石川导,1928年,明星电影公司出品)。《火烧红莲寺》改编自平江不肖生的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如今,张石川版的《火烧红莲寺》早已失传,作为神怪武侠片的鼻祖,昔日是否曾在电影中出现过少林寺的光影印记已不得而知。直至1950年11月6日,香港诞生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正宗的少林寺题材电影,即是由南海影业公司出品、友侨影业公司摄制、胡鹏导演的《火烧少林寺》。
70年代,港片逐渐复兴岭南文化,张彻导演的《方世玉与洪熙官》(1974)、《少林五祖》(1974)、《少林寺》(1976)、《南少林与北少林》(1978)开少林片热潮。其后,南派刘家良、武指/导演唐佳等,皆有成功作品:《少林门》(吴宇森导演,1976)、《少林木人巷》(陈志华导演,1976)、《少林三十六房》(刘家良导演,1978)、《少林英雄榜》(何梦华导演,1979)、《少林搭棚大师》(刘家良导演,1980)、《少林与武当》(张彻导演,1980)、《少林寺》(张鑫炎导演,1982)、《三闯少林》(唐佳导演,1983)、《少林传人》(唐佳导演,1983)、《五郎八卦棍》(刘家辉导演,1984)、《少林童子功》(薛后导演,1984)、《少林小子》(张鑫炎导演,1984)、《木棉袈裟》(徐小明导演,1985)、《南北少林》(刘家良导演,1986)等。可见,从1974至1986年间,整整十多年,皆是少林电影的热潮期。还有其他反类型/类型变奏的少林片,如《花旗少林》(刘镇伟导演,1994)、《新少林五祖》(王晶导演,1994)、《少林足球》(周星驰导演,2001)等。
众多少林寺电影里,《少林寺》(张鑫炎导演,1982)是无可置疑的代表作,其后,还续拍《少林小子》(张鑫炎导演,1984)及《南北少林》(刘家良导演,1986)合称为“少林寺”系列。至2011年,才有《新少林寺》(陈木胜导演,2011)。而《少林寺》和《新少林寺》都是正式获少林寺授权拍摄的“北派少林寺”电影。
二创作思维的比较
《少林寺》的源起,由当年时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廖承志提出的。据沈容(日期不详)在《廖承志与〈少林寺〉》一文(原载《南方周末》),她说:“他(笔者按:廖公)对武打电影,情有独钟。廖梦醒大姐曾告诉我(笔者按:沈容),他们姐弟两人都曾经跟孙中山的保镖马相学过武术,所以他懂得武术,喜爱武术。他看了香港著名武打影星李小龙主演的影片《精武门》后,赞不绝口,还说,这不是一部很好的爱国的影片吗?廖公要求找有真功夫的人来演。”沈容:《廖承志与〈少林寺〉》,银都机构主编:《银都六十(1950—2010)》,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页360—361。在此建议下,时任“中原”董事长的廖一原率先接下重任,在他的决策下,派出薛后、卢兆璋两位编剧前往少林寺实地采风,最终选择“十三棍僧救唐王”的壁画题材发展成剧本。
据张鑫炎导演(2010)在《谈〈少林寺〉》一文。他说:“‘文革’期间,我们公司有个口号,说就算戏院里只有一个观众,也要拍‘为工农兵服务’电影。可是,香港只有英国兵,工人生活我们不懂,香港农民也很少,编导们都很痛苦,也想去写,也到工厂和农村去生活,但要是搞不好。那时,我们就去请教廖公(廖承志)[当时,廖承志担任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夏公(夏衍)这些老前辈,问我们到底能拍一些什么片子。廖公便提出拍《少林寺》,因为武术是全世界老百姓都能接受的。”张鑫炎:《谈〈少林寺〉》,银都机构主编:《银都六十(1950—2010)》,页359—360。这样,便搞定了开拍以少林寺为题材的电影。
《少林寺》可说是一个异常简单的故事,根据“十三棍僧救唐王”而创作。讲述隋唐年间,群雄逐鹿中原,争为霸主。王世充拥兵东部(古洛阳)潜号郑王,施行暴政,民怨沸腾。著名武术家“神腿张”抗暴助义,为郑王侄王仁则陷害杀死,其子小虎亡命嵩山,垂危时为昙宗(于海饰)所救。小虎在疗伤时,无意中发现昙宗偕十一棍僧禁苑练武,各怀少林绝技,小虎心喜复仇有望,请昙宗纳之为徒,遂落发为沙弥,法号“觉远”。觉远本为俗家子弟,连番犯戒,却在危难中,联合昙宗及各师兄,救出李世民,打退王仁则,保卫少林寺免被火烧。最后,李世民称帝,许少林寺从此公开学武,觉远也正式了断和少女白无瑕(丁岚饰)的感情,皈依佛门。
其实,《少林寺》的情节模式,基本套路不外乎:
一、忠良义士的孤子(小虎),避难于本是尘外之地,超脱于江湖恩怨的少林寺、太平安逸的少林寺也因收留他而惹上各种烦难,最终,王仁则意图火烧少林寺,也由他来保卫少林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