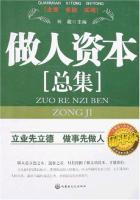总之,在我看来,加缪对作为哲学问题的自杀的论说与其说是自杀学领域的新贡献,不如说是对纷繁复杂的哲学思考的还原。它引导现代生活中一系列琐屑的哲思归零为一个根本性问题,即对生与死、善与恶、美与丑的考量。在“自杀之眼”的观照下,一切肤浅、一切平庸、一切无谓的饶舌都显得如此多余,只有无尽的黑暗与无边的光明在恒久地诱惑、启迪与召唤着我们。正如加缪以诗性的语言所表达的,“假如精神应当遇到黑夜,那宁可是绝望的黑夜,尽管这种绝望是清醒的;那宁可是极地的黑夜,精神的不眠之夜。从中也许会升起白色而贞洁的亮光,以智力的光辉把每个物件照得轮廓分明”(页105)。是的,自杀,一个最严肃的哲学问题,它真正要回答的是生命的价值、选择与依靠问题。易言之,作为一个靠文字安身立命的作家,加缪以自杀为切入点,实际上关怀的是现代人的生活状态与生活意义。当我们以坚韧与执著在这个世界上烙下印迹之后,当“数量伦理学”超越了人生的荒诞之后,当自杀不再是黑暗现实中的必然选择之后,我们重新拥有的是一种生活的发现,是一种我们久违了的生活方式。
三加缪的思想源泉
虽然加缪在《西西弗神话》的开篇几乎一笔勾销了整个哲学,但这绝不说明其思想观念是凭空出世的,更不意味着他对“荒诞的人”的认识是主观臆想的结果。实际上,正如波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耶日·科萨克所发现的,“加缪是从历史的真实以及对之所作的艺术和哲学虚构中,从古代神话和福音诗中,为他描写人同社会邪恶以失败而告终的斗争诸阶段的剧本汲取题材的”耶日·科萨克:《存在主义的大师们》,王念宁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页133。。换句话说,与一切卓有建树的思想家一样,唤醒加缪思考“作为哲学问题的自杀”的灵感之源,或者说影响其思想旨趣的精神之根,同样既不是单一的又充满着内在的悖论。在这部分里,我将简单地归纳出如下结论:希腊悲剧精神、基督教救赎信仰以及变幻的时代风云是构成加缪思想的三个主要源泉。
希腊是加缪永远的精神家园。在那个璀璨夺目的时代里,荷马史诗、希腊悲剧以及柏拉图哲学等共同构成了一个无限丰富的立体世界,以至于英国哲学家罗素谈到希腊文明时,语气都显得崇敬而艳羡:“希腊人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是大家熟知的,但是他们在纯粹知识的领域上所作出的贡献还要更加不平凡。他们首创了数学、科学和哲学;他们最先写出了有别于纯粹编年表的历史书;他们自由地思考着世界的性质和生活的目的,而不为任何因袭的正统观念的枷锁所束缚。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如此之令人惊异,以至于直到最近的时代,人们还满足于惊叹并神秘地谈论着希腊的天才。”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页24。与之相类,加缪对希腊人、希腊思想的情怀同样炽烈而持久。少年时代在大海边嬉戏时留下的美好印象,20世纪欧洲文明遭受的前所未有的摧残与伤害,萨特阵营以历史的名义对自己的排挤,这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让他无限追怀遥远的希腊人与希腊文明。可以认为,希腊精神对加缪的影响体现在其思想的诸多方面。无论是写作方式还是思想基点,无论是对生命的讴歌还是对丑陋的批判,加缪的作品都洋溢着一股来自爱琴海的咸湿的海风味道。在本书第九章,笔者将以加缪的一部作品为例,全面阐述加缪的希腊情结。
这里只想围绕希腊悲剧精神这一个侧面展开分析。早有学者公允地指出,“古希腊作家的生命力犹在,其标志就是,在至关重要的几个世纪里,通过罗马人对希腊悲剧和喜剧的仿作,通过对文学批评不断加深的认同,他们对欧洲戏剧的发展发生了间接但却是多方面的影响”F.I.芬利主编:《希腊的遗产》,张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页134。。其实,加缪对希腊戏剧的继承并不局限于修辞、格律等外在形式方面,其悲悯人生、洞察存在的内在精神更让他神往。在他看来,希腊悲剧不仅深刻地反思了人性,而且达到了艺术所能达到的第一个高峰。在《反抗者》中,加缪饱含深情地说:“艺术至少告诉我们,人不能仅仅归结为历史,人在自然界的秩序中要找到存在的理由。对他来说,伟大的农牧神并未死去。他最本能的反抗肯定了所有的人共同的价值与尊严,同时为了满足对单一性的渴求,执著地要求享有真实中未受损伤的一部分,其名字就是美。人们可以拒绝全部历史,却可以与星辰和海洋融洽无间。”加缪:《反抗者》,吕永真译,见柳鸣九、沈志明主编:《加缪全集》散文卷Ⅰ,页334。可见,长期浸润于希腊悲剧中的加缪,在其中发现的核心词汇永远是“自由”与“美”。借助对希腊精神的弘扬,他要在荒诞世界的边缘呼唤一种自由精神。由此可知,加缪概念中的自然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大海、山丘与沙滩,而是蕴涵着人类创造精神的生命力。
原始的生命力永远让加缪神往,正如他神往着做20世纪的希腊人一样。正是从希腊悲剧精神中继承的悲情气质引导他走上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创作之路。通过创作,他更深地感受了荒诞,也更彻底地克服了荒诞。依照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说法,“思想是最大的优点。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并且按照真理行事,听自然的话”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三联书店,1988年,页29。。所谓的“听自然的话”实际是主张在自然中感受神秘,按照自然的规律安排人类的事务。加缪所延续的正是这种原子论思想,而反感以历史的名义实施暴政,主张像希腊人那样回到自然,在自然之美中感受生命的伟力。可以说,希腊悲剧精神对于加缪,不仅是创作的动力与源泉,而且是孤独心灵的最终归宿。有人说,加缪是一个昙花一现的时代思想者。这当然是有道理的,因为他的思想起点的确属于这个特异的时代。但是,在并不乏欢笑与喧闹的生命之旅中,加缪其实是个独行者,希腊悲剧精神深深地笼罩了他的一生。然而,也正由于此,加缪的诸多自救式作品反而成为最动人的篇章。
如果说信仰与理性是西方文明的两大转轮的话,那么两千年来基督始终以其道成肉身的神秘启迪着一种十字架上的真。这种“真”在通常所谓的“无神论存在主义者”加缪的思想中的烙印其实很深。美国学者威廉·巴雷特的成名作《非理性的人》中如下这一番概括多么像是为加缪量身定做的啊:“在牛顿和理性女神的宇宙中,也有一些不幸的灵魂,因此,我们现在必须倾听他们的哀怨。我们可望听到的,首先是那些诗人的声音。在哲学家能够思想存在之前,诗人是他的见证人。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特殊诗人力图显现的,正是今天历史地属于我们的存在处境。他们正以诗歌的语言拨弄着我们自己时代的先兆之弦。”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研究》,段德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页125。的确,我们在加缪的许多知名作品如《鼠疫》、《误会》、《堕落》与《卡利古拉》,以及他所改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均可以很明显地读到对“恶”的揭示(来源、表现与去向),对救赎的探讨(方式、方法与信念)和对灵魂的发现(途径、源泉与可能)。应该承认,所有这些归属于基督教的主题不仅拓展了加缪的思维广度,而且增加了他的写作深度。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加缪实际上从来没有弃绝过对他拒绝追随的基督教主题的思考。
研究者发现,基督教对加缪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另一个证据是,他甚至还撰写过一本不大为人所知的论著《基督教的形而上学和新柏拉图主义》。这是加缪于1936年5月在阿尔及尔大学为获得研究生学位和进一步深造而提交的一篇长达100页的论文。从这篇论文可以看出,帕斯卡尔、普罗提诺、奥古斯丁等为加缪最初的哲学思想提供了宗教根源;其余思想家,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克尔凯郭尔、舍斯托夫和雅斯贝尔斯则促成了加缪后期思想的发展。这篇论文尽管存在缺陷,但从中仍能看出加缪对这些宗教思想家的亲近与热情——他们所致力于解决的不完美的世界与完美的上帝之间的和谐统一问题令年轻的加缪激动不已。理查德·坎伯:《加缪》,马振涛、杨淑学译,中华书局,2002年,页19—37。此外,在加缪写给比利时神学院学生的一封信里,我们甚至还颇为意外地读到这样的表达:“告诉你自己,在今天的西方世界中有四分之三的人不信仰上帝,而且人们必须试图有意或无意地陈述自己的思想。现在是该为有罪的人做些事的时候了——我想上帝曾经是,现在仍是人类伟大的良机之一。但那些背离上帝的人必须找到另一条出路,并且必须在没有太多自豪和幻想下这样做。”Oliver Todd, Albert Camus: A Life, tr. Benjamin Ivr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7, p.215.从这些迹象可以看出,加缪将自己的职责定位于照顾那些既无信仰、也不确信上帝存在并且没有希望得到上帝恩典的人。
加缪始终没有摆脱对基督教的迷恋,对此我们该如何理解呢?一个似乎合理的回答是萨特在《情况种种》中对加缪的下述评价:在加缪的书中存在一种对上帝的仇恨,因此,可以称其为“反有神论者”,而不是“无神论者”。换言之,对于一个无神论者来说,上帝与他毫不相干;而对于一个反有神论者来说,上帝则与他有着绝大干系。这也意味着,一个反有神论者所坚持的是上帝的不在、上帝的沉默,或是上帝仁慈的缺乏在世界上留下的不容忽视的大空洞。对于这个问题,理查德·坎伯从比较视野出发作出了富有积极意义的发现:“与萨特相同的是,加缪认为没有什么强制性的理由去信仰上帝,更无理由去相信一个来世。但与萨特不同的是,加缪不能确定上帝是否不存在。加缪承认有三种可能性,而且这三种可能性让他感到恼火。如果没有上帝,那么人类就被抛入一个对人类需要漠不关心的宇宙之中;如果上帝保持沉默或者上帝只与一些人交谈并拯救一些人(上帝所选择的人),那么上帝就忽视了其余的人。”理查德·坎伯:《加缪》,页37。这正是加缪的思想悖论。
加缪思想的第三个源泉颇为庞杂,既包括变迁的现实政治,又包括深邃的存在哲学,同时更少不了卡夫卡等小说家的现代作品。因此,我这里将它统一称为变幻的时代风云。现实政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思想的激发与实践上,而加缪与存在哲学则有着复杂的渊源关系。众所周知,存在哲学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人的生存的思想,处境意识与生存意识是其思想的起点。这两种意识是与现代的生存危机感相伴随的。长期以来,本质主义借助对本质标准的设定,为人提供了稳定的历史进程与生活方式。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一劳永逸地无须为时代、环境和自身的生活多加思考。但是,“本质”的设定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标准”、“规律”与“习惯”常常给渴望自由的心灵造成无可抑制的压抑。这种情况促使存在主义思想家采取另外的方式来把握自身,转而关注以往被忽略的情绪、身体等现象。
柏格森哲学中突出的反理性主义和直觉主义为加缪所欣赏。尼采对基督教的无情批判、对成见与旧的道德标准的攻击,也引起了加缪的共鸣;但他对尼采的权力意志和超人哲学却不苟同,他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具有毁灭性的虚无主义哲学。在克尔凯郭尔那里,加缪不仅找到了刻画孤独、疾病和死亡的共同话题,而且认同他的“应该研究孤独个人”的观念,但又对其沉溺于上帝中以期得救的方式并不赞成。此外,他对克尔凯郭尔“人生三阶段论”中的审美价值层面也颇有异议,并在自己的哲学随笔中给予了鲜明的颠覆。此外,前文曾经谈到,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等人的思想同样滋养过加缪。例如,海德格尔对人的境遇和命运、人内心的破碎状态的关注,以及用“焦虑”来概括“此在之在”,认为它是人生在世之基本状态的观念,还有雅斯贝尔斯哲学中的生存概念、对历史进步论的反思与否定等都深刻地影响了加缪。值得注意的是,加缪吸收了上述哲学的部分思想,但又和它们始终保持着相当的距离。
索伦·克尔凯郭尔(1813—1855)
在文学渊源上,对加缪最直接、最显著的影响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加缪认为前者是现代悲剧的创始人,他的作品努力揭示现代人的苦恼、彷徨和软弱,揭示出人类的历史命运,不断地给予我们生活的希望和勇气。他花了数年工夫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改编成剧本在舞台上演出。加缪也对卡夫卡作品有过专门阐释,即那篇附于《西西弗神话》之后的研究文章《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和荒诞》。他充分体会到卡夫卡作品中的“悲剧性和日常性、荒诞和逻辑之间永久的摇摆”,十分欣赏卡夫卡的“客观性”风格,并自觉地在《局外人》中加以模仿——流放、死亡、孤独与自由是他们作品的共同主题。但正如波兰哲学家W.查列夫斯基所指出的,加缪与卡夫卡的思想也有着明显的区别:“卡夫卡只看到命运多舛的人,而加缪则以为,人虽然是命运多舛的,但他不顾这些,仍然要斗争。而且这不是毫无意义的斗争。因为虽说人生是荒谬的,但在人的心中,也同样根深蒂固地蕴涵着一种对于俯首听命的反抗。一旦有人发现,没有任何美好崇高的目的来填补他自身和他的命运之间的鸿沟,这条鸿沟上面,不能架设一座通往天堂或人间乐土的桥梁,造反精神便油然而生。然而,与对荒诞范畴也表示无能为力的卡夫卡不同,加缪在拒绝超验性的谎言时说,人,并且只有人,才天生拥有造反能力。”W.查列夫斯基:《希望的变种》,华沙,1968年,页155—156,转引自耶日·科萨克:《存在主义的大师们》,页129。
总之,无论师承何人,无论源出何处,加缪的问题意识始终如一。如何在荒诞的人世生存中拥有积极的意义是其人其作的不懈追求,而勇敢地承担个体的命运,以挑战的姿态超越荒诞,用艺术的笔触描写人生的悲剧性与幸福的不可期,最终建立一种道德、明智的哲学是自己不可逃避的使命。或许,这就是他对自杀这个最沉重、最严峻的哲学问题的个体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