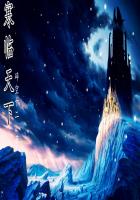的确,当自杀不再属于社会事件而成为内心信念的组成部分时,当自杀不再属于精神医学的治疗对象而成为我们每时每刻的生活本身时,它就真的作为一个鲜血淋漓的哲学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在它阴冷而狂暴的黑暗之眼注视下,正如加缪所说,其余一切哲学思虑诸如“世界是否有三维,精神是否分三六九等”等等都是一些小问题,小到几乎不值一提。应该说,在现代哲学的园地里,这是逻辑实证主义(亦称“科学哲学”)远不熟悉的一块飞地。当前者将思维的探照灯聚焦于科学的发现及其规律,并把科学看作人类生活的至上支配者时,后者关注的却是伦常世界里普通人的悲欢与祸福,它在“光明”的天地里无法遗忘人内心无意义的“黑暗”。同样,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宏大叙事匆匆掠过的一个章节。当前者把“商品”当成解释整个资产阶级走向腐朽命运的密码,并乐观地坚持一种历史主义的世俗信念时,后者倾心的却是现世人生中鲜活而具体的个体生命,它在支离破碎的存在中坚守着完整的人的信念。这就是加缪进入这个问题时的思想语境。然而,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加缪的观点究竟是什么?
实际上,对自杀的思考是一个从荒诞出发的旅程。在加缪看来,生活中的荒诞自然无处不在。在处女作《反与正》中,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独特而孤僻的女人,无意间分得了一笔财产。由于想不出来该如何处置,她就在本城公墓买了块华丽的地下墓室,并用金色大写字母刻上了自己的名字。这事让她十分满意,终于爱恋起自己的坟墓来,于是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每星期都要饶有兴致地“自我造访”一次,一遍遍体验死后的状态。“后来有一桩颇有寓意的怪事,叫她懂得:在世人心目中她已经作古。万圣节那天她来得比往日晚,发现早有人在门口恭而敬之地撒满了紫色堇。大约是几位有慈善心肠的陌生人,出于细心关照,在这座无人献花的墓前匀出一些自己带来的鲜花,向无人照料的古人聊表敬意。”加缪:《反与正》,丁世忠译,见柳鸣九、沈志明主编:《加缪全集》散文卷Ⅰ,页35。加缪以冷静、节制的笔触叙述的这个故事,却把荒诞人生的诸般况味铺陈得淋漓尽致,好似不经意间撕破了生命的华丽帷幕,不由人不为之叹息与怅惘,颇有《金锁记》(张爱玲)中“七巧”细致地将手镯捋至臂窝那个场景的妙处。这样的白描当然有很多。在《西西弗神话》里,加缪引导我们看见一个在封闭的玻璃亭中打电话的男人,我们无法听见他的声音,却将他指手画脚的拙劣动作尽收眼底。(页76)在《误会》里,一个归乡的游子,仅仅因为想给亲人们一个久违的惊喜,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却被母亲与妹妹杀害于自家开设的旅馆。
所有这些,陈述的都是同一个主题:荒诞。这种“最具有理性的激情”,这种既振奋人心又焚毁人心的激情,无限确定而又无比真实。但是,与海德格尔将“焦虑”当做存在之本体不同,在加缪看来,虽然荒诞是人的精神本质之一,但它仅仅“产生于人类呼唤和非理性沉默之间的对峙”(页84),也就是说,“任何荒诞性产生于比较。所以我有理由说,对荒诞性的感觉并非产生于对一个事实或一个印象简单的考察,而凸显于某事实的状态和某现实之间的比较,凸显于一个行动和超越此行动的环境之间的比较。荒诞本质上是一种分离,不属于相比因素的任何一方,而产生于相比因素的对峙”(页84)这种“比较”、“分离”或“对峙”,实际上是一种生命的错位感。理想与现实的错位,黑暗与光明的错位,时间与空间的错位,男人与女人的错位,鲜花与坟墓的错位,总之是一种浸透在骨子里的荒凉与凄楚。面对世界永恒的沉默时,摇旗呐喊的冲动却只变成无声的喑哑;在本该激情满怀的岁月里,我们的直接感受却是现世生存的无意义。
是的,生存的无意义感,这个虚无主义的幽灵早已悄然而至,刮起一阵阵冰冷彻骨的风。在这个背景下,自杀,似乎成了我们必然的选择。应该承认,就消除荒诞这个目标而言,自杀的确是一种最直接、最简便的方式,它让我们终于有机会彻底远离生之苦痛。如果将自杀粗略地分为精神弃绝与肉体灭亡这两种的话,斯多亚主义表达出来的观念常常倾向于前者。“俯视那无数的人群,他们无数的庄严仪式,和无限变化的在风暴或宁静中的航行,俯视那些诞生出来,一起生活,然后死去的人们中的种种差异。也考虑那些过去时代的人们的生命,将在你之后生活的人们的生命,现正在野蛮民族中生活的人们的生命,有多少人甚至不知道你的名字,有多少人将马上忘掉它。”马可·奥勒留:《沉思录》,何怀宏译,三联书店,2008年,页117。这是古罗马帝国皇帝马可·奥勒留在两千年前描绘的生命感觉,一种可称之为斯多亚主义的感觉。众所周知,在斯多亚派哲学家看来,宇宙是一个井然有序的宇宙,世界是一个浑然和谐的世界。因此,摆脱了激情与欲望的达观,跨越过良善与邪恶的宁静,是构成美好生活的最重要的因素。但是,在加缪看来,当生命的错位感依然顽固地左右着我们的判断力,当作为恶之表现形态的荒诞依然如影随形地伴随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时,斯多亚主义的感觉与其说是善意的死后想象,毋宁说是一种对真实的掩饰或漠视,是心灵的另一种形式的自杀。对此,他毫不迟疑地拒绝接受。
加缪清醒地意识到,这些哲学家不过是在以逃遁的方式摆脱生命的无意义感,注定将是一种缘木求鱼式的努力。当他们“通过奇特的推理,在理性的残垣断壁上从荒诞出发,在对人封闭和限制的天地里,把压迫他们的东西神圣化,(试图)在剥夺他们的东西中找出希望的依据”(页86),新一轮的荒诞又开始了自己的征服。因此可以说,奢望以精神弃绝的方式解决问题是行不通的。那么,肉体灭亡的方式怎么样呢?这当然是一个无比激越的选择,一个无法验证的结果。然而,美国自杀学之父施奈得曼(Edwin Shneidman,1918—2009)却偏偏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指出,肉体灭亡式“自杀”的心理根源在于人性深处的一种“后我”(postself,或postego),即人们对自己死后状态的看法。施氏认为,虽然人们无法体验自己的死亡状态,但他们对于自己死后的状态往往有一个错误的想象。而让人真的相信有一个自己根本不存在的状态,其实很难。自杀者常常会犯一个致命的逻辑错误。他(她)多半会这样想:“谁若自杀了,就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我(主)去自杀,那么,我(宾)就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所以,我(主)要自杀。”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在这个三段论中,大前提和小前提都没有错;错就错在,此人忘记了,那个要自杀的“我”是主我,而被注意的“我”是宾我。这个人假定自己在死后,还能作为主我存在,可以受到别人的注意,而忘记了,他自杀以后,主我已经不存在了。参见Edwin Shneidman, “Suicide, Sleep, and Death: Some Possible Interrelations among Cessation, Interruption, and Continuation Phenomena”, in Journal of Consulting psychology, 1964, vol.28, no.2; The Deaths of Man, Baltimore: Penguin Books, 1974; Definition of Suicide, Northvale, J. Aronson, 1994. 转引自吴飞:《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页22—23。值得注意的是,吴飞此著从家庭政治出发,在现实语境中重新思考中国文化中“生命”与“正义”问题,大大推进了迪尔凯姆以来的自杀学研究。亦参见张跃宏:《从“死”开始的旅程》,《读书》2010年第6期。无尽的无可挽回的生命或许就在这个错误逻辑的推导中消逝了。
换言之,想象自己在肉体死亡后依然有生命的“痛”感,这是一个十足的伪命题。正如俗话所说,作为自己观念的囚徒,人永远不能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它暗示给我们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生命的感觉只有在生命存在的前提下才会存在。因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加缪不无肯定地说,荒诞无法消除,也不必消除,“自杀以自身的方式解除了荒诞,把荒诞拽住,同归于尽。但我知道,荒诞是要坚持原状,是解除不了的”(页99)。这也意味着,从荒诞出发的旅程将是一次永恒的长征,一切试图摆脱荒诞的努力都是怯懦的表现,包括自杀。加缪以自己特有的夸张宣布:“自杀是一种忘恩负义。荒诞人只能耗尽一切,包括耗尽自己。荒诞使他极端紧张,而他不断孤军奋战,维持紧张。因为他知道在日复一日的觉悟和反抗中,他表现出自己唯一的真相,即挑战。这是首要的后果。”(页100)是的,反抗,而不是自杀,这是人应该承担起来的唯一责任。
《卡利古拉》(1944)
我们看到,在后来的岁月里,加缪写了《局外人》、《鼠疫》与《反抗者》等一系列作品铺陈反抗的主题。但在《西西弗神话》中,他却用几乎是警句连缀的方式唱起了一曲反抗咏叹调。“唯一前后一致的哲学立场,就是反抗。所谓反抗,是指人与其自身的阴暗面永久的对抗”,“反抗将自身价值给予人生,贯穿人生的始末,恢复人生的伟大”,“人心中一切不可制服和充满激情的东西都朝着人生的反面激励着人的觉悟和反抗。重要的是死得很不服气,而不是死得心甘情愿”(页99—100)。这些在写作生涯前期记下的字句,几乎成为谶语,无一不在加缪后来的生活中得到了恰当的印证。或者说,他的紧张、艰辛与壮丽的一生似乎是为自己早年的话语所作的精彩的注脚。正如加缪的传记作家罗歇·格勒尼埃所指出的,“加缪并不是一个创作动人文学作品的美学家。他的每部作品都表达了他的介入思想,这同他生活中发生的事件是不可分的。在他的一生中,他从不曾置身于社会斗争、人间疾苦和生活的颤动之外,而是置身于其中”罗歇·格勒尼埃:《阳光与阴影:阿尔贝·加缪传》,页3。。这不仅是反抗之为反抗、哲学之为哲学的本意,而且也在践行中成就了一个“人”的伟大。
“自由”与“激情”是加缪从荒诞中推导出的另外两个结果。但正如我们以后在论述《卡利古拉》时将会谈到的,加缪对自由的界定其实是颇为含混的。他从未在哲学层面给予自由一个清晰的界说,而只是从个体经验出发为它赋予一种文学意味。加缪坦然承认,“一个我抓不住的概念,一旦超出我个人的经验便失去意义,我不能纠缠在对此概念的激扬或简单定义中。我不能理解一个优秀分子赋予我的自由所涵盖的东西。我失去了等级感。我的自由观念只能是囚徒的自由观或国体中现代个体的自由观。我认得的唯一自由,是精神自由和行动自由”(页100)。然而,正是由于他执著地将“精神自由和行动自由”判定为生命中唯一重要的品质,才让我们在荒诞的人生境况中保持着一份难得的清醒。不怀旧,不盼望,没有幻想,也没有未来,只有此时此刻的世界和生命。
“某天拂晓,监狱的门在死囚面前层层打开,死囚表现出神圣的不受约束性,除了对生命纯粹的火焰外,对一切都令人难以置信地冷漠,还有死亡与荒诞。”(页102)加缪的这个平静叙述中所隐喻的人生场景我们并不陌生,无论是在柏拉图的戏剧里,还是在帕斯卡尔的散文中,我们都曾读到过类似的表达。加缪这里的贡献在于,在现代语境里重新加以叙述,从而凸显了一种文学意义上的尖锐与真实。而作为荒诞之最后结果的“激情”,在加缪的叙述中同样没占太多的篇幅。他只是再次强调,自杀或者死亡绝非最适合荒诞的结局。饱含激情地活下去,并且注重一种“数量伦理学”,或许会更有教益。对此,加缪以不无调侃的语气说:“在荒诞人看来,任何深度、任何动情、任何激情、任何牺牲都不能把四十年有意识的生活和六十年持续的清醒等量齐观,即使他希望如此也不行”,这是因为,“二十年的生活与经验,是永远替代不了的”。(页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