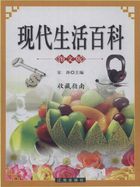郭祥
1946年5月的一个晚上,甘肃省清水县国立第十中学高中部举办了毕业公演,曲目是《飞花曲》。由于毕业生们演出比较投入,整个舞台效果非常好,观众掌声不断。等到演出结束时已是深夜12点多钟。
吕贤汶也参加了演出,他卸完妆,学校收发室的门房就递给他一张条子,说门口有人找。这么晚了,有谁找呢?他有些诧异。当他刚刚迈出学校大门,猛地从黑暗处窜出一个人来,厉声问道:“你是吕贤汶吗?”“对,吕贤汶是!”话音刚落,从黑暗处又冲出两个人,不由分说地扭着了他的胳膊,“跟我们走!”
“你们是干什么的?你们是特务?”“对!我们就是你说的特务。”
对这飞来的横祸让吕贤汶直犯糊涂。进了看守所,一过堂,才知道特务们从他的寝室里搜出了《资本论》,还说他办壁报,批判《野玫瑰》,肯定是共产党。吕贤汶大叫冤枉。
吕贤汶1927年生于南京,高中就读于清水国立十中。他对戏剧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尤其喜爱研究话剧史及话剧人物。话剧就是对现实生活中的“人”与“事”进行浓缩,是社会上的一切“美好”与“丑恶”的再现,由话剧这个窗口可透视和认识社会。他爱好戏剧如同他爱好写诗、写小说一样,是想借文艺为武器,反对黑暗,反对压迫,反对法西斯统治。因此,他遍读1941年10月至1946年5月陪都重庆报刊所载的演剧消息,每个剧的编、导、演、舞美设计、演出场地他都过目不忘,重庆和桂林等地出版的大型文艺和戏剧杂志中所刊载的剧本他都要找来,去如饥似渴地研读。甘肃清水地处偏僻,鲜有时新的报刊杂志,县图书馆“万有文库”成了他的剧库,他读完了文库所有的剧本。由于他在戏剧方面的专才,他主持本校的演出团体“剧声”社,办《剧声》壁报,并参加其他6个壁报组织,写稿,从事演剧活动。他还在报刊上发表小说、诗歌与评论,为反对日本侵略、争取民主而斗争。在高中时代,他就积累了话剧史料和论著文稿上百篇。
特务说吕贤汶批判《野玫瑰》,倒也没有冤枉他。《野玫瑰》讲的是一名国民党女特务打入汉奸内部,利用美色套取情报,从事抗战活动。这种方式是共产党所不齿的。吕贤汶也写了很多批判文章,恰好与共产党的一些观点吻合。于是,吕贤汶的文章往往是白天写好贴在壁报栏,三青团(国民党外围组织)夜里就悄悄撕掉,经过几次较量,特务们认定吕贤汶是共产党,就动手了。
当时内战正酣,承认自己是共产党,无疑是生死交关。面对特务们的盘问,吕贤汶一口咬定,只看过《家》、《春》、《秋》一类左翼作家反封建的书,写批驳《野玫瑰》的文章,是反对把汉奸写成英雄。
特务们始终没找到其他证据。到了7月份,吕贤汶借口自己要考大学,又依靠一个同学家长担保,他被释放出来,但要随时向特务们通报自己的行踪。
为尽快避开特务的纠缠,他到西安考完大学的当晚,就跑到火车站搭乘到开封的火车。由于没有钱,吕贤汶就混上火车,躲在三等车厢座位底下,一路心惊胆战,生怕被查票的抓住。到了开封,吕贤汶去舅舅家住了几天,向母亲报了平安,又转道南京。
甘肃清水十中有一个苏皖同乡会,其中有个同班同学的父亲很有权势,当时正要上任国民党热河省党部委员,吕贤汶找到他介绍工作。他先是想介绍吕贤汶去陈立夫开办的中国农民银行去,吕贤汶推说自己数学不行,但能写点文章,这位同学的父亲有一个朋友在《无锡人报》做总编,就写了一封信,介绍他到无锡去。
吕贤汶就这样到了无锡。
这位总编的工作规律是白天休息,晚上上班。一直等到7点,吕贤汶才见到了总编,并被安排到采访部搞采访。在《人报》唯一一间楼阁子上与他同屋居住的是报社副总编,一个姓叶的国立剧专的毕业生。当他听说吕贤汶喜欢戏剧,就非常高兴,并介绍他去找他的同学张雁,采访正在无锡拍摄电影《遥远的爱》的名演员秦怡、赵丹等。
第二天,吕贤汶通过张雁结识了赵丹。
“赵丹先生,我是《人报》的记者,今天是我第一次采访。”
“你采访我什么呀?”
“我对戏剧比较熟悉,你在大后方演的戏我也有一点了解,今天你在戏里演一个教授,请你谈谈你演这个角色的感想?”
“你对戏剧熟悉吗?”赵丹问。
那年吕贤汶才19岁。穿着一件很旧的白衬衫和带背带的工装裤,脚上穿的胶鞋破了个洞,露出大脚趾。
“你不像记者,你是干什么的?”当时,一些特务把自己故意装扮成劳动阶层,专门找机会套抓共产党和进步人士,被称为“红旗特务”。吕贤汶的装束确实让赵丹产生了怀疑。
“我在学校喜欢戏剧专业,还写过反对《野玫瑰》的文章。”他还谈了自己其他一些经历,让赵丹逐渐对他产生了信任。吕贤汶乘机说:“我今天是第一天当记者,我们的副总编辑是国立剧专毕业的,他把我介绍到这里来找张雁的。”
他明白了吕贤汶的来意,就对他谈了一些自己经历和在《遥远的爱》中扮演肖教授的情况。
当时略显幼稚的吕贤汶,当晚就写出了一篇两千多字的特写,题目是带强烈左翼色彩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为了躲避特务对他追踪,吕贤汶取了个“石曼”的笔名,日后被誉为戏剧史资料的“活字典”、戏剧统计工程师的石曼从此就诞生了。
当时的大多数记者都是西装革履,头发打着发油。哪里有凶杀案,哪里有桃色新闻,各报记者就轮流去警察局抄一抄稿子,没有轮上的上午就睡觉,下午去喝咖啡,等拿回稿子后就添油加醋地编写。石曼却每日为电影《遥远的爱》写一篇特写,连发20多篇,这在中国电影史上是少有的。
从这时开始,他与参加拍摄《遥远的受》演剧九队结下了不解之缘,演剧九队常驻无锡,这支党领导的演剧队成了他真正的“家”。一年半的时间内,他先后在《无锡人报》和上海《大公报》写了有关九队的戏剧、歌咏活动的文章及消息报道六七十篇。由此伊始,到1949年4月,石曼写的通讯、报道和各类作品达六七十万字之多。除发表在《无锡人报》外,还载于上海《大公报》、《新民晚报》、《联合晚报》、《展望》杂志、《经济周报》等。
1949年7月,石曼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文艺大队到了重庆,1952年参加重庆市话剧团《四十年的愿望》的集体创作。此剧获1956年中央文化部颁发的第一届全国话剧会演剧本创作二等奖,列为建国十年优秀作品,195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因体弱留团监督改造,当清洁工兼管资料室,由此他“因祸得福”,从1957年至1966年,他通过向重庆古旧书店以及上海、北京古旧书店购书,搜集到自《新青年》杂志始,《南国》、《舞台艺术》(山东省立剧院出版)、《剧场艺术》、《戏剧与文学》(上海出版)、《矛盾》、《光明》杂志的戏剧专号,抗战期间大后方所出版的《抗战戏剧》、《新演剧》、《戏剧岗位》、《戏剧月报》、《戏剧时代》、《戏剧春秋》等多种刊有戏剧作品的大型文艺刊物;民国以来所出版的话剧剧本以及其他有关话剧书籍共数百种。并悄悄用许多化名和笔名,在《重庆日报》、《甘肃日报》、《武汉晚报》、《北京晚报》、《新民晚报》发表话剧史话。1964年,他利用刻印剧本的机会,将搜集到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编印的《1941-1942年重庆演剧概况》刻印出版,以“重庆市话剧团资料室”的名义,向全国各大报刊、大专院校、戏剧团体通报了这一珍贵资料的信息,发行了一百多册。
“文化大革命”期间,剧团中许多人把所谓的“文艺黑线”书刊当废纸出售,他这个“清洁工”乘机与收废品的人做交易,收得了《国立剧专同学录》,国立剧专、中华剧艺社、中国艺术剧社的演出说明书以及抗战版书刊百余种。“造反派”后来抄家抄去了他历年发表的文章作品的剪报集,但这部分戏剧史料被他巧妙地藏在公家图书中,得以保存。
粉碎“四人帮”后,石曼更是焕发了青春,他参加了有关周总理在重庆革命实践的剧本创作,先后访问了宋平、陈舜瑶、荣高棠、冯乃超、蒋南翔、何谦、廖梦醒、龙飞虎、阳翰笙、张瑞芳等数十位同志,为恢复抗战时期话剧的历史地位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他还为《戏剧电影报》、《戏剧报》、《新民晚报》、《四川日报》、《成都晚报》、《抗战文艺研究》、《戏剧与电影》杂志、《重庆日报》、《重庆晚报》等报刊写抗战剧坛盛事百余篇。在他负责主编的《重庆剧讯》期刊上辟“我在重庆的戏剧生活”专栏,陈白尘、吴茵、路曦、周彦、胡绍轩、石羽、吕恩、奚立德、谢晋、张逸生等在重庆生活过的戏剧界老同志撰写回忆文章50余篇。
石曼对抗战话剧史的研究工作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北京、上海、天津、桂林、成都研究大后方话剧史的人纷纷来渝和他交流史料;许多大学生、研究生撰写论文请他解答疑难问题;拍摄《于伶》、《曹禺》、《司徒慧敏》电视片的摄制组来渝,请他担任咨询。重庆出版社请他编纂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戏剧篇三卷,编辑了代表各个方面的26位剧作家28本剧作共160万字,其中所选顾一樵、胡绍轩、臧云远、吕复、吴新稼等抗战时期剧作,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是首次出版。
1995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石曼所著《重庆抗战剧坛纪事》一书,该书阐明了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戏剧对整个大后方戏剧运动的影响和在中国话剧史上的地位,被分别授予重庆市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和全国文化系统革命文化史料征编成果优秀奖,并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授予“全国革命文化史料工作先进工作者”称号。
(该文原刊《重庆统一战线》2002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