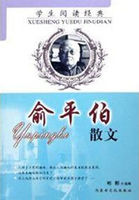故乡的老人,将吞咬烧饼或馒头这类食物所洒落的残渣碎粒,视之为馍花,这是在我小的时候。现在,我已经离开村子十年有余了,那会儿的老人,都相继去世,社会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起码我的村子,耸起了一座一座的楼房,那些装饰墙壁的五颜六色的瓷砖,在阳光之下熠熠生辉。显然,粮食是装满了板柜和老瓮的,否则,农民不会这样建造自己的家。然而我不知道今天的老人,是不是还像过去的老人一样,依然在咀嚼食物的时候,防止残渣碎粒掉到地上,甚至要将散在地上的馍花捡而咽之。
馍花是多种多样的,面粉细白,馍花就白,面粉粗黑,馍花就黑。烙的烧饼或锅盔,脆而酥,容易洒落,它们如蕊如沙;蒸的馒头或包子,柔而软,其渣其粒,相对要少要小;但玉米发糕是蒸的,它却洒落得又多又大,那种金黄,很像秋风吹撒的点点菊瓣。
我爷爷在吃馍的时候,常常是双手将馍掬着,这样,馍的渣粒便掉进了掌心,最后,他会张开口,将其送入,并要把洒落地面的馍花,一个一个地捡起,放到嘴里。我是不能这样做的,不但不能,而且暗暗讥笑我的爷爷。那时候,我觉得这是毛病,脏,啬,我想,这样一些馍花,究竟会有多少作用呢?
父亲在工厂上班,他当然不会掬而食之,更不会捡起地面的馍花,然而在过去,他也有让我难以理解的行为。这就是,他会把自己剩下的或别人扔掉的馒头,用手绢包着,拿回家去喂鸡,他认为这些馒头丢了,是一种浪费。我的父亲很有口才,而且对人热情,他由工厂回到农村,家里总是要来很多的乡亲,他们围着父亲希望从他那儿得到一些关于城市的消息和逸闻,以满足好奇之心。那热闹的场面,使我激动而自豪,为着我的父亲。然而,放在窗台上的一堆馒头,显然让人扫兴,我盼望父亲以后不要带着它回来,特别害怕乡亲看见他的做法。我以为,这很丢脸,并要影响他的威信的。
在相当长久的岁月,爷爷和父亲的节省之举,一直为我所不齿。虽然我清楚,家道的败落,曾经使他们遭受饥馑,不过苦难已经过去,就没有必要这样了。我一点都没有明白,珍惜粮食,或者扩而大之,爱护人类所创造的一切及人类生存环境之中的一切,是一种良好的品格。甚至在我读大学的时候,竟将完整的馒头扔进食堂门外的瓷缸,并几次把馒头远远地甩向楼房的墙壁,看它如何反弹过来。我是在模仿个别纨子弟,以为这很潇洒,是一种风度。我是在艰苦的农村长大的,然而我显然忘却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情景。
当我有了家庭,有了孩子,品尝了生活的真实滋味之后,才体会了爷爷和父亲的心情,体会了我小的时候,那些故乡老人的心情。我已经很自然地不忍将剩饭剩菜倒掉,而且要将偶尔放坏的馍积攒起来,像我父亲那样,带回老家去喂鸡,我的母亲仍生活在农村。我这样做,已经没有丝毫不好意思的感觉。
选自1993年8月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白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