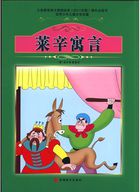在吃过面以后,他的母亲一边打发这位老长工到埠头去挑行李,一边嘱蠫安心地睡一觉。她自己就去整理蠫的书室,——先将床前床后的稻草搬到后边的小屋去。再用扫帚将满地的垃圾扫光了。再提了一桶水来,动手抹去橱桌上的这层厚厚的灰。她做着这些事情,实在是她自己心愿的,她不觉劳苦。她的意识恍恍惚惚似这样的说道,“我的儿子重寻得了!他已经失去过呢,可是现在重寻得了。我要保护他周到,我要养他在暖室里面,使他不再冒险地飞出去才好。”
她几次叫王舜离开他的哥哥,而这位小孩子,却想不到他哥哥的疲劳,他只是诉说他自己要说的话。以后母亲又叫,“王舜呀,不要向你哥哥说话,给你哥哥睡一下罢。”
王舜皱一皱眉,十二分不满足似的。于是蠫说,“你说,我在船里睡够了,现在不想睡,你说。”
这样,王舜似得了号令,放肆的告诉他满心所要说的话。他大概所告诉的,都是关于他们的学校里的情形。教师怎么样,谁好,谁坏,谁凶,谁公正和善,谁学生要驱逐他。功课又怎样,算术是最麻烦的,体操谁也愿意去上。他喜欢音乐和图画,可是学校里的风琴太坏,图画的设备又很不完全。于是又谈到同学,谁成绩最优,被教师们称赞;谁最笨,十行书一星期也读不熟。他自己呢,有时教师却称赞他,有时教师又不称赞他。以后更谈到谁要做贼偷东西,偷了别人的墨还不算,再偷别人的笔,于是被捉着了,被先生们骂,打,可是他自己还不知道羞耻的。这样,他描写过学校里的情形以后,进而叙述到他自己的游戏上来。他每天放学以后,总到河边去钓鱼,鱼很多;所以容易钓。星期日,他去跑山,他喜欢跑上很高的山,大概是和朋友们五六人同去的,可是朋友们喜欢跑高山的人少。他更喜欢跟人家去打猎,打鹿,山鸡,兔,鹁鸪,可是他母亲总禁止他。实在说,他一切所告诉的,都是他自己觉得甜蜜而有兴趣的事。就是母亲的责骂,教师的训斥,他也向他的哥哥告诉了。他的世界是美丽的,辽阔的,意义无限的,时时使他向前,包含着无尽的兴趣和希望。在他诉说的语句之中,好像他一身所接触的地方,都是人生的真意义所存在的地方。他的自身就是蜜汁,无论什么接触他都会变成有甜味。他说了,他很有滋味地说了;最后,他想到了一件不满足的事,他说,“可惜哥哥不在家,否则,哥哥不知有怎样的快乐,我也更不知有怎样的快乐呢!”
说完,他低下头去。这时,王舜也听的昏了,他微笑地看着他的弟弟,说了一句,“以后你的哥哥在家了。”
“呀?”王舜立时高兴起来。可是一转念,又冷冷的说,“你病好了,又要去的。”
“那末你祝我的病不好便了。”
“呵!”王舜骇惊似的,两眼一眨。蠫说,“王舜,我老实向你说,我的病一辈子是不会好的,那我一辈子也就不会去了。”
“哥哥一时真的不去了么?”王舜又希望转机似的。
“不去了。那你要我做什么呢?”
“快乐哟,当然随便什么都可以做。”
王舜又沉思起来,一息说,“哥哥,你第一要教我上夜课。第二呢,钓鱼。”
“你白天读了一天的书,还不够么?”
“不是啊,”王舜又慢慢的解释,“同学们很多的成绩都比我好,算术比我好,国语比我好。但是他们的好,都不是先生教的,都是从他们的哥哥,姊姊那里上夜课得去的。他们可以多读几篇书,他们又预先将问题做好,所以他们的成绩好了。我呢,连不懂的地方,问都没处去问,妈妈又不懂的。所以现在哥哥来,我要求哥哥第一给我上夜课。第二呢,钓鱼;因为他们都同他们的哥哥去钓,所以钓来的鱼特别多。”
“好的,我以后给你做罢。”
“哥哥真的不再去了么?”
“不会再去了,哥哥会不会骗你呢?”
“骗我的。”
“那末就算骗你罢。”
而王舜又以为不对,正经地向他哥哥说,“哥哥,明天我可同你先去钓鱼么?”
“好的。”
“你会走么?”
“会走。”
“妈妈或者要骂呢?”
“妈妈由我去疏通。”
这时王舜更快乐了。一转念,他又说,“可是我那钓杆在前天弄坏了,要修呢。”
“那末等你修好再钓。”
“修是容易的。”
“钓也容易的。”
“那末明天同哥哥去。”
“好的。”
这样又停了一息,弟弟总结似的说,“我想哥哥在外边有什么兴趣呢?还是老在家里不好么?”
蠫也无心的接着说,“是呀,我永远在家了。”
弟弟的愿望似乎满足了。他眼看着地,默默地立在他哥哥的床前,反映着他小心的一种说不出的淡红色的欣悦。正这时,只听他们的母亲,在蠫的书室内叫,“王舜呀,你来帮我一帮。”
王舜一边答应着,“口汗。”
一边笑着向他的哥哥说,“哥哥,你睡。”
接着,他就跑出门外去。
可是哥哥还是睡不着。他目送他的弟弟去了以后,轻轻地叹息一声。转了一转身,面向着床内,他还是睡不着。虽这时的心波总算和平了,全身通过一种温慰的爱流,微痛的爱流。剩余的滋味,也还留在他的耳角,也还留在他的唇边,可是他自身总觉得他是创伤了,他是战败了。他的身子是疲乏不堪,医生对他施过了外科手术以后一样。他的眼前放着什么呵?他又不能不思想。他想他母亲的劳苦,这种劳苦全是为他的。又想他弟弟之可爱,天真,和他前途的重大的关系。努力的滋养的灌溉与培植,又是谁的责任呢?他很明白,他自己是这一家的重要份子,这一家的枢纽,这一家的幸福与苦痛,和他有直接的关联。回想他自己又是怎样呢?他负得起这种责任么?他气喘,他力弱,他自己是堕落了!过去给他的证明,过去给他的响号,过去给他的种种方案与色彩,他已无法自救了!现在,他还能救人么?他汗颜,他苦痛呀!他在喉下骂他自己了,“该死的我!该死的我!”
他想要向他的母亲和弟弟忏悔,忏悔以后,他总可两脚踏在实地上做人。他可在这份家庭里旋转,他也可到社会去应付。但他想,他还不能:“我为什么要忏悔?我犯罪么?没有!罪恶不是我自己制造出来的,是社会制造好分给我的。我没有反抗的能力,将罪恶接受了。我又为什么要忏悔?我宁可死,不愿忏悔!”
这样想的时候,他的心反而微微安慰。
一时他又眼看看天外,天空蓝色,白云水浪一般的皱着不动,阳光西去了。一种乡村的草药的气味,有时扑进他的窗内来。他觉到他自己好似展卧在深山绿草的丛中,看无边的宇宙的力推动他,他默默地等待那死神之惠眼的光顾。
如此过了一点钟。一边他母亲已收拾好他的房间,一边和伯也挑行李回来了。
和伯帮着他母亲拆铺盖,铺床。
他半清半醒的在床上,以后就没有关心到随便什么事,弟弟的,或母亲的。而且他模糊的知道,母亲是走到他床前三四次,弟弟是走到他床前五六次,他们没有说过一句话。她轻轻的用被盖在他胸上,他身子稍稍的动了一动。此外,就一切平宁地笼罩着他和四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