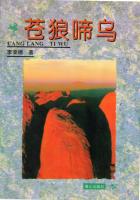这个天空上蒙着一层灰雾、笼映着几线惨淡的阳光的秋日下午已经将要过去,黄昏已经渐渐地来临了。在花残木缺、水淤屋乱的海晏堂内外,一种原始的、衰败的气息更加强烈地侵袭过来,连额尔金都觉得有些毛骨悚然。在一面用汉白玉砌成的墙壁上挂着一副描绘着乾隆皇帝在塞外热河"巡幸"、"秋狩"场面的巨型油画--《秋猎图》,画面上,乾隆皇帝穿着满式盔甲战袍,手持弓箭,用一副睥睨天下的眼光看着画面中、以及画面外的一切,一名衣饰鲜明的八旗侍卫高捧着一个盘子跪在乾隆皇帝的马前,在那个盘子上装着大小不同的几支西洋火枪。额尔金抽出指挥刀,在那副巨型油画上猛劈、猛划、猛刮、猛刺了一阵--乾隆皇帝的脸、盔甲、战袍、弓箭、战马,簇拥着他的八旗子弟兵,晴朗的秋天中的壮美山河……这画面上的一切都被额尔金用指挥刀给尽量地毁灭了。额尔金看了看他用指挥刀在原来的那幅画布上添续的又一幅新画面,然后,他绷紧了脸,"嘡嘡嘡"地踢着靴子上的马刺,离开了海晏堂。
额尔金走在往圆明园中的紫碧山房而去的路上……他忽然想起,被清朝廷拘捕的巴夏礼(Harry Smith Parkes)等人可能在近两天之内就会被那个吓破了胆的"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恭亲王奕訢给放回来了,北京城内的虚实到底如何,还是应该听听巴夏礼的报告。紫碧山房到了,这一片宫殿建筑在一组玲珑而俊秀的山丘上。额尔金沿着蜿蜒的石阶走了上去,来到了建在一处山脊上的敞厅之中。当他站在这座敞厅的雕花栏杆旁边,举目四眺的时候,一股莫名其妙的、说不清的心情占据了他的心头。噢,他想起了他在牛津大学读书的年代,每逢傍晚,在学院附近散步的时候,常常用一种略带感伤和忧郁的情调所欣赏的英格兰式的黄昏--教堂的尖尖的钟楼,从钟楼上传来的做晚祷时的钟声,枝繁叶茂的稠李子树,细草绵绵的山坡,慢慢归圈的羊群和健壮、警觉的牧羊犬,温柔的、小小的英国五月花……但是,现在不是想这些遥远而美丽的景象的时候,等到他退休之后,他会坐在腾蹿着温暖的火焰的壁炉边,一边抽着烟斗、喝着雪利酒,一边在那种温馨的、熟悉的环境中回忆他所经历的大学时代、在牙买加和加拿大当总督的黄金岁月、以及在中国的战争体验……想到此处,额尔金的眉头又紧紧地皱了起来,他将一种恶毒的、玩弄的目光向四周更远处投了出去,在那里的各种景象,有的是从他现在所在的这座山顶敞厅能望见的,有的是不能望见但是仍然活动于他心中的版面之上的--他知道除了圆明园、绮春园、长春园这三座号称"圆明三园"的最著名的皇家园林之外,还有曾经在欧洲享有神秘的名声的康熙皇帝曾经起居的畅春园,围绕着乾隆皇帝所沾沾自喜地命名的"万寿山"和"昆明湖"而建造的清漪园(乾隆皇帝是个傻里傻气的家伙,他曾经告诉在1793年来中国要求中英建交的马戛尔尼爵士"中国什么都有"), 点缀在那正飘荡着血一样鲜艳的红叶的香山之下的静宜园,在流淌着甘洌的、适于冲沏昂贵的龙井茶的淙淙泉水的玉泉山之下建筑着的静明园……还有许许多多的像景明楼、鉴远堂、治镜阁、功德寺这样的虽然规模不大、但是依然布置有序、自成体系的皇家别业和御用寺庙……而在他指挥下的英国军队和在法国侵华军全权专使葛罗(Jean Baptiste Louis Gros)指挥下的法国军队在那些园林中也进行着抢劫和破坏,有了在圆明三园中新磨砺出的抢劫和破坏的经验,他们的摧毁工作想必进行得更加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