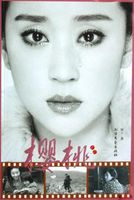查睿楼太太尽她的心力将她能想到能安排的事,都想到都安排了。但是她不可能预料到,她煞费苦心为查婉香准备的这份妆奁中的珠宝、古董、字画,在运到北京城之后,将会在无数次的战乱和逃亡、偷窃和劫掠、敲诈和勒索之中,渐渐地散失在人间。其中的一部分,被辗转于多人之手,有的甚至漂洋过海,出现在英国的博物馆的展台上和古董铺的橱窗里;有的就在北京城的珠宝、古董市场上流通,直到民国初年,还常有一些有心人在逛古玩店时,认出哪些是当年从状元大学士府流落出来的查家的旧物。
从海盐到北京的一路上,查婉香记住的只是江南的水泽山川,落日黄昏。那黄昏仿佛永远没有尽头,笼罩在大地上的每一个角落,就是这黄昏,伴随着她在北京城度过了在族叔查谷荪家和状元大学士府举行的每一个细节都规定了繁琐程序的迎亲仪式和婚礼大典。据说,这是北京城在那几年少见的豪华风光、排场古雅的婚礼。
查远平护送查婉香到达北京查谷荪家,安顿了下来。过了几天,状元大学士府就派人来查谷荪家送那份气派不减当年的聘礼中除了礼金之外的其他部分--礼单已经请查婉香的父母在海盐查家祖宅过目,并得到了他们满意的认可。状元大学士府派出了出行时的全副执事,请了四名戴红顶子的和四名戴亮蓝顶子的官员当"保山"和护送聘礼的使者,用三百名绿营兵和三百名挑夫将那份聘礼装在两百抬映出了幽然而锃亮的光芒的朱漆大抬盒中抬着,浩浩荡荡地穿过半个北京城,送到查谷荪家。
这时正是咸丰四年(1854年)二月中旬的天气,北京城早春的树木花草已经显出了绿意柔氛,可是春风依然那样冷峭,满街的黄土漫漫,无情地掠过那些护送聘礼的官员、池家的族人、管家、绿营军官和那些抬着执事和朱漆大抬盒的绿营士兵以及挑夫的那硬得像岩石一样的脸,他们身上穿着的崭新的、还能看出未捋平的折痕的马褂的襟袖,马褂下面的在冷风中呼啦作响的长袍和战裾,悠然地踏在锃亮的马镫子上的黑缎子朝靴和慢条斯理地有节奏地踏在京畿大路上的皂色战靴。
这是状元大学士府池家要娶新娘子了,很多市民都在街市的道路两旁或专心、或无意地张望着。有几个衣衫破旧、面色黎黑像是商贩走卒模样的人也在人群中默默地张望着。看了一会儿,为首的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低声对旁边的同伴说:"走。"
话音刚落,这个青年就好似无心地踱出了人群,顺着旁边的通向另一个方向的另一条街道走去。他旁边的几个人也不说话,跟在他身后一起走了出去。
他们就像漫步闲逛似的走过好多条街道,当他们来到了珠市口附近的一个胡同口前的时候,他们折了进去,又朝前走了一会儿,就来到了胡同深处的一个院子的院门前。这几个人在为首的青年的带领下,走进了这个院子,一进院门,转过影壁,他们就看到一个衣饰齐整、管家模样的人正在跟住在院中的徽班戏班"松菊班"的主人柴成松谈话。他们没惊动这二人,泰然自若地径直走进院子,来到西厢房跟前。除了那个为首的青年,其他人都走进了西厢房。那个为首的青年且自留步,站在西厢房的房檐下,拿出了旱烟杆和旱烟袋,往铜烟锅里装上了一锅烟丝,然后用火刀、硝石打着了火,拿火绒把烟丝点着了,闲闲地抽了起来。他一边抽着旱烟,一边看院中的戏班人员们练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