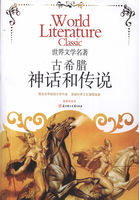生活不是每天都在众星捧月的光环下,生活是永远在路上,在为梦想添砖加瓦之中,生命本就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
——大同·北风
一双着风的眼睛,静静地坐在面孔之上。
这时,一片羽毛坠临在湖泊中间,它轻盈地回旋,辗转的技巧及飞来的姿势,让神态生动。
翻阅着你的来信。真真的一种温馨的享受。
很久以来,无人再用弹奏高山流水的手势,把一林树荫投影,在你字句构筑的田间路径踱步,感觉很好!
你或许还不知道吧?
地处川西北重镇的绵阳的阳光很直接很爽朗,于千里之外就想念北纬39°的山西大同的你。
想大同这个“三面临边,最号要害。东连上谷,南达并恒,西界黄河,北控沙漠。实京师之藩屏,中原之保障”的兵家必争之地,缅怀追忆杨家将血浴沙场的故址——金沙滩(今属山西朔州市界)与大名鼎鼎的抗日战争战场——平型关……
这一切的一切,像是最尖锐的话题,不可能一抹而过。
这一切的一切,像是最明确的线索,可以深到无法化解的渊源。
那河流亦浅亦深,赤足走完全程,倘若不被水暴湿四年沉默后的胆怯,已成为不可能了。
翻阅回信,要用手心触摸羽毛的仔细,用掌与掌之中的贴进,便要几日缄口的沉静。
但凡轻柔的东西,要相近似的平息,才可能有最贴身的了解。
绵州校园,那现实的生活如绻空窗纱,委婉地阻挡把一片羽毛看得更清楚。
闲暇,当我在文字里谈学业生活、话人间冷暖、评远喜近忧、书市井芸芸众生,你的信就搁在我的句子底下,是最合味的酒色中最纯粹的冰,沉在最深处。
心境太喧杂了,我不肯再混沌里匆忙摆渡一封信函。
当我静到可以看的时候,我就一直看到它整个彻底溶解,通过一个手势,轻意变成一股酒意沁心,让一颗心温热而继续含蓄。
信中,难得你把一段心绪放大,看得见每个细胞的跳动,然后你静静地、自然地挪开放大镜,避开一切深究,那就是你日晒雨淋练就的功力吗?
在你的信到达的这个地方,是我营造的第一个壳,在壳中还没孵化出啄破黎明的雏鸡,便整个外壳内连滚于红尘了,唯恐与生存空间与生活时间渗透不够,像上苍宠爱的电动鸡仔,一阵忙碌就做完规定的程序动作,一停下来,生怕如啄米时带动的灰尘,被惯性远远抛弃。
我拥有许多梦寐,舒适的座椅为我设定,我站在金光灿灿的橱窗,展览一种生活的姿态,一百年也就过去了。
但我却期待结束黑暗的苔藓,在钟声疲惫了,有一段离开自己的距离,从一些过程中深入故事情节,让它们在文字的岸边晾晒,像木乃伊吹干水份,浓缩最本质的成份。
这样在一次仰首之后,我不敢出声,只是把一些深刻的事件堆码起来摇摇手而血液从枝丫上滴落,已经是无法更改的事实了。
保留一种清醒已很不容易,正如你说的我们彼此的印象早就十分模糊。
走在街上,彼此都会亲自省略彼此,日月当头,我迎合生活环境的面孔,布置得工整,打扫得很干净,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张张花草稿纸单薄的灵魂。
将来,即使你看见我,只要一眼就够了,但现在我们自有另一种注目,在文字与文字里相互凝视,语言似强频度的电信波段,不会因为不同的质地、距离或位置而随时随地中断。
读你的信,犹如一杯意蕴复杂的浓咖啡,小杯而澄莹的茶色,味浓不会饮的,总说那是化不开的苦涩,真正的饮者却滋滋乐道,意迷其中。
我真想盗取你立体的表达方式,让农夫也感叹:多么美丽的玻璃!使贵妇人惊喜:多么辉煌的炫耀!让钻石家说:吃惊的游刃表达……
要怎样的智慧,才能用最简单的表现那些最复杂的,用最复杂的表现那些最简单的,只是想想便累了。
而你把那些象形符号附上魔力,调合成可以狂饮可以细品的咖啡,又如那颗木糖醇一般的润喉糖,初期的清凉就一路走下去,合上了嘴,木糖醇犹如在口,滋味早已潜入我心。
当我真真正正地读完你的来信,离我梦游山西、神游大同的日子就不远了。
既然你对我的性格、品行、才学有了基本的概念,我就不必掩饰字迹的杂乱与思绪的凌乱,在清雅别致的书房里呆久了,实在太喜欢半躺半坐在床上,零食与饮料摆在床头柜上,边吃边喝边想边写,指尖的舞蹈在夜里如蝴蝶一般翻飞。
如果你有耐心看这团团乱草,我就非常高兴地继续维持,大抵习惯也放任不管了。
在电脑故障排除后,一盘清逸的檀香,散发袅袅的流云,久久回旋在书房和我的心间。
键盘一旁是一大堆的新鲜杨梅,那是一个同窗赠送我的,口含一枚梅子,打出一些清楚的文字符号给你。
暑假很热,子夜已过。夜间吟叫的蝉儿也热得不耐烦。
明天中午十点我或许才会醒来,叮嘱那些文字符号变成鸿雁,振翅高飞,问候千里之遥的朋友——山西的你!
正是那个时刻,我拜托了睡眠的纠缠,活在心灵之中,每每想起惊落的故事和面孔,这样的时刻总是如同春风一样温暖。
(此文刊发于2010年某期《同学少年》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