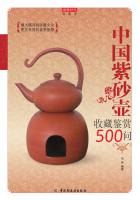中国上下数千年的古史中,民族融合斗争的进程从未停止过。公元1279年,大漠的蒙古灭掉了南宋,统一中国。但当时的阶级对立和民族矛盾并没有缓和下来,在社会意识形态和宗教文化方面也呈现了歧异多元的现象。
蒙古族人风俗是秘葬而不立墓冢,连其英雄圣祖成吉思汗也不例外。自然元朝一代在陵墓建筑石刻方面无所建树。但元世祖忽必烈却以其雄才大略,在今北京扩建了举世闻名的元大都。
元大都的宫殿建筑穷奢极欲,采用了很多稀有贵重的材料来装饰豪华的言殿,其中也有大量的石雕装饰构件。在官修的《元代画塑记》中就记述有当时大都(今北京)、上都(今内蒙古多伦)的重要雕塑创作活动。当时建筑与室内装饰用的大理石、汉白玉等石料加工工艺也比较发达。
西藏化的密宗佛教——喇嘛教,在元朝受到统治者的高度尊崇和礼遇,因此喇嘛教风格的庙宇、白塔、木石雕刻的造像、建筑等宗教艺术在全国普遍盛行。现存的北京北部居庸关内镇的云台,就是当时最为著名的建筑石刻艺术。
居庸关云台称为“过街塔”,这是佛教密宗信仰的产物。元皇室兴建过街塔,除有奉佛建塔祈福延寿以及利国安民的用意外,还有“下通行人,皈依佛乘,普受法施”的劝诫之意。
这座过街塔仅存基座,原上部有三座喇嘛塔。在这基座上可见雕刻有天神、金翅鸟、龙、云等喇嘛教纹样及梵文、藏文、八思巴文、畏兀儿文、西夏文和汉文等6种文字的经文。这些形象都是高浮雕,其人物的姿态神情都很有气势,威武夸张,各种图案洋溢着跳跃活泼热烈的气氛。其中有天王脚踩汉服装饰的妇女,以及持笏恭迎的汉人和塞外,民族形象,这也反映了元代统治者推行民族压迫,歧视政策的实质。与居庸关云台石雕类似的过街塔,也见于桂林、镇江等地。
从前者的装饰风格看,它与前代的汉式传统风格有所区别,是元代雕刻中的杰作。喇嘛教的建筑和雕刻形式,对明清艺术影响是深远的,如过街塔在明代仍在建造。
蒙古元朝的统治者,勇于开疆拓土,铁骑横跨欧亚,无形中扩大了中华文明的影响,也进一步加强了中西交通,所以元代中国也产生了中亚风格的伊斯兰教建筑。如泉州清净寺重建于1341年,全部石造,就属西亚形式,至今仍保存有伊斯兰教礼拜堂的石雕壁龛和阿拉伯文字石刻。此外还有基督教、婆罗门教、摩尼教石刻,这些碑石、柱式、神话雕刻、飞天形象都具有浓厚的异国情调。
明清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动乱、复苏、繁荣又走向崩溃的最后一轮循环的周期,当时的建筑艺术,还是沿着古典艺术的传统向前发展,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史上的最后一座高峰。
明代的宫苑、陵邑的规模都十分宏大,附丽其中的建筑石刻艺术也取得了不少创新的成就。清代的离宫园林,更是在规模质量上超过了明代。
当时的大、中型住宅也普遍采用了石雕装饰构件,这是一种空前的现象,其中又以北京明清故宫及其皇城园林的建筑石刻艺术最具典型性。
明清北京城的设计布局都是以宫室为主体规划的,它以一条长达7.5公里的南北中轴线作为全城的骨干,所有的城内宫殿及其他重要建筑都围绕着这条轴线巧妙地组合为一个整体。从大明门到天安门之间,就是由一条宽阔的石板御路衔接的。在天安门前,则配以五座石桥和华表、石狮,以衬托出皇城正门的雄伟壮观。
石刻华表古已有之,但明代天安门的白石华表却自有其时代的特点和艺术成就。它是以多种雕刻手法塑造的空前建筑装饰,华表柱身的主体龙纹,以压地隐起的浅浮雕刻画出蟠曲而上的龙形,间夹以云纹华饰,使得华表瑰丽而庄严,其柱头上满饰异彩纷呈的透雕云朵,莲瓣石盘上饰以圆雕的雄狮。其下还有华丽的八角座围以雕刻精致的龙纹栏板和雕刻有狮子的望柱。综观华表的总体造型,它是在传统形式基础上的升华,同时我们也看到,华表本质上也是中西文化合璧的完美象征。
从天安门的华表石桥到二大殿三台玉阶石雕,以至后宫御花园的石刻,都是配以绚丽花纹图案的龙、凤主题飞舞的世界。
故宫是明清王朝最高等级的建筑,凡重要的国务活动和典礼都在这里举行。其四坡重檐式建筑庄严肃穆,金色的琉璃瓦与色彩斑斓的彩绘交映生辉,庞大的红色建筑壁体之下,必以浅白而深广的石雕构件组合作为对比铺垫。才能烘托出壮丽而完美无缺的帝宫气派。
事实上,故宫主殿的台基、阶梯栏杆、走道、中庭、石桥,皆为各种石雕艺术形式的有机组合。如汉白玉的栏杆上雕镂各种装饰和图案,大殿下的阶梯正中是汉白玉的长形石雕板向两端延伸,实为二方连续的石刻高浮雕图案,主题依次为海水江涯、卷云中是群龙戏珠向前推进,气势逼人,边饰则为浅浮雕的二方连续缠枝蕃花带纹。站在台阶上远视,它犹如一幅无尽延伸的壮美画卷。据认为,这些石雕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下令凿去原有的明代纹饰后重新雕刻而成的。不过,从现有的石栏杆边饰花纹,我们仍可看出明清故宫石雕还是承袭了宋元以来的装饰纹样和技法。
综观明清的皇宫园林,其建筑石刻运用的广泛,可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如大殿基座有突出的兽形圆雕装饰,月台上的日规、嘉量也是石雕。如今,颐和园的船形建筑石舫,石砌的十七孔桥,还有那些随处可见的石雕雄狮,可以说都深印在许多中外游人的心目中了。它们雄辩地反映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世界上最优秀最伟大的建筑都离不开石雕装饰构件。
在清代的皇家园林中,圆明园是被称为“万园之园”的伟大园林,令人痛心的是它于1860年被焚毁于八国侵略联军之手。如今,我们从园中废墟残存的石雕建筑遗迹,仍可窥视到这座绝冠古今的园林建筑艺术的一些风貌。
所谓的圆明园西洋楼旧址,它位于圆明三园的东北部,长春园北端,是仿照瑞士、法国等宫殿园林建筑的一处欧洲风格的宫苑,它原占地百余亩,创建于清乾隆十二年(1747),是由法国传教士蒋友仁、王致诚和意大利画家郎世宁等人设计的,主要景区有谐奇趣、方外观、喷水池等。这些建筑和陈设虽多具西洋特色,但它也注重结合我国传统的砖雕、琉璃饰件和叠石雕刻的技术,实体现了欧洲式建筑的民族化。圆明园伟大的石刻艺术,既证明了中华民族具有吸收一切优秀外来文化的博大胸怀,也暗示着古老中国迈向近代文明的不可逆转的趋势。
明清建筑广泛运用石刻艺术形式的例子,可说是不胜枚举。
如众所周知的北京天坛,那是明清两朝皇帝祭天与祈祷丰年的场所,其主体建筑之下的基座、白石圆坛、石构件上都雕刻有十分精丽的装饰。它们都是在朝廷官府的控制之下,为适应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以及奢侈豪华的生活等各种需要创作的,这在陵墓建筑上也反映得十分突出。
现今,在安徽凤阳的皇陵、南京的明孝陵、北京的十三陵、河北遵化的清东陵、河北易县的清西陵等处,都保留有大量的明清陵墓石刻。
以凤阳明皇陵为例,它首创明清两代陵墓宏大石雕群的先河。这里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父母、兄嫂、侄子的葬地,洪武十一年(1378)建成。在通向陵墓的深远神道上,相对刻置麒麟2对、狮4对、虎4对、华表2对、马与控马手6对、豹1对、羊4对、文臣2对、武将2对、太监2对,共32对,为历代帝陵中石雕群像最多的一处。
以明成祖为首的明十三位皇帝的陵墓,散布坐落在今北京昌平三面环山、群峰耸立的天寿山南麓,这就是与雄伟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的明十三陵。为了衬托出帝陵区深不可测及其庄严肃穆的风貌,这里采用了一系列的石刻艺术形象来加强帝陵建筑群的宏伟效果。
例如,陵区山口外的石牌坊为入口,牌坊的中线正对着远方天寿山主峰。牌坊起源于汉代坊墙上的坊门,宋以后里坊制瓦解,但坊门脱离坊墙的形式仍然存在,并成为象征性的门——牌坊。它处于显著的交通位置,一是具有装饰的功能,同时还具有表彰功德的纪念意义。明十三陵的石牌坊,实为石刻艺术的杰作。它象征性地模仿木结构建筑,高约14米,宽约29米,以汉白玉石构件组成,柱脚浮雕蛟龙云海翻腾,雄狮戏球,枋额上镂刻绚丽光彩的云纹,仿木结构雕镂得一丝不苟,为五间六柱十一楼的雄伟石刻建筑。
石牌坊作为陵区神道石刻的前奏,由此北往,经大红门、碑亭,石像的雕刻一直延伸到长凌外围的龙凤门。这些用巨大整石雕刻的文臣、武将、象、骆驼、马等造型,写实生动,刀法娴熟而明快洗练。
明代高超的石雕技术也反映在陵墓地宫的构筑上。明陵经发掘的有定陵地宫,它用巨石券构而成,门券上都雕有龙凤和吻兽,这些石拱结构天衣无缝,雕工极为精致,至今仍固若金汤。
清代陵墓石刻,也基本上沿袭了明陵旧制,皆有石牌坊、神道石刻的组合。只是地宫的石雕装饰有所加强。尤其清裕陵地宫,是石构建筑与石雕艺术结合的集大成者。图88乾隆帝裕陵地宫,是用汉白玉中最上品的“艾青叶”雕砌而成,其券顶、墙面、门扇、过道均雕刻有佛教内容的浮雕,刻工细致华美,姿态各异的立式菩萨,仪态端详的佛像与精丽的花纹图案,藏文和梵文的装饰经咒文字,组成了有机和谐的画面。这些石构件都预先雕琢,经试拼后再安砌,浑然一体,不见接缝,其工艺之精湛,为古代帝陵所罕见。
自清前期盛世之后,中国封建社会逐渐走向衰落,政局动荡,内忧外患迭起,但统治者并没有放弃其繁文缛节和穷奢极欲的生活,如今残留在清东陵等处的各种石刻艺术,规模宏大,历朝层出不穷就是明证。而且,在这些石刻艺术上还留下了时代的急风骤雨的痕迹。
在清末的戊戌变法前后,阶级与民族矛盾空前尖锐,中国社会在生死存亡的历史十字路口上正面临着新旧势力的搏杀,结果是保守的太后一党战胜了革新派,光绪帝被囚禁,康、梁亡命海外,鼓吹变法者惨遭杀害。慈禧寝陵隆恩殿前的阶石雕刻图案,就折射出这一历史背景。这方阶石上的龙凤图案,表面上是表现对立统一的均衡构图,意味深长的是飞凤却凌驾于蟠龙之上,实为暗喻皇太后与皇帝关系的错位实质。
元明清王朝的石刻艺术成就辉煌灿烂,细审之,我们察觉到其中仍具有十分浓厚的宗教色彩。在元代,除了建筑石刻有佛教密宗喇嘛教艺术的影响,在佛寺、石窟中也常见密宗造像。甚至还产生了一些陌生的救度佛母、马哈哥剌等神像。一方面,外来艺术的冲击仍然存在,如元代以后的佛像雕刻,即受尼泊尔艺术家阿尼哥的一些影响,其弟子刘元,所作佛像。宽眉细腰,这种形式在西藏佛像和清代喇嘛教雕刻中可谓一脉相承。但是绝大多数的佛教造像,自唐代以后,就日趋中国化了,作品中的衣饰、背景、用具皆与云冈造像为代表的早期风格样式相去甚远。
在元代,道教也极为盛行,仅次于佛教。远在金大定七年(1167),王重阳创全真教派,其弟子丘处机得到了成吉思汗的礼遇。其后,全真教著名道士宋德方及其门徒于蒙古窝阔台(太宗)统治时期(1234—1239),在今山西太原西南的龙山之巅,修建了道教石窟。
龙山石窟有大小洞窟8个。洞窟分别凿刻有全真道祖师及其著名弟子,以及三清尊神等道教造像,除了个别有模仿佛教涅般木造像者,均具有自身独特的风格。
元代佛塔不及前代著名,不过江苏吴县万佛石塔(大德十年),以及广东南雄等地的石塔和石经幢的石雕艺术,还是能够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元代雕塑的丰富性及其成就。
明清时期,各地佛教、道教塑像盛行泥塑,石刻造像就相对衰落了。西藏地区自7世纪中叶起,就逐渐成了佛教的胜地,佛教艺术包括雕塑也蔚成大观。但后者取材庞杂,佛教石雕较少,且受到印度古佛教艺术的较多影响,因而其雕刻艺术具有区别于内地的强烈地方色彩。到了元明清时代,由于西藏喇嘛佛教受到最高统治者的尊崇,就如我们前述所说,其佛教艺术的形式,对内地和京师的石雕创作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元代蒙古贵族的习俗与中原汉人不同,因而作为世俗生活反映的墓葬人俑和明器,已不多见,仍然因袭旧习俗的少数汉族官僚虽用雕塑人俑和明器随葬,但也罕见石刻作品。反而是为适应各种生活摆设玩赏的小石雕日渐增多,其所表现的题材和形式也多种多样。这是石雕艺术挣脱宗教的束缚,逐步走向现实表现的一种趋势。
明清时期,作为案头摆设的小型装饰性石雕更为常见,其所表现的观音菩萨、罗汉、达摩、寿星、八仙之类题材,使得宗教的崇拜偶像,已经从神坛走向千家万户,成了人们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形象。
中国古代石雕艺术是极其丰富多彩的,它们既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也是艺术家创造生活的记录;它既表现了统治阶级的意志,也反映了人民的心声。作为一种最为普遍,最为概括,最有感染力的艺术形式,其价值是多重性的,可以说是融科学、历史和艺术的魅力为一体。例如,晚清的太平天国革命,波澜壮阔,在中国被压迫人民的反抗斗争史上,曾写下了光辉不朽的一页。同样,太平天国的石雕工艺美术,也如同其卓绝的反抗斗争精神一样,给传统的石雕图案形式,注入了“革故鼎新”的活力,著名的“太平天书图”石刻,就是用形象比喻的手法,把太平天国革命的号令和战斗檄文运甩到建筑石刻装饰之上。如“直捣清廷”石雕图案,描写一只正在前进的战船,船头上有一只行将坠落的蜻蜓,用“蜻蜓”与“清廷”同音,表示彻底推翻腐朽的清政府的无畏决心。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当现代人的“黎明曙光”初露,石雕艺术就伴随着文明的进化,与美术史的演进升华相始终。尽管它形式多样,千变万化,但与其他艺术门类一样,其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中也具有一般的同一性特征,它具有自身独特的表现形式,也具有同其他造型艺术的共通之处。从本质上说,它还是古先民把握、改造和创造世界的一种诉诸于情感和理智的方式。
传统的古石雕文物世界精深博大,远非小书所能一一述及。
考古发现和传世的石雕文物中存在大量的优秀作品,其中既蕴藏着无数的奥秘,也是我们从中发掘再创造的不枯竭源泉。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地下石刻和地上的传世石雕文物,还存在着许多我们迄今尚未了解认识的奇珍。如今,随着物质文明的不断提高,对美的追求也渗透到人们的衣食住行,如果我们能进一步提高对古石雕文物的艺术鉴赏力,那么这对弘扬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为谱写新时期伟大的历史篇章,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