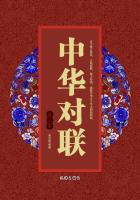每每看见漂亮的灯具,我就会想起童年的小油灯。那是吐着火星和希望的油灯,它会将吞噬视角的黑夜刺破和化解,给黑夜的凝重氛围带去意想不到的祥和与温情。
从记事起,我家那半圆形陶制油灯,就成了我和弟弟的宝贝。乡村的傍晚,天一擦黑,生产队收工,家家户户便掌起了灯。母亲和姐姐顾不得休息,乘着夜色不太深,匆匆做起晚饭。夜幕下,家里的人气和色调才略略浓一些,大人们才有时间小聚闲谈,饿了的小狗在我们脚下窜来窜去的。就在昏暗而温柔的油灯下,漆黑的夜也有些激动,一家人吃饭、聊天;我和弟弟一人一盏油灯写作业、读书,然后揉着有些干涩的眼睛甜美地睡去。
小时候我一直不解,为什么晚上母亲的针线活永远也做不完?长大才懂,一家老少的穿戴全是她利用夜晚一针一线做出来的。所以,至今记忆中的夜晚都是母亲忙碌的身影。八岁以前,我一直与母亲住在一起的,现在算来,那时母亲也就四十几岁的人了,却已是华发满头。油灯下的母亲总是打禅般盘腿坐在窗台边,凑近油灯缝新补旧。睡不着时,我总躺在被窝里看着母亲穿针引线的动作,她的目光是那么专注、凝重、娴熟而富有节奏,感觉不是在走针,而是在构思创作一幅只有儿子才能读懂的作品。因为光线暗的原因,有时穿针引线是困难的,要么扎了手,要么凑得太近,头发被灯火烧得发响。“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点灯熬油的日子里永远都是母爱的积累。小油灯下母亲的剪影,如同油画般美丽,小屋是那么的静谧和温馨,动听的纳鞋声慢慢把我带入梦乡。
冬天的午夜,母亲偶尔为我们炒黄豆吃,那时就会有豆香和“啪啪”的豆跳声一起冒出来,我会手里拿着小油灯,听话地守在灶旁。寒冷中,我和弟弟一副喜悦的馋相被灶内柴火发出的亮光写满整个小脸,甚至于为几粒豆子的分配不均也要争一番。外面下了雨雪,母亲就着灯光做着针线活,会给我讲起一些传说故事,回忆起她小时候的那些颠沛流离和难以糊口的岁月,小屋里充满了我好奇的疑问、稚气的表白和愤然不平。
府河风带着狂热和无奈无数次地穿越树林、田野和荒原。我突然觉得,小油灯一直从我岁月的记忆之初亮到现在。常回首,看到的仍是一盏昏暗的小油灯。这时,我的心绪总是涌动着难以平静的海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