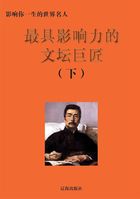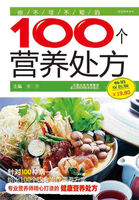1645年秋天,莫里哀和患难与共的玛德隆·柏扎尔一家共同商量,如何度过难关,继续努力,完成理想的戏剧事业。这时,老演员查理·杜非朗领导的流动喜剧团准备离开巴黎,到外省去巡回演出。莫里哀和他的朋友们认为,也许这条路子能开辟新径,便决定一起加入这个剧团。
从1645年秋天到1658年10月,莫里哀和他的伙伴们在外省整整流浪了13年。这13年,对莫里哀来说是一个生活体验和艺术训练的大学校,他在这一阶段所形成的思想立场和艺术经验,对他一生的创作都有着巨大的影响。这一时期,他走遍了大半个法国,这在法国古典诗人、作家中还是少有的。
莫里哀在外省的流浪生活是他24到36岁时期,正如拉布律耶尔在《论人》一书中所说:“谁要是投身到人民大众之中或者到外省去走走,只要他有眼睛,就很快会有新奇发现。他在那儿能看到他没有想到过的新鲜东西,他不可能有一点儿怀疑;他通过经常不断的体验,逐步加深对人类的认识;他能计算出大约在多少个不同的方面,人是令人难以忍受的。”的的确确,莫里哀在此期间积累了许多宝贵的资料、观察记录和艺术经验。一长串各式各样的人物在他眼前掠过:达官显贵、贵族和小贵族、乡绅、以在市政府里任职而自豪的市民、大小城市中傲慢的女人和女才子、商人、法官、店主、农民……他能够始终自如地向国王提供节日庆典上的娱乐节目;当收入下降时,他能为自己的剧团十分迅速地写出剧本;这是因为在他的头脑里或笔记中,存有大量的提纲、草稿、计划、一些试演过或未曾试演过的滑稽片断。此外,还存有一些舞台动作和表演的草图以及由观众的某个反应启发的、就在舞台上感受到的表演节奏。他多产的秘密就是这个存放在内心之中的取之不竭的剧目库,每当需要充实剧情,搞些新的噱头和高潮时,他那戏剧的想象力就到内心的剧目库中去汲取营养了。莫里哀的想象力出奇地发达,并不断得到外界事物的补充和刺激。在外省的十三年流浪生活赋予他认识真理的本领,不容置疑的是,在同外省居民的接触中,根据他的所见所闻,他锻炼并加强了自己的幽默讽刺能力。
杜非朗剧团离开巴黎后,主要在法国南部及中部一带活动。剧团主要是在农村集市和小城镇演出,观众主要是农民和下层市民。17世纪的法国,君主专制制度日益巩固,宫廷里穷奢极欲,上层统治阶级过着豪华的生活,但是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对广大农民的残酷剥削的基础之上的。当时法国共有1900万人口,农民占3/4,他们过着贫苦的日子。宫廷的挥霍、教会的压榨、官吏的贪污,再加上连年的战争,使农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非人的境遇逼得农民铤而走险,因此17世纪法国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没有停息过。法国南部虽说稍微安定,但是,广大农村濒于破产的情景同样不堪入目。
莫里哀在巴黎不可能看到、甚至都不可能想象到农村的这一切,这样的情景自然不能不对他的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
流浪剧团在外省的遭遇也是非常悲惨的。剧团出发时,演员们都挤在一下雨便漏的篷车里,坐在装戏服、内衣和家具的木箱上。扑扇着翅膀的鸡也装在同一辆车内,车里发出阵阵腐肉和陈面包的气味,这是由于常常要带着数天的食物和数月的演出用具。男演员几乎总是步行。上坡时,女演员也下车步行。路途不安全,自从黎士留红衣主教和国王路易十三逝世以后,战争又起,强盗拦截行人,往往抢个分文不留。不管是法国兵还是西班牙兵,他们想要什么就必须给他们,为了讨好他们,让他们走开,还要给他们演出。路途遥远,马匹跌伤,车轮损坏,河水猛涨,许多困难折磨着他们。天色晚了,得找个地方过夜,他们走到邻近的农家。农妇一看见他们就喊:“喂!一群流浪汉!快看好咱们的鸡!”他们经常住在农夫的谷仓里。在冬季,天寒雪飘,他们往往互相依偎着,在车里过夜;在夏天,有时他们就睡在草垛里。每到目的地,又要去找当地的行政官以及警察,请他们批准演出。如果允许演出就要寻找场地,要预先付钱、打扫、洗刷、搭台等等。衣服刷干净,舞台布置好,这时本地教士跑来了,嚷嚷道:“来了一帮戏子!倒霉!”然后这个教士就会赶紧跑去找警察、贵族、总督,演员们经常是被迫当天就开拔走。演员们质问道:“我们人困马乏,无衣无食,上哪儿去呀?到下一个城市,足有三天路程呢。”教士则回答说:“那你们跟大家一样干活吧,那样就会有饭吃啦。我们这里不需要懒汉和坏人。”演员们只好重新上路,跟在那些实在拉不动东西的牲口后面。到了上坡时,他们还得推车。他们就这样挨时度日,往前赶路,如果没有钱就要饿肚子。
杜非朗是一位老演员,多年来为波尔多总督艾贝尔农公爵当差。公爵每年给杜非朗一笔钱,叫做年金,让这个剧团每年为他演出若干场。其他时间,剧团只好在附近城市演出,以维持生活。当剧团团长不容易,什么都要知道,什么都要过问。既要管马匹车辆,又要防盗贼和大兵,还要应付行政官员和警察局长、贵族老爷和教堂教士,还不能忘记剧场和金钱、男服和女装,不能忘记一天三顿饭,最后还要关心那些难伺候的男女演员,必须给每个人分一个角色,并且要让他们接受,然后让演员学会台词,再上台排演。假如仅是这些,杜非朗还对付得来。可是经常是不知演什么好。可以给贵族老爷们和大城市里几个富有资产者演一些悲剧,但是这些剧目不适宜在小城市里演,更不可在乡村演,至少不可常演。在法国,真正的喜剧已经被遗忘了。人们只知道闹剧:脸上涂红抹白,儿子、女儿、妻子、受骗的丈夫一窝蜂涌上,这些人用棍棒厮打、摔倒、转动眼珠、呼扇鼻子、摇晃耳朵,最后被人装进麻袋。台词根本就没有书面记录,每个演员凭着老套路都知道该说些什么,不幸的是观众也知道。到最后,能付钱的人寥寥无几。在大城市里也如此,所以杜非朗剧团无法在波尔多久留。人们可以在芒斯、南特、阿尔比、卡尔卡森、贝兹那等城市遇到这个流浪剧团。返回波尔多时,如果那位公爵老爷能如约付钱,如果大家能够重新找到工作和住所而没有让另外一个剧团抢走地盘,那么作为这个剧团的团长就算走运了。
杜非朗很快发现莫里哀比他更会同世上的权贵们打交道。这个年轻人,严肃,有礼,讨人喜欢,他还是一位优秀致辞人,戏剧开演前先由他向观众介绍演员和剧情。他甚至不时写一些短小闹剧,他写的这些小戏已经不同于通常演的那种闹剧。有一天,大约是1650年,艾贝尔农公爵离开了波尔多。剧团失去了靠山。怎么办?杜非朗向众人询问。莫里哀建议去贝兹那城,说:“我听说孔蒂亲王要路过那里。我和他都在同一所学校里上过学。不过他比我年轻多了,而且又是亲王,因此,我从来没有同他讲过话。不过他总不会天天遇到当演员的老同学吧。也许我能使他对我们发生兴趣?”柏扎尔一家人高呼:“巴狄斯特万岁,我们走吧!”杜非朗这时说:“朋友们,我上了年纪。如果你们允许,我要留在剧团里并作为你们的一个成员随同你们去贝兹那。不过要由莫里哀来率领你们去。他已经比我更懂世故。请相信我,如果有谁能使我们解脱困境,带领我们有朝一日回到巴黎,这个人就是他。”
莫里哀以其威望博得剧团成员的拥护,接替了杜非朗的位置。从此,莫里哀不但是演员,而且成了剧团的领导人。莫里哀又重新启用了“光耀剧团”的名字,他以里昂作为剧团的固定住所,经常率领剧团到别的地方去作短期公演。莫里哀很快表现出他的卓越的活动能力。他一方面与政府当局、与各种社会势力打交道,为剧团的演出活动排除障碍。大约就在莫里哀开始担任剧团领导人的前后,由于莫里哀的努力钻营,还给剧团挂上了一面亲王的旗帜。这样,他们仗着法王兄弟孔蒂的招牌,减少了社会恶势力对他们的无理刁难和压迫。另一方面莫里哀开始着手考虑剧团的长久大计。他感到一个剧团如果总演一些普通的剧目,没有自己的特色,那是办不好的。为此他决心解决剧目问题。他曾几次去巴黎寻找好剧本,可是每次都是失望而归。
在外省流浪的十三年,莫里哀不但了解了社会和人民,而且在此其间,他广泛学习民间艺术和人民的艺术欣赏习惯,并从中发现了自己的真正天才。从前,在巴黎光耀剧团的时候,他是专门扮演情夫角色的。其实,他扮演这种角色,既没有内心的激情,更不具备外表条件,因为他长得又高又瘦,大嘴厚唇,黑眉宽鼻,棕色脸,这在法国人中显得有些奇异。所以,莫里哀早期的表演很不成功。在流浪剧团他改为专演喜剧中的滑稽角色。自从扮演这种角色以后,莫里哀的戏剧艺术便突飞猛进,他的声誉也就一天天高起来。
莫里哀在外省时有许多逸闻趣事。在贝兹那时,莫里哀长时间呆在理发师热利的铺子里。他在那儿静静地、聚精会神地——他作为一个“静观者”——观察那些顾客,听顾客们在刀剪声中或在等待洗头和刮脸的空隙中聊天。
在巴黎和法国南部的流浪演出的经验使莫里哀深深懂得,剧团要得到发展,必须有自己的剧目。他决心自力更生,自己为剧团编写喜剧剧本。当时的法国时尚高雅,重视悲剧,看不起喜剧,更看不起闹剧。一般人都认为那种东西不登大雅之堂。莫里哀最初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在巴黎参加剧团时,希望自己成为悲剧演员。加入流浪剧团后,起初也是演悲剧。后来,莫里哀广泛地接触了流行在法国民间的闹剧和意大利即兴喜剧。这种戏只有演出提纲,没有固定的脚本,演员演出时即兴编词,主要演员一般都戴面具,人物有定型,情节有套路。意大利即兴喜剧有比较高的艺术技巧,在当时欧洲各国风靡一时。法国闹剧用滑稽戏谑的情节,插科打浑的手法来表现世态人情,风格粗犷泼辣。这种戏当时在巴黎已经衰落下去,在外省却相当流行。莫里哀在外省流浪期间,通过学习这两种戏剧,掌握了喜剧艺术的技巧。
莫里哀把法国民间闹剧和意大利即兴喜剧结合在一起,剧情模仿闹剧的滑稽性,脚本只有散文形式的提纲,演员可以在演出时即兴编词。这些脚本一般短小精悍,生动活泼。当时,莫里哀写了许多独幕剧,但这些剧本大都失传了。只有两部五幕诗体喜剧流传下来,这就是1653年和1654年分别写成并上演的《冒失鬼》和《情仇》。这两部喜剧的取材及表演手法都是来自于民间,是他深入群众生活的收获。这两部喜剧,内容清新,情节也非常紧张。《冒失鬼》是莫里哀在外省所写的剧本中流传至今最早的一部。剧情发生在意大利,仆人玛斯加里尔拥有无穷无尽的智慧,号称“骗子大王”,为了帮助主人筹备一笔巨款去赎回其钟爱的女子,他想出了一连串的办法。他的计谋每次都被莽撞的主人破坏,但他的新招还是层出不穷。他帮助主人并不是一种奴才的忠心,而是为了显示自己才能超群,表现一种自尊心和自信心;相比之下,贵族人物和资产阶级的人物都显得愚蠢无能。
《冒失鬼》于1653年1月上演,莫里哀亲自扮演玛斯加里尔,这部戏的成功超出了莫里哀和剧团人们的期望与想象。在里昂初次上演之后,观众便蜂拥而至奔向售票处。曾经有这样的事:两个贵族在拥挤时吵了起来,吵得很凶,甚至进行了决斗。当时里昂还有一个名叫“米塔拉”的流浪剧团见状,便认为自己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干脆关门解散了。“米塔拉”剧团的一些优秀演员纷纷投奔莫里哀的剧团,从而大大壮大了莫里哀剧团的实力。特别是来了两位出色的女演员:德·布里和苔莱扎·玛尔吉扎。德·布里是位杰出的演员,擅长演情妇角色;苔莱扎·玛尔吉扎的美貌和舞姿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每次出场,都把男人们搞得晕头转向,甚至莫里哀也曾为她痴迷过一段时间,不过很快迷途知返,恢复了与玛德隆·柏扎尔的亲密关系。玛尔吉扎是无与伦比的悲剧和舞蹈演员。
演出的巨大成功,使光耀剧团一跃而成为外省最有名气的剧团之一,甚至首都巴黎的社会上层人物也非常注意它;莫里哀自然也成了一位颇有名气的喜剧演员和作家了。随着剧团声望的增加,这个剧团的组织也越来越壮大了。许多演员以加入该剧团为荣幸。
这时,玛德隆的小妹妹也加入了这个大家庭。玛德隆的妹妹叫阿尔芒德·柏扎尔,小时又好玩又可爱,她像爱父兄一样地爱莫里哀。她不懂事,总爱叫莫里哀“小丈夫”。莫里哀则管她叫“莫努”,经常把她抱在膝盖上逗她玩。莫里哀每天工作非常繁忙,他很高兴不时地同一个天真可爱的孩子玩玩谈谈。莫努一直很瘦削,长得也不很漂亮。后来似乎是在突然间,小莫努长成了一个美丽的少女。莫里哀在这朵青春蓓蕾中大概回忆到一点从前的玛德隆的神采,想当初就是这位玛德隆有足够的魅力把他拉出波克兰家,使他由一个资产阶级少爷变成了闯荡江湖的“戏子”,使他居无定所,游荡在法国条条大路和处处乡镇间。长大的莫努痴心地爱着莫里哀,发誓一生只嫁他作丈夫。于是,莫里哀就和她结婚了。这件事伤害了莫努的姐姐玛德隆的感情,但这并不妨碍她与莫里哀在长期患难与共中建立的深厚友谊。实际上,在所有女性中,玛德隆·柏扎尔是莫里哀最忠诚最信任的知己。
莫里哀的剧团是一个快乐融洽的大家庭。大家欢声笑语,日子过得非常甜美。有一天玛德隆的一个兄弟带着一个名叫沙尔·达苏西的人来吃晚饭。达苏西为人很滑稽,爱讲故事,大家都爱听他说话。忽然,他发现了挂在墙上的一只号角,便把它取了下来,一面吹一面绕着桌子追女仆。他吹着号角,跑出去赌钱,输得精光,连衬衣也输掉了,回来时,脖子上唯一剩下的就是那只号角了。他说:“号角是你们的财产,我没有拿它下赌注。”莫里哀十分赏识和同情达苏西,从此以后,不管他做出什么蠢事都能得到莫里哀的原谅。达苏西后来写道:“我不能离开这样好的朋友们。我们在里昂一起度过了三个月。跟他们在一起,每天都像过节……我跟随他们到了阿维尼翁,后来又到贝兹那,一个人能有像莫里哀和柏扎尔一家人这样的朋友,是永远不会当穷光蛋的,我从来没有如此富有过,如此高兴过。他们像对亲人一样,对我讲话。俗话说:兄弟之间感情再好,一个养活另一个,过了一个月也会厌烦的。但是他们这些人比任何亲兄弟还要好。我整整一个冬天在他们桌上吃饭,他们也不厌烦。”他曾写了首打油诗纪念这一段生活:“美味七八盘,生活真舒坦。餐桌多丰满,肥我穷光蛋。”达苏西感慨道:“我可以这样写,我在他们那里如同在自家。只有在他们中间我才能遇到如此的善意和礼遇。是的,他们完全有资格在人间代表他们在戏中所扮演的君子。”
莫里哀的剧团在外省演出一直得到皇亲孔蒂亲王的资助和支持,孔蒂亲王是莫里哀在克莱蒙中学的同学,他每年付给剧团一笔年金,剧团打着“孔蒂亲王剧团”的旗号,每年也专为亲王演出他喜欢的剧目。孔蒂亲王开始十分赏识莫里哀的才干,曾命令莫里哀接替他死去的秘书的职位。对于一般人来说,这自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是一个借机攀龙附凤向上爬的机遇。但是莫里哀已将一生奉献给了戏剧事业,而且他从心底里就蔑视权贵,另外,莫里哀也舍不得他的那些患难与共的伙伴们,他说,那么多的伙伴跟我远道而来,我去作官,他们怎么办呢?他们相信我,依靠我,我怎么能忍心抛弃他们。所以莫里哀费了很大的力气,以最委婉的方式,推说体力不足以胜任此职,才总算免掉了这一任命。于是,剧团在他的领导下又活跃在法国的大小城镇。
可是,1657年,孔蒂亲王没有再支付给剧团年金,而且他也禁止演员们再打他的旗号。原来,一个具有雄辩口才的主教,注意到孔蒂亲王对戏剧的嗜好,就来对他说,一个人无论在世上有多高的地位,他仍然应当更多地想到拯救自己的灵魂。如果他已经想到了这一点,那么首先应当像逃避火灾那样逃避喜剧演员们的演出,为的是今后不堕入地狱。孔蒂亲王接受了主教的训诫,向他左右的人宣称,今后他甚至害怕见到喜剧演员了。
莫里哀再一次孤立无援了。难道他还要继续流浪各省,挨个儿央求贵族老爷们,而且到头来还是白跑一场吗?
可这时的莫里哀已不是13年前被迫流浪他乡青春冲动的少年郎,在无数次艰辛磨难和数不尽的屈辱与斗争中,莫里哀已成熟起来;而且莫里哀觉得剧团和他本人已羽翼丰满,完全可以回到戏剧的大本营——首都巴黎闯一番天下。当时的法国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律:在外省无论怎么出名都成不了著名艺术家;要想成功,只能在巴黎,在国王身边。这时玛德隆虽然依旧美丽,然而时间流逝,她快40岁了。莫里哀也人到中年。强烈的在戏剧领域建功立业的雄心也促使莫里哀不能再等待了,他有信心在巴黎开辟一个戏剧创作的新时代。
而被陈词滥调笼罩着的巴黎剧坛也需要一位伟大的斗士来冲垮一片郁闷之气。时代造就了戏剧天才莫里哀,他终于要大鹏展翅,向世人昭示其犀利的思想锋芒和迷人的艺术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