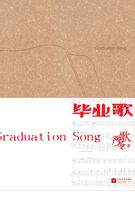下午是先接到袁莉的电话,问他去不去她家里过中秋,是她妈的意思,黄土塬推辞了。接着意外地接到红与黑小姐的电话,艺名兰茵本名朱墨的那位。黄土塬这天看了司汤达的名著《红与黑》,突然发现朱墨这个名字倒是和这本名著的名字相似得很,于是私下里叫她红与黑小姐。红与黑小姐自那日起不时来电话约他,黄土塬拗不过曾和她去喝了一次茶。这次红与黑小姐是请他去看晚上的时装表演,她自然是模特之一。黄土塬想到上次和她喝茶时看见她端着茶杯的姿势,人也如茶杯放在木头架子上,连带着感觉自己的关节都是硬的,想看看她真正在T台上走起标准的模特步之后,自己怕一晚上都会传染关节石化症,须有人提线才能像木偶那样动作。就推说晚上要和亲人团聚赏月,八月十五月团圆。哪知红与黑小姐早已把他打听得滴水不漏,反问,你既没结婚也没亲人,和谁团圆?黄土塬一听惊讶得呆了,他琢磨红与黑小姐准是把本市一至十位的钻石王老五的资料都详细记载了下来,作为猎取对象。以她的智力难免张冠李戴地搞错。想到滑稽处冲电话哈哈大笑,末了说:我有个干妈,今天干妈要我去她家。想来这一条也在红与黑小姐的资料之中,才得以推脱成功。
他打了电话给欧阳纫兰,又一番前思后想,直觉认为大致不会被推辞,临到拨电话时,红与黑小姐曾说过欧阳纫兰有未婚夫这句话突然而至。他一直想那和他关系不大,几天来拒绝去想。这一天来这句话却像个反复打扰的不速之客,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光顾。原来人世上的蜚短流长并非出自多么巧妙的阴谋多么睿智的安排,它自身是有生命力的,就像细菌,遇到腐败的食物就会长毛,而细菌是无处不在的,却并不能在新鲜的食物上长毛。黄土塬打了欧阳纫兰的电话,想的话分了二段,前一段说晚上有时间吗,一起赏月吃饭,在这儿顿住等她的反应,如对方犹豫就抛出后一段,说也约杨远宏一起。哪知电话一通,欧阳纫兰就有些责怪地问他前次说请她喝茶,怎么一直没请?黄土塬乐得差点跳起来,忙解释说,我早就想请的,现在推到事情上就是搪塞,我宁愿说真话。我很多次拿起电话又挂了,怕冒昧。我是一直没找到借口。欧阳纫兰说,那你怎么有空请兰茵。黄土塬不好说是兰茵打了好几次电话来逼着他请的,这点风度他还是有的,又明显听出欧阳纫兰的不满,忙一脸快活地诚恳道歉,又说,请兰茵不需要借口。欧阳纫兰比红与黑小姐聪明百倍,自然听出他的意思是对自己的郑重,也就高兴起来。接下来顺理成章,约好时间地点。
到了时间,去了约好的地方,两人几乎同时到达,谁也没等谁。两人聊了一会闲话,慢慢地语言融洽起来,这已是第三次见面,就如本是熟饭冷了以后只要加点热水就成了。欧阳纫兰说起这段时间袁莉经常去摄制组找杨远宏。黄土塬说,你觉得杨远宏这人怎么样?欧阳纫兰说,那要看哪一方面。他工作起来太要命,就像明天会死一样,是个工作狂。至于其他么——笑一笑不说话,黄土塬也不愿把话题拐到这上面来,倒了一杯红酒自斟自饮起来。
吃完饭黄土塬提议去赏月。
去过城外的小南山吗?
欧阳纫兰说,清明的时候去过的。山上有道观,道观里可以抽签的,我还摇了一签,很灵验。说完脸一红,想起那个操一口安徽话的老道士说她抽的签乃是桃花加金龟。黄土塬笑了,说,你上当了。欧阳纫兰不信,问为什么,黄土塬说,历来佛道都有各自的预卜方式,先不论灵不灵,但是佛教是抽签,道教历来是算卦。所以说你上当了。欧阳纫兰说,我倒宁可信。算卦要用龟甲或是铜钱,解说的都是周易那些怪异符号,就是卦象也都是古话,谁能听的懂呢?哪有签上那么明白,又是自己亲手抽出,只要他来一解说,前后一贯通,就皆大欢喜。想道士必定是从和尚那里学来的。黄土塬听得哈哈大笑,说,这个是深知拿来主义的道士。他把车开上出城的路,路边的灯光越来越少,四面却越来越亮,再开一气,只觉得四周茫茫的雪地一般,没有路没有田野,一股银水把一切都融化了又摊在一块薄板上,车亮着二道光在上面驶着却像停着不动。黄土塬问,在想什么?欧阳纫兰从沉思中醒转,说,在想那签。突然之间红晕上脸,偏过头去,好一会见黄土塬在专心开车,这才说,我想那抽签,一半是自己抽的,一半也靠运气,所以人生的境遇就和抽签一样,一半靠自己争取,一半还看命运。这话本来是临时勉强想着解释的,说完才感觉不妥,生怕黄土塬问起签上的内容,不由得心慌意乱。黄土塬却在几打方向盘全没有注意,原来已到了小南山。
站在山前,就见通透彻亮的一块大石头,石头也透着光,只是略微有些纹路。欧阳纫兰说,小南山成了一块石头,玉石。这山本来就不大,更缺少连绵,只是平原上多了这么一个疙瘩,如今被无处不在的月光把外衣剥了去,剥的小巧玲珑,四面都是白亮,山上是有树的,路边也有草,都在一片雪白中踪影不见,只如白光里的飞絮,飘了些白影子。等到人向山上走,人也化在白茫茫里面。顺着石径,只觉得四面都在向下流着月光,那月光是从山头上倒下来的,而这么走上去真不知会走向何处,难保不一抬头就看见眼前有株月桂,月兔和嫦娥——走入月亮中了。黄土塬把这感觉跟欧阳纫兰一说,欧阳纫兰道,吓,我觉得这已经在月亮里了,还好刚才听到满山的虫子在叫,我想,月亮里肯定是没有虫子的,这才回来。然而突然虫子都不叫了,原来耳朵习惯了细微的声音可以不往脑子里传递的,刚才黄土塬并没有听到虫鸣,欧阳纫兰一说,他又觉得满山都有虫声,才一感觉,山上的虫子作对一样突然无声,像突地掉进一个深谷里,茫然得叫人心慌。欧阳纫兰说,怎么突然又无声了。黄土塬把脚一跺,猛然间,一二声嘹亮的虫音起来示威,带领着群虫齐心协力地鸣叫。欧阳纫兰笑他是虫子头,虫王,一头大虫子。这是她第一次和他开玩笑,黄土塬听了却没有本该有的惊喜。他想起一本书上说的,一个女人把一个男人比做一种可爱的动物时,等于告诉这个男人可以为所欲为。他想的是无论什么样的男人都会在某个女人面前心甘情愿当那个无力的小动物么?这让他心忽地一痛,一根针在心上一扎,通成了一条线一个点忽忽悠悠地向下钻。银白满天满山满地的世界,只有这一点痛鲜明地属于他自己,独自在体内流淌着。他们站在山石上看,原来月光也不是静止的,看久了就看出流动,一大片白从这边增补到那边,一大片白又从那边向这边淌来。再看天上,月亮大而明亮的像要掉下来。山月看起来空蒙,原没江月给人太多的情思,所以黄土塬望了一阵之后就兴味索然。空蒙是独享的,好比听二胡独奏,如果旁边有个顽皮的孩子不时地点个爆竹捣乱,二胡是不肯打个折扣给人听的。黄土塬的思想不时就从二胡一样深幽的山月中炸一个飞花爆竹,再看欧阳纫兰,月光泼银一样地把她重新装点了一番。她来时做过修饰,穿了身短袖月白丝绸上衣,一条同样颜色的短裙,于是衣裙的颜色使它们没有,同样是白,和月光一见面就像糖溶入了水,实体化掉了,只剩味道。黄土塬觉得这人像二十五年前的又觉得和二十五年前的不一样,又觉得天上大约和二十五年前的一样又觉得和二十五年前的不一样。他不清楚是悲是喜,是想从这种感觉里走出去还是走进去,像一头被甩在岸上的鱼,面对一个水泡,那薄薄的水泡有它熟悉的河流的味道,可一头扎进去,又怕只是一个水泡,啪地一声化作一股烟气。他迷惘地看着煮沸的水一样流淌的月色,发起呆来。他由此想起了一个古老的东方寓言故事,公主那没有与之匹配身份的情人被国王处罚,面临二扇门,一扇门里是美女,一扇门里是猛兽。就在他选择的时候公主偷偷给他做了个暗示,公主暗示的到底是哪一扇门?他会选择公主暗示的那扇门还是另一扇?
他把这个故事讲给欧阳纫兰听,然后问,公主要救自己的情人,就应该指美女的那扇门,可是话又说回来,她又怎能忍受自己的情人和别的女人一起生活呢?那她暗示的又可能是猛兽的那扇门。到底会是美女还是猛兽呢?
欧阳纫兰琢磨了一会,说,我看呢,公主指的那扇门里一定是猛兽。见黄土塬定定地望着她,两眼里有点白乎乎的月色反光,便把嘴闭上,等他发问。而黄土塬久久没有开口,心想该赌气不说话,便从旁边伸过来的一株山茱萸上折了一枝,拿在手上来回地晃,这么一晃倒引来了山风,从侧面扑过来一阵风,像一个大手把他们一卷,握在手上,又一松,身后一片树枝草蔓摇动,扑扑喘喘地响起来又消散,身上略微寒了寒。黄土塬问,有些冷了吧?他流露出想回去的意思,抬手看表,见时间竟然慢的出奇,才八点多一点,不由惊奇地说,我还以为过了很久了,才半个小时。欧阳纫兰说,你以为是快了还是慢了?黄土塬一低头,她眼里也是二点白乎乎的月色反光。依着旧日的性格必然会很绅士地说巴不得再爬慢一些,比赛慢过蚂蚁,输过蜗牛。按这段时间的心事,这种说法也算的是量体裁衣,可在却不情愿说,好像在和自己的心事作对,好像是故意要去设置一点障碍,装做不懂不做声。见欧阳纫兰眼里的两点白渐渐地深入眼睛里,白的像是两粒冰晶在慢慢融化,马上就要变成两滴水流出来。他头一晕,见她的脸白的透明,两颊微微吹气一样鼓起来,恍惚地就看到二十五年前的那张脸,他仔仔细细地凝视这张脸,看月色里些微的光粒,原来可以看见的,那些月白色的光原子流淌在她的脸上,突然一暗,欧阳纫兰被他看得满脸通红,转过头去。黄土塬瞬间有伸手把她的头搬过来的想法,她的脸就像一个开关啪地一声关上了他的记忆,黄土塬手一动,突地又缩了回去。举目一望,还是在小南山的山顶,并不是二十五年前坐在一堆建筑材料上仰看的脸。兴趣如瀑布一样飞流直下,心里就只剩了瀑布下的潭水一样大的一个幽幽深深的叹息。
欧阳纫兰把手上的山茱萸一拂,笑了一笑,觉得该接上前一段的话了,她又深知对黄土塬这种阅历和年龄的男人来不得半点马虎,如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别看刚才用那种深情的眼光看自己,如果是二十岁的男人等同于上阵交锋自缚双臂,再交刃于敌,四十岁的男人也就等于是老虎打了个哈欠。她说,你那个故事啊,我说公主必定指的是猛兽那个门,知道为什么吗?黄土塬唔了一声,没想到她怎么又提起来,怔了下。欧阳纫兰说,女人的心思总是依托着男人的心思来的,我想呀,公主定是想她在做了暗示以后她的情人会怎么做,所以她指的是有猛兽的那扇门。如果情人欣然接受,证明她的情人不值得她的爱,喂了野兽也活该。反过来,如果她的情人爱她,宁愿去推另一扇门,就证明他视她超过自己的生命,那样他即使和别的女人生活在一起,公主心里也不会妒忌。黄土塬听的哎哟一声,说,可被你解开了这个专门给东西方哲人添白发的难题。其实他对这个问题已经了无兴趣了。欧阳纫兰被夸得高兴,说,你刚才肯定以为我是个嫉妒加恶毒的女人。黄土塬说哪里哪里。心里明白,她是故意把前后二段拉开,引自己的惊异,就好像梁山好汉在相交结拜之前必有一顿拳脚相加的互殴,又如美国人的谚语,想得人尊重就向对方的鼻子猛击一拳。黄土塬倒有些佩服她,先设置一个讨厌的答案,再推翻那个讨厌的答案,如此给听者心里留下远比直接说出来更深的印象和好感。因为这个印象里包含有因误解对方而出现的负疚心理和补偿心态。照例,一佩服则脑子清醒得像涂了风油精在太阳穴上,看月色也不过是月色了,眼前这个人也不过是才认识不久的一个女孩子。他说,我觉得那个情人无论推哪扇门都是对的,只要他推,不要一直站在两扇门前就好。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说,他们在山头走了一会,看见了道观白乎乎的房顶象个小蘑菇,看见了道观前的泉水,月色下的水亮白地一闪一闪,好像有一只手在搅,又说了一会话,这才拾阶下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