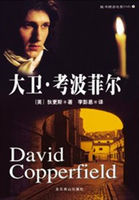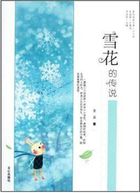全天下宾馆客房都是一个模子拓出来的,只有名字的区别。
“拥抱大海,多么诗意的店名。房间的色彩以蓝色调为主,床罩、窗帘、浴巾……甚至于牙刷、梳子的小备品都是蓝色的。店家就是让入住客人感觉到投入大海的怀抱。”她理解透了,说。
“天舒……”
他的声音春雨一样缠绵,这是她的理解。接下去她望了一眼房间里那张宽大的双人床,心里一片迷茫。
张景云上了摩托车,骑走。路过马路劳务市场,远远见老贾在揽活的人群中。他面前戳一块牌子:钻孔。
“怎么样老贾?”张景云下车子问。
“三天没活儿,按道理说安装电话、有线电视什么的,钻孔应当有活儿干,可就是……景云,你呢?”老贾问。
“可以,可以。”
“什么时候你们那儿缺人,给我推荐推荐。”老贾说。
张景云答应道:“一定,一定!”
托运公司大门前,张景云下摩托推车进院,金丹在办公楼的台阶上等他上来,说:
“景云,纪总找你谈谈。”
张景云随金丹一起上楼,她在自己的办公室门前停下,向走廊尽头指了指道“纪总在他的办公室等你。景云,谈完到我这儿来一趟。”
“哎!”张景云点下头,朝里边走去。
金丹面前的板台上,摆着一个精美包装盒,看出是一部摩托罗拉手机。她看了看,收起来,打开电脑,敲击键盘,显示器屏幕上出现:景云。她把“景云”变大字号,选择字体,变“景云”为华文彩云体,继而又变成文鼎、胡子体……她忍不住失笑。
敲门声响起,她删除屏幕上的字,正襟危坐:“请进!”
张景云进来,脸上还残留兴奋。
“谈了吧?”金丹起身倒一杯水给他,“你的办公室在一楼,挨着保安室那间,阴面,光线不太好。先将就着,以后腾出房间再给你调整。”
“汽修车间里办公蛮好的,工作也方便,搬到楼里来……”
“景云,纪总和你谈话后,你已不是普通的汽车修理工,是车队长,托运公司的中层领导,办公环境要好一些,与之配套。”她说,要说的话没全说,车队长的办公环境,代表公司的形象和实力。
“金丹,又是你起的作用。”张景云感激地说。
“是你自己胜任。”金丹笑笑道。
保安捧着一束鲜花进来,说:“金主任,有人送花给你。”
“请放在桌子上吧!”她淡淡地说。
保安放下花,转身出去。
“景云,你猜猜谁给我送的花?”她问。
“这,我怎么猜得到。”
“你的‘弟内弟’。”
“天飞?”张景云一愣道。
“天飞立体进攻,在网上给我留言,送花……”手机提示音骤然响起,她打开读:“唔,他发来短信。”
“你不是跟他谈了吗?”
“我讲得很直率,说我们俩不合适,当时他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同意我给他介绍一位姑娘,跟小晶处了一段,他突然就不同意了。”
“其实并不突然,他心里给一个人塞满,再也装不进去第二个人。”他说。
“是吗?”
“就是你,他自称是暗恋。”
“这是不可能的。”金丹态度明确。
“连他自己也认为不可能的,但是他说不会放弃,要追你到底。”
金丹淡然一笑。此话题进行不下去了,张景云说工作的事:“汽修队招一名工人的事,纪总让我和你定。”
“有这方面专长的人你不陌生,看准了就招进来,我同意。”她表态道。
“老贾过去和我一起在铁艺分社工作,钳工出身,技术不错。”张景云推荐道,要招的人不是修理汽车,修理货箱什么的,老贾正合适。
“你看行,就定吧。公司规定试用期一个月,试用期间月薪五百,正式录用月薪八百。景云,中午我请你去高句丽酒店吃饭。”
“还是我请你,是我爸妈叫我务必请你吃顿饭,我提出请你喝茶,我妈都不准许,“请我的理由呢?”
“你辛辛苦苦,精心护理我爸。”
“这顿饭先攒着,改天再请。”她说。
张家也准备吃一顿喜儿,张建国主张的,他早晨起来往下额巴抹肥皂沫,持老式剃刀子,照着镜子刮胡子,脸颊下方如同冬天的荒野一样,苍凉稀疏地长着几根胡子,刮掉它不是美观不美观,而是一种心情了。
张母做着家务,不时瞥老伴一眼,问:“今个儿啥日子,又刮胡子又洗脸的。”“心里高兴嘛,”张建国边刮胡子边说,“景云当上了车队长,你不高兴?”
“你也有高兴的时候……”老伴说。
“买条鲤鱼,吃喜!”张建国说。
张母准备晚饭,刮鱼鳞,张建国滋味地喝酒,样子很香,他端起盅,抿一口酒:
“嗬,辣得好这个得(读相;音)呀。”
“他爹,酒超标了。”
“得!”张建国仍兴致勃勃地喝酒。
“喂,我说你吃的是哪顿饭?”
“中午饭。”
“你不想撤桌了,晚饭接着吃?”张母说。
张建国撂下筷子,说:“结束,战线拉得太长也得罪人。你收拾桌子吧!景云呢?”
“景云去接二多。”她说。
“没给天舒打个电话?”他问。
“哪里找她去呀!”张母怨言道。
丛天舒在这天吃了顿丰富我们故事的晚饭,饭菜没什么特殊内容,关键在那瓶假洋酒上,造假者白酒勾兑时比例搞错,醉了我们的主人公,使下面的故事充满了酒味。
朱刚大醉,丛天舒扶他进客房,酒精作用让人发笑,他挣扎嚷道:“回别墅,回……”
“你喝成这样回不了别墅,开房休息一下,然后再说。”丛天舒半清醒半迷糊,还是知道开房。
“回……回家!”朱刚趔趄站起,随即摔倒在床上,睡过去。
她脱掉他的鞋,费力脱去他的外套,给他盖上被子,酒精魔力上来,她瞳孔焦点消散,盖在朱刚身上的被子水一样波动起来,面对诱惑的海水,她脱掉织物,蛙泳下去……三江警察今晚进行扫黄行动,数名公安人员进人宾馆。在保安、服务员配合下,公安人员逐一检查客房。
“打开门!”一间客房前,警察命服务员。
服务员用钥匙开客房。
“别动!”几名警察涌进去,喝道。
床上的丛天舒惊慌失措,用被子掩盖胸部。
“怎么,怎么啦!”朱刚惊醒,惹祸的假酒逃之夭夭。
“我们是迎宾街派出所的……请你们配合。”警察道。
赤条条的丛天舒缩在被子里,身子微微发抖。
“请出示下你们的身份证。”警察道。
朱刚把自己和丛天舒的身份怔交给警察。
“她是你什么人?”警察查验证件,问。
“我同学。”朱刚坦然自若道。
“她叫什么名字?”警察诘问。
“丛天舒。”他坦然答道。
“同学,到宾馆开房?”警察又问。
“宾馆浪漫呀……这是我们个人的私生活,隐私。”朱刚似乎看出警察在干什么,努力挺拔起来。
“对不起先生,请你们跟我们到派出所走一趟。”警察例行公事,要带走宾馆房间里的男女。
“为什么呀?”朱刚问。
没人回答他的问话,警察转过脸去,给他们时间穿衣服。
迎宾街派出所走廊,朱刚和丛天舒分别被带进两个房间,他进所长室,她进警长室。
“微机査出你家庭住址,名洲花园九号别墅,你的妻子叫罗薇,可是跟你在一起这位女士家庭住址……”李所长问,“你怎么解释?”
朱刚额头沁出细密的汗珠,理直气壮不了,态度在改变,说软话道:“所长,你放了我和那位女士,我情愿交罚款,几千都成。”
“交罚款?你怎么了?”李所长问。
“这种事公开出去,我们哪有脸……”朱刚装羞耻地说。
“开房时没想到脸面,没想到难堪?怎么才能证明她不是卖淫女,证明你们是情人的关系呢?”李所长严厉地说。
“最有力的证据有,我老婆。”朱刚厚颜道。
“怎么和她联系?”所长问。
“她出国了。”
警长室女警察也跟所长问同样的问题:“谈清楚你的身份,可以放你走。”
“我再说一遍,我们是同学,我不是卖淫妇女。”丛天舒说。
“我们也没说你是卖淫妇女,你不谈清与那个男人的关系如何证明你的清白。”女警察求真道,“你有丈夫吗?”
“有,叫张景云,住迎宾街爱民小区……”
女警察在微机上査询,疑问道:“你们户口倒是在一起,可你张景云丈夫标明未婚,你怎么解释?”
“我们没领结婚证……”
“说些什么呀?为证明你讲的都是真的,通知你丈夫来证明你一下,立即就放你。”女警察说。
丛天舒咬咬牙,说:“可以,我有个要求。”
“说吧。”
“我公公、婆婆年纪大了,心脏不好怕刺激,找我丈夫不要打电话……”
“我们会妥善安排。”女警察说。
夜里咣咣有人敲门,写作业的张一多乐颠儿去开门道:“妈妈回来啦!”
门开,警察小童出现。
“谁呀,一多?”张建国听声问。
“警察叔叔。”孙子说。
“警察?警察来干什么?”张母惊奇道。
箐察小童走近张景云,低声说:“你跟我们去趟派出所。”
“跟你们……去派出所?”张景云愣怔道。
“走吧!”小童到两位老人面前换了一副面孔,说:“大叔大婶,我们找景云有点儿事出去一下。”
“啊,啊’去吧景云。”张建国说。
“咋回事呀?”坐警车去派出所的路上,张景云问小童,“叫我去干什么?”
“到那儿你就知道了。”小童说。
张景云走进警长室,见到丛天舒一愣。
“你认识她?”女警察问。
“我妻子,她怎么啦?”张景云说。
“先别说她怎么啦,有一个问题你解释一下,既然你说她是你妻子,为什么户口上记录你未婚?”女警察问。
“我们没有登记,但是结婚了,是夫妻。”张景云说。
女警察似乎想说什么没说,问:“谁证明你们是夫妻?”
“她,我,全家人,街坊邻居、社区,都能够证明。”张景云理直气壮道,“警官同志,我妻子怎么啦,你们把她带到这来?”
“这个问题你问你妻子吧!”女警察严肃地说,“你可以带她走啦!”
张景云拉架势跟警察理论,丛天舒说:
“走吧,景云。”
“不行,我要问清楚,警察怎么可以随便抓人呢!”张景云求真道。
女警察要开口,丛天舒拉起张景云:
“走景云,出去我对你说。”
丛天舒像猎人枪口下逃脱的动物一样,一口气跑出很远,认为安全时才停下脚步,气喘吁吁的张景云赶上来,问:
“你说说怎么回事?”
“是这么回事……”丛天舒没藏没掖,最后说,“我们都喝多了酒,什么都没发生。”
张景云听完,愤怒地道:“又是朱刚!”
丛天舒把这一切归罪于警察的扫黄行动,在宾馆遇上……“不遇上,说不定发生什么!”张景云第一次冲着她大喊大叫,“你还好意思说呢!”
回到家两人直接进卧室,他用身体靠着关上门,她坐在床沿,低垂着头,神色惶惶,毕竟让警察堵在床上,又赤身裸体,她怕警察对他说这些。
“天舒,你太不像话了,去宾馆开房,让警察逮去,多丢人呐!”
“我们什么都没有……”丛天舒申辩道。
“还想有什么?让警察的扫黄大行动给碰上,带你们到派出所询问,你竟然说没有!”
“景云,你听我解释。”
“不听,不听!天舒,你一直背着我跟你那个大款同学在一起。”他终于爆发了愤怒,倒不是讨还什么,是要说说委屈,“当年我为你治病,去贪污公款,蹲了大狱……”
“景云你什么都别说啦,事情已经出了,你愿怎么想就怎么想吧。你听听我的决定,从今天起,我们离婚!”丛天舒说完跑了出去。
丛天舒从张家赌气跑出来,谁都知道她准去一个地方名洲花园别墅。
“天舒,你干什么?”这是朱刚见面的第一句话,如一桶冷水当头泼下来,“你睡在那儿也罢,脱光衣服……”
“我、我……”她吞吐道,“鬼使神差。”
“哼,鬼使神差!你脱得那样光,正好给警察撞上,人丢大啦。”他一个劲儿地责备,语言尖刻而挖苦。
她哪里受得了这个,委屈落泪道:“我想回到你的心里……”
“我说过,你铭刻在我的心里,进入血液,周身流淌了十几年,你永远是从前的天舒。”
“我对不起你……”
朱刚目光飘向墙壁,落在罗薇的巨幅照片上,罗薇的一双眼睛令朱刚顿生恐惧。
“可是,我……”丛天舒抽咽道,“我再也不能回到张家去了!”
电话铃突然间响起,朱刚拿起话筒看眼来电显示,伸出双指放在唇边,制止丛天舒出声:“墟!一”然后接电话,“是我……想,怎么不想你。是,明白,我立即去上海。”
“她要回来?”噩耗一般的消息,丛天舒陡然灰暗下去。
张景云头顶着墙,呜呜痛哭。
最不想看到的结果还是出现了,张建国大口地吸烟,面前的烟灰缸里,数颗刚抽过的烟蒂堆在里面。
“你千万别着急上火,走就走吧,她干的事,太招人恨。”张母劝慰老伴道。“你说这半斤咋就换不回八两来。景云,还有咱一大家人对她天舒没二五眼,她咋就这样绝情啊?”
“用离婚吓唬谁?反正也没登记,离了岂不更好!”
“老话说,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哪。尤其他们这种情况,叔嫂就和在一起,更不容易。”父亲说。
“离!左右是天舒先提出来的。”张母不觉得可惜,相反希望儿子快刀斩乱麻,早断早好。
“好端端的一家人……”
“到这个份儿上,惋惜啥?趁景云还年轻,再找一个比她强的人。谁愿把他俩再往一起捏谁捏吧,我是不管了。”张母说。
朱刚放下电话,再次瞟了一眼罗薇的巨幅照片,说:“她叫我去上海办一件事。”
“几天?”
“一周吧!”
“你把翠亨花园别墅钥匙给我!”丛天舒说她在那儿住几天,等罗薇回来前交回钥匙。
不料,他作出了一个让她先惊异后惊喜的决定,说:“天舒,我们一起去上海,出外玩玩,散散心。”
宾馆遭遇的阴影还笼罩着,她心有余择,到上海还要住酒店宾馆,三江的事情会不会重演啊!
“放心天舒,我会安排好。”他给她吃定心丸。
一幕只有电视剧里才能看到的场景出现在三江火车站,徐颖在一辆轿车里,注视通向候车室的路。
一辆接一辆出租车,乘客下车,走向候车室。
另一辆私家牌照的现代轿车里,警察小童也在监视候车室的人员进出。
一辆出租车停下,朱刚下车,丛天舒下车,他们带着简便的行包,一起走进候车室。
徐颖浮现得意的笑,将车开走,随后,警察小童也开走车。
驶出三江站的火车软卧包厢里,朱刚放置旅行物品。
“天飞,”丛天舒打手机,“我出外玩几天……有件事我不放心,你去看一下二姐,一定去!”
“天霞又怎么啦?”朱刚问。
“打她手机无法接通,我叫天飞去看看她。”
大姐的命令是圣旨,丛天飞不敢违抗,他立刻到天霞家来,防盗门上贴着天然气催缴单,他望着犯愣。
哗啦!他身后邻居防盗门上的小窗户开了,呈现(居女人脸部的一小部分,她问:
“你找谁?”
“找我二姐。”丛天飞指指丛天霞家的房门说。
邻居女人仔细辨认后,说:“见你来过。你二姐已经走了六七天,去找你二姐夫了。”
“她说没说去了哪儿?”
“不清楚!”
丛天飞下楼回到出租车上,拨通了丛天霞的电话:“二姐,你始终关机,在哪里?”
“秀水镇。”
“你能马上回来吗?”
“听人说你二姐夫在这一带做活儿,昨天找了,没有,今天再找找。”丛天霞问,“有什么事你?”
“大姐和姐夫闹翻,她离家出走了。”他说。
“因为什么?”
“一句半句话也说不完,见了你再细说……抓紧回来二姐,我俩想辙,劝她回到张家。”
“开弓没有回头箭,大姐既然迈出了张家的门槛,还回去干什么?何况大姐她为追求幸福,没错儿。”
“我说不过你,问题是大姐在火车上给我打的电话,去哪里没说,急死人啦!二姐,你快点回来!”丛天飞最后补上一句道,“想想张家吧!”
此时张建国自己摇轮椅到立柜前面,翻找什么,哼着一首老歌:“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牙没疼吧?怎么越听越像谁掉牙似的。”张母讥道。
“你最能埋汰我,音乐我比你懂,当兵时我是……”
“排里文艺骨干……”张母接过话头道。
“连里的好不好。”
“排里连里还不是一样,谁老提当年勇呢。撂下饭碗你就翻箱倒柜,找什么?”“头些日子晾衣服时我还看见,怎么找不到了?”他叨咕道,“毛料帽子呢?”
“找那古董啊!我当什么呢。社区排节目借去给汉奸戴,我说连人带帽子一起借去,岂不更省事……”
“你的意思我像汉奸?”
“咱可不敢诬蔑文艺骨干。”她说。
“记得真真亮亮的,社区还回来了,我顺手放起来,愣是想不起来啦。”
“准是放忘了地方,你问问景云,上周他收拾柜子看见没?”她随即朝卧室喊,“景云!”
“妈,啥事?”张景云从卧室走出,使劲睁眼睛道。
“见我毛料帽子没?”父亲问。
“喔,让我扔到北阳台那堆杂物里了。”儿子说。
“你真混,把我的帽子当成废物……景云,麻溜给我找回来!”
“爸呀,满大街你还能找到戴这种样式帽子的人吗?早该撇大道上去。”
张母说还真看见有人戴它,翻垃圾箱捡废纸袋子的那个人。
“捡纸袋子那个花子,有时拿帽子当饭碗用,使它装残羹剩饭。”张景云找回那顶破毛料帽子,父亲半抢半夺地从儿子手中拿过帽子,弹去上面的灰尘,说:“败家,真败家。”
“放那儿吧,倒出空儿我给你洗一洗。”张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