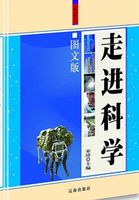出了农贸市场张景云接到刘国强电话,请他中午赶来东方山庄吃饭,他编个理由谢绝。
雅阁轿车停下,丛天霞对迎上前来的丛天舒说:“姐,我总想看看你的办公环境,没实现。”
“哟,这有什么难的,先不进餐厅,跟我到办公室去看一眼嘛。”姐姐说。
刘国强响应不热烈,木然地站在一边。
“走啊,国强。”丛天霞催促道。
山庄经理室,丛天霞坐在老板台前感觉,说:“我坐坐姐的宝座,当一次经理……”她拿腔作调,逗得刘国强、丛天舒发笑。
“天霞总想当经理。”他说。
“姐,你的位置真令人羡慕。”
桌子上的电话响起,丛天霞拿起听筒递给姐姐。
“我是天舒……手机放在家里没带……好吧,我马上过去。”
“天霞我们走吧,大姐有事。”刘国强说。
“总公司让我们去一趟,开个会。不巧,今天陪不了你们。”丛天舒歉意道。
“偏偏这个时候开会、有事……”丛天霞嘟哝道。
“鹿血膏我安排好了,你俩去吃吧。接我的车快到了,不陪你们俩了。”丛天舒说。
这一天与张景云的表现水煮黑鱼片有关的重要人物丛天舒很忙,意味着他的计划有落空的危险,换句话说,天舒可能受冲击吃不上水煮黑鱼片。
张景云腰扎围裙下厨,在菜坏上收拾鱼。
“叔,气球。”张二多玩鱼泡道。
“二多,那不是气球,是气泡。”张景云说。
小侄子眨巴眼睛,问:“鱼为什么长气泡?叔我长气泡吗?”
张景云将改好刀的鱼段放入锅中,说:“鱼长泡泡,鱼要在江河湖海里上浮下沉啊!”
张二多天真地说:“我也要长泡泡,游水……”
做鱼的油烟跑进里屋,父亲闻到剧烈地咳嗽起来,张母问:“景云你锅里做的什么,这么呛人?”
“水煮鱼片。”
“我说这么辣,看把你爸呛的。”张母给老伴捶背,“忘了跟景云说你怕呛,他放了辣椒。”
“水煮鱼片不搁辣椒咋成……”张建国说。
推开厨房窗户,调小炉灶的火苗,张景云拉上侄子离开厨房,说:“等妈妈回来,我们就吃鱼喽!”
罗氏布业公司总经理办公室里,丛天舒说:“徐颖完全变个人似的,为我们争利益,她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何止一百八十度,是三百六十度。机器设备作价,库存纱锭……都低价给我们。”朱刚笑得得意。
“是吗?!”
“天舒,我们赚啦,赚了个沟满壕平。天舒,你也算迈进罗氏布业半个门槛,应该对罗氏布业的经营内幕有所了解,我告诉你吧……都对你说了,这可是罗氏布业的核心机密。除了公司几个高管,没人知道的。”
“我刚踏入半个门榲,算是荣幸。”
“听我解释为什么说你踏人半个门槛,罗氏布业是个庞大的集团,养鹿只是其中一项业务……天舒,你千万别误会,这样说绝没拿你当外人。”
半个门槛也好,一个门槛也罢,不想进人集团更深,丛天舒这样想。
“天舒,”朱刚将一叠钱塞给她,“送二多人幼儿园,需要花费。”
“你这样帮助,我真不好意思。”
“有什么不好意思,你的事不就是我的事嘛。噢,时候不早了,走天舒,我们去吃曼波鱼。”
“今天晚上,我得回家。”她说。
“哦,不方便?”
丛天舒又改变了主意,说:“没事儿。”
“有人特地请你?”他问。
“谁请我?”
“徐颖,”他说,“她让我通知你,一起吃晚饭。”
酒店雅间一桌子海鲜,服务员端上曼波鱼。徐颖使用公筷夹鱼,放在丛天舒的盘子里。
“谢谢!”丛天舒吃到美味,这时,她的手机收到一条短信:天舒,全家人等你回来吃饭。她望眼徐颖,不好意思地说:
“对不起二位,家里有点儿事,我失陪啦。”
“特别急吗?”朱刚问。
“我得回去,你们慢用。”丛天舒离开酒店。
徐颖疑心丛天舒突然离席,是不是因为自己呀“怎么会因为你?她家的事情很多。”朱刚说。
“你们俩是老同学,旧情再续……”
“哦,你也这么看?”
桌子放好,端上碗筷,餐具极富诱惑,傻子首先受不了,张景锁嚷着:“吃鱼,哥吃鱼!”
“等嫂子回来,嫂子爱吃水煮鱼片。”张景云哄弟弟道。
张景锁安静一会儿,他对嫂子很有感情,说等她回来吃鱼他能等,但是忍耐的时间不长,食物的诱惑太大了,他说:“哥我饿啦。”
“我给你盛块儿鱼,你先垫巴垫巴。”张景云想出解决办法。
“天舒回来一起吃!”张母阻拦道,“把菜弄得乱七八糟的,也不好看。”
“景锁饿了,吃吧。”张景云说。
“挺一会儿。”张母说。
张家人继续等下去,张二多在奶奶怀里昏昏欲睡;张景锁目光向厨房投射,鼻子深吸着香味,吞咽着口水。张景云不时看墙壁上的石英钟,时针指向九点三十分,他说:
“要不咱们先吃吧,菜都凉啦。”
“再等等,景云,打电话问问天舒。”父亲说。
张景云给她重发一次短信,过会儿门响动,张景锁喊叫:
“嫂子!”
孙子张二多从奶奶怀里惊醒下地,跑向饭桌子:“吃鱼,妈回来吃鱼。”
“吃鱼,吃鱼。”张景锁拉嫂子到饭桌前。
张母注视丛天舒穿的新裙子。
“天舒你顶爱吃的黑鱼,尝尝我做的水煮鱼片,肯定不比饭馆的差。”张景云兴奋地说。
一家人围坐,开餐。张景锁、张一多、张二多夹鱼吃,很香。
张景云夹一片鱼放入丛天舒的碗里,父母的目光不约而同落在她的脸上。她送人口中一小块,大呼大叫道:
“一股柴油味儿,太难闻了!”
公公怔住,送到嘴边的筷子停滞。
“景云,”丛天舒放下筷子,捂着嘴离桌道:“你从哪儿弄来的死鱼……”
张建国撂下脸,对张母狮吼:“去把它倒掉!”
倒掉菜,张母犹豫着,家里很少吃鱼,经济条件决定吃不起鱼,差不多有几个月没闻到鱼腥了。
“你没听见?倒掉!”张建国愤怒道。
老伴的脾气她清楚,叫倒你就倒,不然摇着轮椅自己去倒,张母端起盛鱼的盆子,没走几步,傻儿子冲上来抢夺:
“妈我吃鱼,鱼……”
啪!张建国一巴掌抡向傻儿子,训斥道:
“有味能吃吗?”
傻儿子捂脸哇哇大哭,张景云把弟弟揽在怀里,默默无语。
张母端鱼进厨房,倒掉舍不得,偷偷捞出鱼片留下,藏进碗橱里,回到饭厅,碗筷堆在桌子上,桌旁空无一人。
张景云来到天舒房间,她靠坐在床头上,脸冷冰冰,他把钱放在床头柜上,说:“挖地沟结算了,一共三百二十元,买了条鱼,还剩下三百元,二多人园费……”
“你收起来吧,钱有啦。”她说。
“几千元都凑齐啦?”
“入园费解决了。景云,跟你商量一件事。”
“说吧,天舒。”
丛天舒犹豫了一阵,说:“明晚你搬过来吧。”
“明晚?”张景云一愣。
她坚定地道:“明晚。”
“是不是跟爸妈说一下?”他试探性地问。
“我去说。”丛天舒说。
猜想丛天舒突然决定结婚的日子原因没什么意义,这是张家人关心的事情结局。她同公婆谈了,就明天结婚。
“操办一下吧!”公公说。
“咱们全家吃一顿饭就成了。”她坚持简办,简到极限。
“亲朋好友请几个……”
“不请了,天霞、天飞都不请啦。”她说。
对于这样不声不响的婚礼,两位老人觉得别扭,总不像那么回事,可儿媳的决定谁修改得了。今天跟你招呼,明天就结婚,相当于突然袭击,想做什么都来不及。
“结婚是大事,有蔫巴悄儿办的吗?”张母说。
“唉,都决定了,照他们的意愿办吧。”张建国无可奈何地说,他比老伴先想通一步,什么常理呀?嫂子嫁小叔子本来超了常理,就超常理到底吧,也没什么不好,以后过的是他们俩人的日子,只要他们好好过,婚礼操不操办何妨,他想得周到,说,“准备点儿改口钱“叫啥(称呼〉没变,她仍然是你儿媳妇,也不改口。”张母说。
“过去是大儿子媳妇,现今是二儿子媳妇,一样吗?”张建国叫起真来,“一多要管景云叫爸。”
她听出老伴语调的几分凄凉,大儿子景山没了,小小的年纪啊!妻子再嫁给二儿子,喜事,他高兴不起来,痛惜和怀念掺和进这几句话里。
“景云腰里没有钱,孩子改口管他叫爸爸,总要表示表示。”张建国说。
“我给他准备。”张母说。
“明天吃饭你控制点儿,别提景山。”他嘱咐道。
“给景山上上坟,给他报个信儿。”
“别整啦,他们俩咋安排咋是。”张建国觉得此时此景提景山不合适,人都不在,世间的事他什么都不在意了,妻子再嫁天经地义,不嫁景云,也要嫁别人。
一整天里,张家全在挪床,丛天舒坚持新房选择在自己的房间里,一多、二多的床搬出,去向是一多到景云原来的房间,将来是小哥俩的房间,眼下二多年纪小,暂跟爷爷奶奶一起住。
“搬家,搬家!”傻子景锁不知咋回事,帮着抬床,他见母亲将一个大红喜字贴在嫂子门上,瞅了一会儿觉得好看,嚷着:“妈,给我贴一个。”
“景锁,听妈跟你说……”母亲对傻儿子讲解一番,直到他明白不再要贴喜字为止。结婚,他部分理解,想起游戏时的歌谣,跟二多对坐客厅里,一送一拉念道:
洞房陈设简单,一张双人床,拉大锯,扯大锻,老爷门口唱大戏。
接闺女,请女婿,小外甥,也带去,问你愿意不愿意。
被子很新。开始他们一个床上,一个椅子上分坐着,沉默良久。
“上床吧!”床上的她说。他起身,爬上床。
“上来吧!”她说。
张景云慢慢起床,丛天舒仍然睡着,他轻手轻脚走出来,直接进厨房。
“起这么早,没多睡一会儿。”张母说,她在厨房做早餐。
“妈,我做吧。”他说。
“我都做好啦。”
“妈,我今天去刷油漆。”张景云说,“先送一多去上学。”
“好,你把一多叫起来,小点儿声别把二多吵醒。”
三江市的夏天满街的树木味道,经常刮的南风把白狼山的植物气息送进城市。张景云拿着书包,送张一多上学,向公交车站走。
“终于啦。”张一多喜悦道。
“什么?”
“你给我当爸爸。”
被不明真相的天真孩子叫爸爸的人掩饰着内心的苦楚,一股致命的火药从铁器里喷出,痛疚跟随他几年,一生一世都解不脱。
“爸!”
他望着侄子,嘴唇哆嗦一下,勉强答应:“哎!”
“明天开家长会,你和妈俩谁来参加?”张一多问。
“你妈哪有时间,我来开。”
孩子雀跃道:“太好啦,爸一定来!”
时间对丛天舒不是金子,却是什么事,就是说时间给忙不完的事占据。班上今天稍稍清闲些,她给妹妹接走,驾驶新车的丛天霞兴致勃勃。
“天霞,你带我去哪儿?”
“陪同新娘洗奶浴。”
“贫嘴!洗奶浴,太浪费了吧,天霞你皮肤细嫩,还用洗奶浴?”丛天舒结婚二十几天,也算新娘子。
“越是皮肤好越要加倍呵护,牛奶十分营养皮肤。”
丛天舒轻叹口气,默默低下了头。
“怎么啦,大姐?”
蓦然想起小时候的事情,妈常说她从小喜欢牛奶,经常喝爸涮奶瓶的水。丛天舒感慨万千道:
“那会儿咱家的日子……”
“饥寒交迫。”丛天霞说。
丛家日子清苦,饥寒交迫那倒不是。父亲在翻砂厂干活,体力消耗太大,母亲给父亲吃小灶,每天喝一斤牛奶,熬牛奶的香味馋得姐妹直流口水。丛天舒无限感慨:如今天霞都用牛奶洗澡啦,总归嫁对了人,假如你嫁错人,还能用牛奶洗澡吗?她说:“说来不怕你笑话,每次涮二多喝奶的瓶子,你姐夫都舍不得倒掉,全喝了。”
“哪个姐夫?”
“还能是哪位,冰箱冻自来水,还美其名曰:景云牌矿泉水。”
“姐夫真逗,他挺会过日子。”
“老是算计口袋里的钱,即使一分钱掰八瓣花,口袋里也只有一分钱,得想办法去挣钱,填鼓口袋再研究花法。”
“大姐,问你一个私密的问题,你跟朱刚分手啦?”
丛天舒愕然,“天霞,你也这样认为?”
“难道你俩……”
“没有什么难道,我们是老同学,友谊纯洁。”
大概这样说鬼都不会相信,现实生活、影视作品里比比皆是丛天舒跟朱刚,大款和美女成为一种组合,各有所需不言而喻。所以妹妹不信,但是她还是举出了不信的人:
“景云姐夫也这样认为?”
“我们从来没谈过这个话题,他一天到晚在街上劳动累死累活,回家话都很少说。”
不交流有两种情况,要么知道不说,要么干脆不知道。丛天霞坚信是前者,他们现在是夫妻,一方允许另一方有婚外情,生活中不乏其例。
繁重的劳动能够减少烦恼,张景云是否如天霞揣度的知道妻子跟她的同学关系密切,而态度宽容?目前尚难定论。他确实劳动很繁重,此刻人便吊在过街天桥上,他手持刷子,正在漆广告牌,车辆水一样不断从下面驶过。
刷子探进桶中蘸油漆,刷向广告牌高一些的地方,他手一抖刷子从手中脱落掉下去,落在一辆经过的宝马车上,溅污了机盖子。张景云顿时吓呆了。
“喂!刷油漆那个师傅,你下来!”宝马车靠边停下来,司机气呼呼地跑过来大喊大叫。
惹了祸的张景云慢吞吞地从天桥上下来,胆战心惊地走近司机。
“你看看,油漆弄脏了车,咋办吧?”司机问道。
“对不起师傅,我擦……”
“你擦?这是什么车你知道吗?宝马,宝马啊。苍蝇朝上拉泡屎都影响美观,更何况你弄上油漆?”
张景云仍在道歉:“对不起,实在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