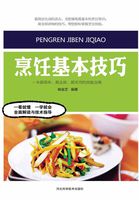至于从中国带茶种回日本种植的时间,在我国历史文献中的记载是唐代中叶。最澄(即传教大师)于唐德宗贞元年间在天台山拜道遂禅师为师,于805年(唐永贞元年)回国时,从天台山、四明山带去了不少茶子,种植于日本滋贺县。空海(即弘法大师)是不空和尚嫡传惠果的十二弟子之一。不空在唐肃宗、代宗年间,是“尊为国公,势移权贵”的最出名的大和尚,被赐有“大广智三藏”法号,他曾在五台山上建有金阁寺、文殊阁,成为当时的国际佛教中心。空海曾几次往返于日本和中国,也带去了饼茶、茶子。最澄和空海可以说是日本栽种茶树的先驱者。
宋代两度来我国的日本高僧荣西(即千光国师),对日本的茶叶传播和发展,以及后来茶道的发扬都起过很大作用,有“日本陆羽”之称。荣西第一次入宋在1168年(宋孝宗乾道四年),从四月到九月,只有短短五个多月时间,他从宁波入境,经四明山、天台山,在参拜了育王山广利寺、天台山万年寺等有名寺院后回国。第二次入宋在1187年(宋孝宗淳熙十四年),他已47岁,经当时京城临安入天台山,万年寺拜虚庵(怀敞禅师)为师。他于1191年(宋光宗绍熙二年)回国,也带去了不少茶子,先后在他主持的禅寺,如博多安国山圣福寺及脊振山灵仙寺(在今佐贺县神崎郡等地)试植。荣西除亲自推广栽种茶树外,还写了一本《吃茶养生记》,宣扬饮茶的功效,并传播了宋代各大寺院中僧侣讲经布道的行茶仪式,大大丰富了日本饮茶艺术,并促进了种茶事业的发展。
如上所述,在饮茶风尚的传播过程中,佛教僧徒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同时皇室贵族的爱好,文人学士的歌颂,医药学家的评价和推荐,茶商的宣传和推销,在各个历史阶段对各种不同阶层也都起过推广的作用,不过还应该着重指出,饮茶风尚之所以风行全球,是历代茶树种植者、茶叶制造者和茶叶工作者长期辛勤劳动的必然成果,这里所以提出佛教僧徒的作用,仅仅是从历史的一个方面着眼的。
五、饮茶的习惯
人们饮茶,大抵有这样几种不同的目的:一种是把茶当作药物,饮茶用以防治疾病。关于茶的药理功能,在第一章里已经加以介绍。由于饮茶确有健身和防治疾病的效果,很多人就把茶作为健身饮料,久而久之,养成了饮茶习惯。一种是把茶当作生活的必需品,不可一日或缺,甚至每餐必备,由于生理上的需要(一般是以肉食为主、缺乏蔬菜的地区的人,例如蒙古、康藏等牧业地区,茶叶成了该地区的必需品),从而代代相传下来。又一种是把茶视为珍贵、高尚的饮料,饮茶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是一种艺术,或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手段。这也有一定道理,生理作用与精神作用是密切相关的。《茶经》作者陆羽可说是一个讲求精神效果的代表人物,日本的茶道也属于这一类型。正是由于茶叶具有满足人们不同目的要求的特性,饮茶之风才有了它的物质的和社会的基础。
在《茶经》的写作年代,茶的种类,只有属于不“发酵”茶类的粗茶、散茶、末茶和饼茶,其中饼茶是主要的。在人民大众中,饮用前对不同的茶叶先作不同的处理(斫、熬、炀、春),然后用沸水冲泡,这就是《茶经》所说的“庵茶”;有的再加葱、姜、枣等添加物,用以调味,“煮之百沸”,然后饮用。前—种冲泡法现在还非常流行;后一种煮饮法在我国西南、西北地区以及中亚、西亚和非洲的一些国家也流行很广,仅在具体做法和饮用器具上有所不同。但陆羽把用这两种方法调制的茶汤,看作沟渠中的弃水,表明了陆羽饮茶的目的有着与众不同之处。
我国最早的饮茶方法,据《广雅》说:
“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复之,用葱、姜、桔子芼之。”
又据明慎懋官《华夷花木鸟兽珍玩考》所记:
“唐李德裕入蜀,得蒙顶,以沃(浇的意思)于汤瓶之上……”
可见用沸水冲泡或加葱、姜之类的调味品早巳为一般人所试用。
《茶经》所提倡的煮茶方法,在《五之煮》中已有详细的说明。陆羽对茶汤的“沫饽”和香味都非常珍视,而冲泡和“百沸”都不能获得“沫饽”和香味鲜爽浓强的茶汤,这就是他反对民间习惯方法的原因所在。民间着重于茶的物质效果,而陆羽则重视精神效果,这是很明显的。
《茶经》作者是主张常年饮茶的,所以他说“夏兴冬废,非饮也”,这表明他认为饮茶并不仅仅为了在夏天解渴、消热,即使在寒冷的冬天,还应照样饮茶。为什么要常年饮茶,《茶经》没有加以说明。从现在看来,由于茶内含有多种有益于人体健康的物质,所以经常饮茶,确是既能健身,又能防治疾病。有饮茶习惯的人,无论中外,也不是“夏兴冬废”的。但从全文来看,“夏兴冬废,非饮也”,是对不重视饮茶的精神作用,而偏重于饮茶的解渴作用亦即饮茶的生理作用的批评,因为从生理上说,夏天天热,需要饮茶,冬天天冷,可以少饮或不饮,但在精神生活上并无冬夏之分,常年饮茶是必要的。
《茶经》作者所提倡的饮茶方式,也与众不同。《红楼梦》“贾宝玉品茶栊翠庵”一回中所说的妙玉泡茶款待宝玉的故事,对《六之饮》中所说的饮茶方式也是一个很好的注解。妙玉讥笑宝玉说:“岂不闻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三杯便是饮驴?”曹雪芹笔下的妙玉,认为饮茶一杯已足,亦即她饮茶的着重点在于“品”,可说是领悟了《茶经》的饮茶艺术了。
《茶经》所说的“夫珍鲜馥烈者,其碗数三……”说的是煮一“则”茶末,只煮三碗,才能使茶汤“珍鲜馥烈”,如煮五碗,味就差了,所以,五个人喝茶,也只用三碗的量。在《四之器》中,煮水的熟盂,容积二升,越瓯(碗)的容积半升以下,两者大致是四与一之比,不能超过五碗是受熟盂容量限制的关系。直到现在,讲究喝乌龙茶的人,所用茶壶的大小,也随人数或盅数而定,他们先闻香,后品味,茶杯很小,饮茶的目的主要也在于精神上的享受。
《茶经》作者饮茶,特别重视茶汤的香和味(“珍鲜黪烈”),并说“嚼味嗅香,非别也”,就是说,“干看”不能鉴别茶叶品质,必须“湿看”茶汤,看汤的“沫饽”,品汤的香味。
到了宋代,在上层社会里风行“斗茶”(也称“茗战”),当时为了把最好的茶叶进献给皇室,千方百计地搜罗名茶,经过斗茶,评出“斗品”,充作官茶。斗品的要求,在蔡襄《茶录》中有详细的记述,主要是“茶色贵白”,“茶有真香”,“茶味主于甘、滑”,“点茶……着盏无水痕为绝佳”,“茶盏……宜黑盏”。当时的斗品虽也是不“发酵”的蒸压茶,但对茶汤的要求,却没有具体提到《茶经》所说的“沫饽”。
宋徽宗赵佶在《大观茶论》的序言中,曾吹嘘斗茶的风气是“盛世之清尚”。其实,斗茶不过是一种茶叶品质评比的方式,与陆羽以精神享受为目的的品茶是完全不同的。由于品茶是以精神享受为目的的,所以我国古代诗人曾写下了大量的咏茶诗句,陆羽在《七之事》中,就引述了左思的《娇女》诗和张孟阳的《登成都楼》诗。饮茶与吟诗结下了不解之缘,说明了饮茶与精神上的享受的关系。
把饮茶或品茶作为精神上的享受,虽然是历代文人所提倡的,但在我国民间也颇流行。众所周知的闽南人和广州大小茶馆中的群众,就是用欣赏品味的态度来对待饮茶的。许多地方都有吃早茶或在清早上茶馆的习惯,这都不是为了止渴、提神,同时,除少数中上级的茶馆外,也不十分讲究茶的质量,只要一壶在握或一杯在手,就感到怡然自得了。
饮茶风尚传到外国特别是传到日本以后,把煮茶、品茶发展成为一种特殊的艺术——茶道。茶道吸收了我国宋代大寺院中的行茶仪式,可以说它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产物。今天的日本茶道,已成为日本特有的文化,受到世界人民的重视。
日本的饮茶风气,在高僧荣西的倡导下,逐步地盛行起来。以后,在上层社会中,曾有一种用于交际的、相互夸比豪富的叫做“茶数寄”的茶会,这种茶会,不仅要评赏茶叶质量,还要夸耀从中国输入的茶具之类的所谓“唐物”。此外,在民间又有一种用于联谊娱乐叫做“茶寄合”的茶会。在寺院僧侣间,更普遍地利用茶会来布道传法,修禅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