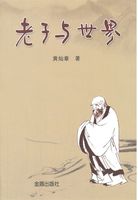周景王十八年(公元前527年)八月,穆后因太子寿的去世而抑郁成疾,不久便病逝于王后小寝之中。
同年十二月,各国诸侯纷纷派出使者,前往雒邑去参加穆后的葬礼。在宴会上,周景王以鲁国的丰富朝贡来讽刺晋国的数典忘祖。
陪荀跞(智氏族长,辅佐赵鞅执掌晋国)一同前往雒邑的晋国大夫籍谈,被周景王骂得狗血淋头,刚一回国,就对叔向发起了牢骚:“我听说,人往往容易死在自己最喜好的事情上。此话一点不假,而且很快就会在当今天子的身上应验了!”
叔向不解道:“籍父何出此言啊?”
“哼,一年之内两次遭遇丧事,丧服未除就急着与前来吊唁的使臣交杯换盏,这也就算了,身为天子,竟然当着群臣的面向诸侯索要贡品,简直就是在打着丧事的幌子敲诈勒索嘛!为自己的亲人服丧,就算是个形式,也应该走走吧?他可倒好,丧期未满就饮酒作乐,依我看,他早晚要乐极生悲!”籍谈愤愤不平道。
叔向闻言,哈哈大笑道:“籍父这是生的哪门子气?如今的王室,吃穿用度皆出自诸侯,礼乐征伐亦出自诸侯,大周天子早就成了个空架子。人家心里不痛快,骂两句娘,我们这些做臣子的应当理解。”
早在周灵王在世的时候,各诸侯国对王室的朝贡便已经大打折扣。宋国弭兵之后,小国哪头都不敢得罪,不仅要向晋国进贡,还要向楚国进贡。周天子虽然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可是并没有实力号令诸侯,因为不向天子纳贡,最多也就是在道义上有所缺失,名声上有所败坏,大不了再被天子臭骂一顿。可骂归骂,真要是动起手来,王室还真不是诸侯的对手。
周景王刚一上任,就发现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先王留下的府库中几乎空空如也。王室所辖之地方圆不足百里,每年所得的供赋更是少得可怜,宫中所有的开支用度几乎都要依靠诸侯的施舍。贵为天子,却要低三下四地向诸侯摇尾乞食,一想到这些,景王的拳头就捏得噼啪作响。
作为天子的近臣,宾起为景王出了一个主意——铸造大钱。所谓铸造大钱,就是用大面额的钱币来代替小面额的钱币。仅仅将货币面额稍作调整,就一下子生出许多钱来,这样的好事,景王自然是再欢喜不过了。
对于此事,单穆公第一个跳出来反对,他义正词严地向景王劝谏道:“大王,万万不可铸大钱,废小钱啊!此令一出,王畿之地的百姓必遭灭顶之祸!”
景王眉毛一挑,不悦道:“哼!简直是一派胡言!”
“大王,您想一想,用大钱代替小钱,这不等于是打劫百姓吗?掠夺百姓的财富来充实自己的府库,就像截流蓄水一样,可能一时丰盈,但用不了多久,水就枯了。为什么?因为水源都没了,哪里还会有水。百姓匮乏,王室早晚也会变得匮乏,王室匮乏,自然又要加重对百姓的课税。如此往复,百姓必然无力承受,到那时,局面可就不好收拾了。”单穆公据理力争,不依不饶。
景王对单穆公的话不予理睬,他已经暗下决心,要从铸造大钱开始,一步一步在王城中实施变法。
周景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24年),景王力排众议,在王畿之地强制推行大钱。
然而就在数月之后,雒邑城中的物价就翻了几番,景王倒是赚了个脑满肠肥,可百姓的日子却变得异常辛苦。一时间,怨声载道,物议沸腾。富人的积蓄大大缩水,穷人则流离失所,许多人都被迫离开雒邑,逃亡到周边的诸侯国中另谋生计。
望着日渐充盈起来的府库,景王每天都笑得合不拢嘴。直到此时,他仍未意识到,民心的散失是多少钱财也换不回来的。
周景王二十四年(公元前521年)春,在经过了多年的准备之后,景王决定在王畿之地颁布另一项新法。他特意请伯阳写了一篇题为《义经》的长文,作为法令推行的基本纲领。
为了给新法造势,景王早在三年前便将王城里的全部工匠都集中起来,准备在雒邑城南铸造一口巨大的铜钟,钟面上还要镌刻上《义经》的全文,以供天下之人瞻仰、学习。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无射钟”(无射是古代音乐十二律中的第十一律)。
无射钟属于大型乐钟的一种,由于它个头太大,所以在调定音律与音准的时候便遇到了麻烦。为此,景王亲自到乐官伶州鸠的府上登门拜访。
景王还没开口,伶州鸠便猜到了他的来意:“大王是为铸造无射大钟的事情而来的吧?”
“爱卿深居简出,想不到竟有未卜先知的能力。”景王抚掌笑道,“不瞒你说,这无射钟的音律一直定不下来,久闻爱卿精通音律,不知可有良策?”
“古代的神瞽根据律度来调和钟音,并制定出一系列相应的法则。以三为纲,平分而得六律,相间则又得十二音律,这种关于音律的分类法是合于自然之道的。”伶州鸠眼睑微合,幽幽说道。
景王迫不及待地问道:“何谓六律?”
“在古代,‘六’处于中正之位,因此将与之对应的音律称为‘黄钟’,用来颐养六气、九德,此为初律。依次往下,第二律为‘太蔟’,用来演奏钟乐,增益阳气,消除积滞;第三律为‘姑洗’,用来洗涤万物,迎宾敬神;第四律为‘蕤宾’,用来宴饮宾客,安抚众神;第五律为‘夷则’,用来歌颂万物的生长,安定民心;第六律为‘无射’,用来弘扬先贤的美德,并为百姓树立榜样。”
“何谓十二律?”
“六律之间又可分出六吕,用来斥乱宣泄,使乐声达到一种和谐的境界。其中,第一间称为‘大吕’,以增补阳气,助长万物;第二间称为‘夹钟’,以调节四时之气;第三间称为‘中吕’,以宣泄阳气;第四间称为‘林钟’,以平衡诸事的发展,使之各行其道;第五间称为‘南吕’,以辅助阳气而成事;第六间称为‘应钟’,使器用完备,以配合时序的周而复始。”
景王频频点头,并示意伶州鸠继续说下去。
“只要六律六吕这十二音律符合常规,就不会发生什么灾祸。音声高细的乐调中有钟而无镈(一种形制接近于钟的乐器,口呈弧状,器身横截面为椭圆形),这是要显示钟声的低弘;在音声低弘的乐调中有镈而无钟,更低的乐调中连镈都没有,则是要表现弦乐的悠扬。高细与低弘的音声都能得到彰显,便是乐的和谐境界。这是因为,音声和谐均平,才能持久;持久稳固,才能纯正;纯正显明,才能完善;完善复始,才能成乐。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可以使政事有成,所以先王都很重视律吕。”
景王瞥了瞥伶州鸠微合的双眼,别有用意地问了一句:“那么七律又是怎么回事呢?”
伶州鸠抚了抚案上的古琴,幽幽道:“当年,武王欲以礼乐征伐建功立业,完善教化,将岁、月、日、辰、星这五个方位与天鼋、岁星、月亮三种祥瑞结合在一起,以‘七’来协同其数,‘律’来和谐其声,人神便以七律的形式相互感应,相互交汇。”
“七律的意义分别是什么呢?”
“一天夜里,就在武王编排乐阵的时候,天上突然下起了小雨。最终,在‘夷则’律相应的时辰上排阵完毕,正好与辰星相应。其时辰星在戌位之上,所以就以‘夷则’律为主,称之为羽,用以护佑百姓的法度。在与‘黄钟’律相应的日子里,武王恰好陈兵于商郊牧野,所以称之为厉,用以激励六军。在与‘太蔟’律相应的日子里颁令于商都,弘扬文德,指斥纣王的罪状,赞颂先王的美德,所以称之为宣。返回故土后,在与‘无射’律相应的日子里,发布政令,施惠于百姓,所以称之为嬴乱,用以宽容优厚地对待百姓。”
景王对伶州鸠的回答十分满意,他马上下令,额外铸造一口“大林”之钟来为无射钟校准音律。
铸造无射钟的消息刚一传出,朝中便已是一片哗然。如今又要造什么大林钟,百官群臣对此议论纷纷。
一日早朝,单穆公以太师的身份,代表群臣向景王提出了质疑:“大王,铸造大钱,已经掏空了百姓的口袋,如今又要铸造什么无射、大林之钟,一再劳民伤财,恐怕会激起民变啊!”
“危言耸听!”景王不屑道。
“大王不要忘了,先王当年对铸造大钟可是严加限制的,从重量上来说,绝对不能超过一百二十斤,您要造的这两口钟都大大超出了这个规定。再说,钟造得越大,就越难用耳朵分辨出其音之清浊,也很难判断出音律是否和谐适中。这样的钟既无益于百姓,又无益于音声,造之又有何用呢?”单穆公直言谏道。
“先王当年夜观星象,在细雨中编列乐阵,不就是为了以礼乐来安定天下吗?我现在就是想要将这种礼乐精神发扬光大,这样做难道有什么不妥吗?”景王愤然反驳道。
“礼乐治国固然很好,可是也用不着造这么大的钟吧?音乐不就是为了让耳朵能够听见,美物不就是为了让眼睛能够看见?假如音乐听起来震耳欲聋,美物看起来眼花缭乱,臣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更糟糕的事。只有耳闻和谐之音,眼观正当之物,才能耳聪目明,德行磊落。唯有如此,一个人的思虑才能变得纯正。”在景王面前,单穆公总有讲不完的道理。
景王还没有来得及插话,便又听单穆公侃侃而谈道:“视听不和谐,百姓的心中就会失了准则,就会与大王您离心离德。到那时,政令出而无人响应,该会是多么尴尬呢?如今,您在三年之内就做了两件让百姓与您离心离德的事情,再这样下去,恐怕就要危害到社稷了。”
“哼!”景王冷哼了一声,没有接话。
于是单穆公继续说道:“口吐优美之言,耳闻和谐之音,将这些作为法令颁布于天下,百姓自然会尽心尽力地追随您。不用刻意改变什么,就能够成就一番国泰民安的伟业,这才是礼乐的至高境界啊!与之相比,钟的大小实在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
单穆公言在此而意在彼。他所关心的根本不是无射、大林之钟,而是铸钟背后所隐藏的政治动机。
景王听出了单穆公的弦外之音,他不愿与一个食古不化的臣子多费唇舌。景王十分清楚,单穆公不过只是冰山的一角,他的背后还站着一大群面目狰狞的争食者。
单穆公见景王默不作声,忙将话锋一转:“大王您再想想,钟造得这么大,倘若音律不和,岂不是适得其反?”
“爱卿说得也不无道理,容我想一想吧。”景王恨透了堂下这位手握重权的太师,但表面上,他还是装得十分客气。
退朝后,景王将伶州鸠召至身旁,并将单穆公的话原封不动地向他转述了一遍。
“爱卿觉得,太师的话可有道理?”景王满怀期待地问了一句,不料伶州鸠这一次的回答令他大失所望。
“大王恕罪,臣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乐官,您要是问臣乐律方面的事情,臣倒是还略知一二,可要是拿这些高深莫测的东西来问臣,臣恐怕就无能为力了……”伶州鸠的眼神虽然不好,可政治嗅觉却很灵敏。
“怎么?爱卿这是在明哲保身吗?”景王冷言挖苦道。
“臣不敢,只是……大王如果执意要让臣说的话,臣是觉得,太师的话的确很有道理……”伶州鸠吞吞吐吐,神色也有些唯唯诺诺。
“什么道理?说来听听。”景王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
“大王想要铸造的大钟,乐音远远高于‘无射’的音律,您不觉得这是对和谐境界的一种破坏吗?此外,铸造这样的大钟,耗费定然不小,弄不好,还会造成财货用度的紧张。声音不和谐,又斥资巨大,这样的大钟不要也罢……”
“退下吧,我累了。”伶州鸠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景王哄了出去。
周景王二十四年(公元前521年),无射钟的铸造终于大功告成。
前去查验的乐官回来报告说:“恭喜大王,大钟的声音非常和谐。”
景王闻讯后喜出望外,他一直担心大钟造成后,果真会像单穆公与伶州鸠所说的那样有损乐声的和谐,这回他总算是放下心来。
景王特意命人将伶州鸠召来,一边敲钟一边得意扬扬地讥讽道:“爱卿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吗?你听,这钟声是不是非常和谐?”
伶州鸠轻蔑一笑:“呵呵,和谐?恐怕未必吧!”
“你这是什么意思?”景王皱了皱眉头。
“大王果真是不明就里。臣以为,君王铸造乐器,要让百姓感到高兴,才称得上和谐。劳民伤财地铸造一口大钟,惹得百姓怨声载道,这哪里是什么和谐?”伶州鸠的语气中带着几分傲慢。景王虽然心里不快,却也不好发作。
“古语有云:‘众志成城,众口铄金。’自古以来,但凡是百姓都支持的事业,几乎没有不成功的;百姓都怨恨的事情,也很少有不失败的。您在三年之内做了两件不得民心的事,怕是总有一件会失败的。”伶州鸠的话讲得很不入耳,他等于是在暗示景王,“你现在就像那前朝的桀纣,民心散尽之时便是你灭亡之日”。
景王忍无可忍,当即暴跳如雷道:“你给我闭嘴!我看你是老糊涂了,竟敢在明堂之上大放厥词,滚!别让我再看到你!”
伶州鸠象征性地向景王揖了揖手,然后匆匆地退了出去。
“天子休矣!”刚一踱出宫门,伶州鸠便重浊地叹了口气。
随行的小吏忙提醒他:“这话可不能乱讲啊!”
“我可没有心思和你开玩笑,依我看,用不了多久,天子就会死于心疾。”伶州鸠的语气显得非常肯定。
“您是怎么知道的?”随从疑惑不解道。
“天子欲以礼乐教化万民,就必须要深察各地的民俗,然后再将之制作成不同风格的乐曲。与此同时,还要用合适的乐器来承载它,美好的乐声来表现它。只有较小的乐器发音并不纤细,较大的乐器发音并不粗粝,对于音乐的诠释,才能算得上是和谐之境。和谐的乐声由耳入心,内心就会喜乐安详。反之,乐声如果过于粗粝,那么内心就会惴惴不安,久而久之,必生疾病。你瞧瞧天子铸的那口大钟,发出来的声音要多粗粝有多粗粝,只怕他的心脏会不堪重负……”伶州鸠的话虽不无道理,但更多地带有一种发泄私恨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