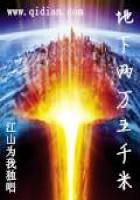“我怎么来了?问问你自己!”刘定公咬牙切齿,劈头盖脸地将那青年暴打了一顿。
“公父,你听我说……”青年头上的皮冠也被打落在地,乌黑的头发凌乱地披散于胸前。
刘定公看到麻点胖子身旁那名被人反剪双手的美丽少女,心里一下子全都明白了:“你说个屁!看我不打断你的狗腿!”
婴离搭了一位老汉的牛车,远远便望见西市里黑压压的一片人群。她忙谢了老汉,跳下牛车凑上前去。
几乎与此同时,西市外忽又突入近百匹全副重甲的黑衣骑兵。当头一骑拔剑喝道:“通通放下武器!否则,杀无赦!”
黑衣骑兵训练有素,顷刻间便已将刘府的家兵分割包围完毕。
刘定公大惊失色道:“你们都聋了吗?还不快放下武器!”
家兵们正六神无主,听到家主发话,纷纷丢下武器,束手就擒。
“哟!我当是谁,原来是太宰大人,幸会,幸会!”黑衣骑兵中拔剑喊杀的那员大将,勒马向前,在马背上冲刘定公笑了笑。
刘定公一眼认出来人,忙上前揖礼道:“老将军,别来无恙啊!”
刘定公口中所称的这位老将军,正是当年在周灵王面前预言儋括将要造反的那名虎贲卫士。他本名单愆期,又名成愆,乃单顷公之子,单靖公之弟,说起来,当朝的单献公还得叫他一声叔叔。
“哈!无恙,无恙,好得很哪!”成愆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似乎不愿与刘定公多做敷衍。
“请老将军恕罪,刘夏家中出了点小事,不敢惊动老将军。您这是要……”见成愆来者不善,刘定公立即装起了糊涂。
“哎呀,太宰大人可真会说笑。一点小事?一点小事也用得着如此兴师动众?”成愆挑了挑眉毛,“你看看,你看看,这么好的羽箭都扎在马车上,岂不是浪费了?”
刘定公的脸色青一阵白一阵,他强压着胸中的怒火,不敢发作。
“哈!太宰大人,别那么紧张嘛!老夫不过就是奉天子之命,在这城中例行巡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成愆望了望跪在地上的男子和那楚楚可怜的女子,“既然是刘府的家事,老夫也不便多问。只是……”
成愆的脸上挂着一丝阴鸷的笑容,让刘定公的脊背不禁有些发凉:“是我管教无方,是我管教无方。刘夏对天发誓,以后绝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罢了,罢了,谅谁也不敢在天子脚下造反,收!”成愆一声令下,黑衣骑兵纷纷拨转马头,扬尘而去。
见成愆的骑兵走远之后,刘定公才长长地舒了口气。他火冒三丈地指着麻点胖子的鼻子:“刘三,你过来,你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麻点胖子名叫刘三,是刘挚身边的一个陪臣。刘三哆哆嗦嗦地来到刘定公的面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老爷,我错了,我错了,不关公子的事,不关公子的事……”
“说!究竟是怎么回事?”刘定公紧握马鞭,一副要将刘三生吞活剥的样子。
“是这样……”刘三知道这次闯了大祸,便不敢再有所隐瞒。他将驭风传舍中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汇报给刘定公。刘挚披头散发地跪在一旁,恨不得马上将刘三那张口无遮拦的大嘴一箭射穿。
刘定公听罢,快步走向被缚的女子,满怀歉意地为她松开了绑绳,接着,又慌忙去搀扶那位跪在血泊中的男子:“壮士,刘夏教子无方,刚才的事多有得罪,刘夏在这里给你们赔罪了。”
男子对刘定公的赔罪显得无动于衷,他的右腿被一支锋利的长箭自膝头贯穿,殷红的鲜血仍在汩汩地流淌。
“还愣着做什么?快去请风先生!”刘定公对刘三咆哮道。
刘三失魂落魄地起身,跌跌撞撞地朝西市东头的栖凤堂奔去。
“秦佚,秦佚!”女子愤怒地推开刘定公搀扶男子的双手,泣不成声地将男子揽入怀中。
“秦佚!”婴离听到这两个字的时候,不禁周身一颤。她又望了望那个倒在女子怀中的男人,“秦佚,秦佚……难道他就是老聃哥的师弟?”
这时,人群之外传来一阵嗒嗒的马蹄声。一匹追风绝辔的棕色烈马前蹄腾空,令人眼前一亮,马上之人正是栖凤堂的掌柜风尘先生。
“风先生,您可算是来了。”一见到风尘,刘定公的心里就踏实多了。
风尘并不多言,径自来到中箭男子的身前。他从药箱中取出一把锋利的匕首和一卷包扎伤口用的麻布,接着又将一团散发着异香的药包塞入男人的口中。
“姑娘,你帮我把他扶好。”风尘对那女子吩咐道。女子见来者并无恶意,便轻轻地点了点头。
风尘熟练地用匕首削去滴血的箭镞,然后又由箭尾处将长长的箭杆缓缓地拔除。
自始至终,中箭男子都没哼一声,他的坚强,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动容……
成周街头上发生的事情,自然逃不过天子的眼睛。
光天化日之下,敢在天子的地盘上大动干戈,胆子实在是太大了!周景王在次日早朝上大发雷霆,可是他的心里一点也不生气。他现在只想着一件事情,那就是以何种方式褫夺刘氏手中所握的兵权。
伯阳也在第一时间看到了有关这次事件的详细奏报,他觉得甚是奇怪,成愆的黑骑兵平日里都驻扎在成周城外的洛水河畔,就算速度再快,也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赶到西市。除非是有人事先就做好了安排,可从奏报上看,整个事件确系偶然,并没有任何人为操纵过的痕迹。
“这一男一女又是何人?”伯阳放下手中的简牍,坐于案前闭目凝神,脑海中迅速勾连着此事的每一个片段与细节。
“不对,这个刘三有大问题!”伯阳忽然眼前一亮,立刻起身。
走到宫门外的时候,阍人忽然将他拦住:“先生,这是婴离姑娘给你带的衣服。”
“甘兄,多谢了!”伯阳抖开包袱,双手用力一挥,将那件葛袍披在身上。
王城之中,风尘骤起。漫天的黄沙,给路上的行人也镀上了一层稀薄的色彩。
再登刘府,伯阳的心中不胜感慨。还是那扇精致的漆木大门,而门后之景却早已不复当年。原本空无一物的中庭里,堆起了怪石假山,栽上了珍贵草木,正中央的那口枯井也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四角凌空的凉亭。
刘定公一见到伯阳,便亲切地拉起了他的衣袖:“聃弟,你来得正好啊。”
“怎么?刘公知道我要来?”伯阳笑道。
“聃弟如今是天子身边的红人,每日深居简出,真是难得一见啊。”话一脱口,刘定公自觉不妥,于是忙又说道,“你要是再不来,我可真要跑到宫里去找你了。”
“刘公这是在埋怨老聃吗?”伯阳笑了笑,转而正色道,“老聃这次来,是想求证一件事情。”
“哦?聃弟请进屋说话。”刘定公将伯阳请入堂中。
堂下已备好两张漆案,案旁各放着一个四脚支撑的火炉。
“去弄点肉羹,给先生暖暖身子。”刘定公支走了身旁的管家,又冲伯阳拱了拱手,“聃弟,这里只有你我二人,有什么事,但讲无妨。”
“恕老聃直言,今日冒昧来访,是为了公子刘挚的事情而来。”伯阳此话一出,刘定公立时变了脸色。
“聃弟的消息还真是灵通啊……”刘定公犹豫了一下,继续说道,“实不相瞒,愚兄近来也日日都在为此事提心吊胆。刘挚他这次算是闯下大祸了,唉!你说我怎么就生了这么个不肖子……”
“刘公不必自责,这件事恐怕是另有蹊跷。”伯阳略作迟疑。刘管家端着热气腾腾的羊肉羹,走上前来。
“哦?聃弟莫非是知道什么隐情?”刘定公眼前一亮。
“刘公府上可有一个叫刘三的人?”伯阳直奔主题。
“聃弟认识刘三?”刘定公显然有些吃惊,“刘三自幼父母双亡,从小在这府上长大,后来就做了挚儿的陪臣。不过说来也奇怪,最近几日,都没有见到这小子了。”
“那就是了。”伯阳似乎早已料定刘三会突然失踪,“刘公恐怕要大祸临头了。”
刘定公闻言一惊:“聃弟何出此言?”
伯阳不愿多做解释,而是反问道:“刘公可知成愆的那支部队是什么来历?”
刘定公眯了眯眼睛,似乎是明白了什么。
“这件事做得不错。不过……”绛紫色的纱帐后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你在这王城恐怕是待不下去了。”
“太后放心,小人已约了城外的渡船,今夜子时便泅出城去。”一个满脸麻点的胖子毕恭毕敬地立于纱帐之外。此人正是刘挚的陪臣刘三。
“哼,我看就不必了吧?”纱帐后的女人突然冷笑道。
“太后这是何意?您可不能过河拆桥啊,太后!”刘三觳觫不止,出了一身的冷汗。
“这叫什么话?若是真的想要你死,你觉得自己还能活到今天?”
“这……这……求太后饶命,求太后饶命啊!”刘三慌忙跪倒在帐前。
“哈哈哈哈……看你那点出息!去吧,你是功臣,没人会为难你,也没人敢为难你。”
刘三刚一退出门外,屋内的髹漆屏风后便走出一位黑衣男子。
黑衣男子望了望紧闭的房门:“太后不会就这么放他走了吧?”
“你说,如何才能让一个人永远保守秘密?”
黑衣男子笑了笑:“自然是让他将秘密带到坟墓里去。”
“你只说对了一点。”
“哦?太后有何高见?”
“你难道不知道吗?坟墓的位置如果选不好的话,死人也是会‘说话’的……”
当天夜里,成周城中发生了一桩离奇的命案。流经城内的洛水河岸旁,打捞起一具溺水身亡的男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