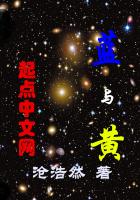我父亲的厂子是一个粮库,一个堆满麻袋的地方,有着高高的运输架,和满地金黄的玉米粒。小时候,我在厂里的幼儿园里上学。
二十几年过去了,我的小伙伴们都搬走了,他们原先都曾是我的邻居。我念念不忘这个幼儿园的原因是,那里有我至今都难忘的回忆。
我小时候是在河边长大的野孩子,别人在上学的时候,我的父母却让我玩儿了3年。到了我该上小学了的时候,他们却让我上了幼儿园。我当然不愿意和那些比我矮一个头的小小孩儿玩儿,他们连话都说不清。于是我就成了他们的大姐,被老师当做看孩子的保姆那么使唤,一直到有一次,我撺掇小孩子们午睡时间跑去粮库里玩滑梯,一个上中班的小男孩儿从传送带上滚了下来,摔断了胳膊。
我深深的记得那满地金灿灿的玉米粒儿,好看的让人想一颗颗捡进兜里,还有突然之间,将它们砸的四散的那个幼小的躯体。
老城南的河原本是一条臭臭的河,去年做了净水工程,水色变得透亮了。从上游冲下来的鱼,也在里面繁衍了。但是现在,河里的水变得很浅,泥沼露了出来,一条条搁浅的死鱼翻着银白色的肚皮,等着野猫给它们收尸。一些工人穿着胶鞋站在泥滩里,清理着灾后留下来的垃圾,我听见人们议论纷纷。
“堵起来了,前面那个闸口被树挡着水了,树还蛮多的,挤在一块儿跟小山似得。”
“那没人管管啊?”
“哪个知道啊,现在政府修大路人都不够,这些小河小道的谁有空管啊。”
“那怎么办啊,河边居民生活排污冲不走,不臭死了啊。”
“那怎么办呢,一步步来唉,臭就只能臭一阵子了唉。”
“唉……”
他们说的那个闸口是一个很窄的弯道,紧挨着一个人防工程,那个地方的水总是黑漆漆的,表面上浮着一层油,散发着让人不悦的气味。
我经过一排河边的老房子,由于水退去了,老房子的墙根都露出了层层叠叠的石砖,青黑色的,也是裹覆着一层油腻腻的污渍,有浓厚污渍的这间房后墙外面挂着一个残旧的红色灯箱,上面写着“好再来饭店”。饭店好像没有营业,因为排气管没有烟。
住在河边的,都是一些老城市人,并不是那么富有,大部分都是小生意人和低保家庭。在我7岁上幼儿园那年,我家就从河边搬走了,不过也没好到哪边去,搬到了铁路边上。我曾问过我的父母,为什么我那么晚才上幼儿园,他们是这么解释的,他们说我小时候得了一种慢性疾病,会传染,花了3年的时间才调理好身体,我问他们什么病,他们说是肺结核,后来,吃了一个老中医的药方子,就渐渐痊愈了。
我想我身体虚弱是有原因的。
我个子不高,瘦瘦小小的。一旦运动量大起来,就脸色发白。现在我气喘吁吁的爬过了一个大树坑,终于走到了粮库的正门前,眼前的情景,着实把我惊呆了。
麦浪你一定见过,那方方正正的,像抹茶蛋糕似的切的平整的大地,绿油油的让人心醉。但你一定没见过废墟上的麦浪。我猜一定是水的冲击和厂棚的坍塌,让数以万计的麻袋像多米勒骨牌一样从高处坠落,摔得遍地都是,堆叠成连绵不绝的山丘群。很多麻袋破碎了,腐烂了,种子撒了一地。有些种子精加工过,没了生命力,便沤在一起发霉发臭。另一些种子是完整的,便趁着这几天天气晴好,破壳而出,从细密的麻袋缝隙里冒出绿油油的嫩芽儿来。那些没能重生的种子,便成它们的肥料。
实在是太壮观了,我面前绵延着数百米低矮的绿色麦田,一直汇集到了河的那端去,有不少种子应该随着树群飘到逐岛去了吧。。
正当我看的发呆的时候,从我身边走上来一个男人,捧着一只专业单反相机,记录了这个场景。他一头阳气的卷发,还带了个发箍,像是个搞艺术的家伙。
“太美了。”
咔嚓,他取完一张景,沉醉的叹道。
“我可以看看你拍的照片吗?”
我走到他身边,腼腆的问他。
“可以,可以。”
他按下目录,让我看他拍的照片。
“你的角度很巧妙,避开了那些坍塌的厂棚,让这里像个大草原似的。”
我指着他相机的显示屏说。
“嗯,厂棚有什么好拍的。”
“我还以为你是个记者什么的呢。”
“我只是摄影爱好者。”
他对我笑,很难得,灾难以后,我很少再见人们的笑容了。但他的笑很诡异,让我浑身不自在。
“真是太美了,我的杰作!”
我知道我的不舒服来自哪里了,这个人没有对灾难展现出一丝悲悯,反倒是一直沉浸在自己狭隘的美学世界里乐不可支,接着,他又说了让我反感的话。
“我拍的这个系列一定能拿今年的普利策新闻摄影奖,也多亏老天给的这个机会!”
他的眼里闪烁着地狱的欲火,我望着他痴迷的神情,觉得此人不宜久处。
“给你看我拍的这个天赐系列。”
他兴奋的点开目录小图,一张张的向我展示他的作品。我惊讶的发现,这些作品都来自于这次灾难的细节或者部分,均以一种极具表现力的构图撑开了整幅画面,有一种勾魂摄魄的美感,然而这种美喷着带焰的卷舌,渴望着把人吞下去,让人坠入撕裂的地狱。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张细节照,画面里,斜穿过一只青色的手,右上角向下滚洒下来的泥浆,和左下角喷溅上去的鲜红血液形成了鲜明强烈的对比,像是一根微弱的生命和自然做的最后的抗争,然而泥浆的比例是大于血液的,生命的渺小显然无疑。
“这是?!”
我看见照片里的人手中指上带着一个戒指,并清清楚楚的看到了这个戒指的模样,歪歪扭扭的造型,并不细致的流星,粗细不一的戒圈,这!是我亲手做的戒指!
我送给前男友的戒指!
“你哪儿拍的这张照片?!”
我急红了眼,揪起这个人的衣领质问道。
“怎么了,一个坑里啊。”
“我说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这个人是死是活?!”
“今天早上。。在西街,西街。。我不知道,我只看见半个手臂。。只看见。。半个手臂。。”
西街,是报导中这次难情最严重的地方,因为那里不仅保存着古老复杂的下水道系统,还建立了城市中最大型的中央立交枢纽,报道中,中央立交枢纽的由于一根桩的塌陷导致了近3公里的立交桩不同程度倾斜,难以承受原设计载荷,城市交通系统被扼住了空中的喉管。
我飞也似的离开了这片崎岖的麦田,一边拨着前男友佳贤的手机号,一边向西街奔去。手机没有通,也不知前方路如何。可是,我心里有个迫切的念头,一定,一定要见到他,因为他依然带着我送他的戒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