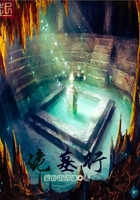念念不忘,终于得到丰盛的回报。范心松满心欢喜,离开华升宾馆开着奔驰回到别墅,亲手洗了一遍瓷具,颇有兴致的煮了一杯苦咖啡。
目的达到了,过程就显得尤其重要尽管满腹的遗憾,这有了开头,他从心里笑了起来。
品着咖啡,范心松直接给石金喜挂了电话:认赔50万。完了,范老板突感内急,慌忙蹿进卫生间却怎么也解不出来,灼热的尿痛急出他一身冷汗,腹胀腹痛交杂着惊慌,诚惶诚恐地冲进医院。
医生给他检查,女护士在一边抿着嘴的笑,医生也是一脸的情趣只是多有克制。
范心松逐渐平静下来,混浊的尿液带着一股恶臭从导管排出,他淡淡地忍着,心里压抑着已经爆发的火焰。
范心松不是个怕事的人,在南山修房子就是为了搞女人。他老婆展媚女士在地产界也是有头有脸的,容忍的极限被撑破,儿子和女儿又在国外,万般无奈抉择了分居。而范老板也是个知情识趣的人,不时有大笔现金转到展女士手里。没人懂得范心松的逍遥是出了钱的。
范心松抓了大把的药,拖着伤痛爬进奔驰,给枭雄打了个电话,叫他带人回家。然后又接通江小心叫他带俩人到团结路华升宾馆,查一查昨夜出入106房有没有****的女人。恼羞成怒的范心松,难以遏制的产生了嗜血的冲动。
郭晶莹和高三相约在绿山。
高三戴了一顶黑色的遮阳帽,一套黑色的休闲装摆式出少有的低调。郭晶莹同样一套黑色,及腰的直发被她扎成长辨。
“事妥了。石总的意思,今天就走。”
“我还有些事。”
“得有个说法。”
“我妈病了。”
“你不是还有个远嫁他乡的妹妹,扯她时间不是更长。”
“哦,是啊——”
郭晶莹好笑地笑了起来,摆弄着脉络分明的梧桐树叶,“石总放心不下三哥。”
“也是——”
“也是?”晶莹伸手摘下他的遮阳帽,光头光光的耀眼的亮。
“昨天找丁秀梅给人打了,被一个叫仁刀王的人给救了。你听这名:刀王!怎么还有人叫这名?刀刀枪枪的你怎么啦?”
“头疼。”郭晶莹还了他的遮阳帽,捏着树叶的手捂住脸,“一会就好。听说西南水库的鱼很有灵性。我们租辆车,约上丁秀梅一起去转转。”
孩童的惊喜往往源自心智欠缺,高三的欣喜源于晶莹知根知低的关照。
关照经过积垒,会产生储蓄效应,一旦遭遇提取,那可件要命的事。范心松每天都会料理他的关照,看着江小心押着俩个女人上了微型车。
文静的江小心身体修长细瘦,总是穿着得体的西服,系一条尽色领带,文质彬彬细皮嫩肉透着儒雅,说话的声音极轻极柔透着较好的涵养,女性不仅倾心于他的文静,更怜惜他的柔弱,大概是母系天生的秉性。
“大兄弟,”
江小心甩手一个耳光抽了上去,往往是在遭受侮辱的时候****的女人才会清醒麻木了很久的东西,倒是另外的那个****女满不在乎地张开大腿根释放她的宝贝,异样的气味令人窒息。江小心耸立起精刀细刻的嘴脸,吓得女子赶紧收缩。
不一刻,范心松接到电话,听了一会,他说:“给她们钱,让她们把病治好。”然后又说:“枭雄在回家的路上。心啊,我们有事做了。”
一个小时之后,范心松的奔驰车驶上了通往省城的高速公路。在车上范老板接到一条短信:刘壳又顶上了你。范心松点了支烟,看了一下腕表,加快了车速。对郭晶莹的动作,必须得到石金喜的同意。至于那条短信,知道了也就行了。
下午,郭晶莹,高三,丁秀梅一行三人进入西南水库坝区。都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坏男人的特点就是能迎合女人,为了那点事可谓耗尽心机。高三整个思想都围绕着丁秀梅结实的身体,大献殷勤,而丁秀梅早已神志恍惚目流惺盼。
没见过这种女人,一旦牵手钻进树林,后果就是没有结果的结果!晶莹正寻思着怎样分开狼与狈的胶着,稍微分神,俩人已经进了树林!
“一对狗男女。”郭晶莹靠到树上,知道了已经晚了。企图借光头的豁达,达到她和刀王产生交谈的目的,没想到计划外的变化,天意弄人!一抬头,看见了他。
一愣之后,面对突然的邂逅,愕然之余,主动而来的晶莹采取了主动,“如果你会想我,那么我不想活得这么累。”
“你不欠我。”
“我爱你。”
“今生无缘。”
“那么来生哪?”
刀王吼了起来,“我不能再愧对月牙!”
死吧!死——他是怀着满腹的愧疚,对自己的诅咒,晶莹虚脱地缩成一团,涕泣不止。
幸福是多样的,幸福是一种感受。
此时,还有一个人在经受不一样的幸福,猪仔三接到靠山歌舞厅张从止的电话。
猪仔三抑制着狂乱的心跳,仿佛看到了仁刀王的惊讶:30万往他头上砸,何等荣耀!
面对杀头的买卖,猪仔三用的是新买的联通电话卡,还想到:张从止,上百万的东西只要他30万,巨大的利润足以使他慎之又慎。还想,想得最多的还是刀王的惊讶。
猪仔三挎上包,跳上偏三轮,想着30万象一座小山堆着等待他去搬动。想一想,热血澎湃。不一会到了靠山歌舞厅的门口,倏感内急,调转车头夹着尿去了一家餐厅找方便。
到人家的地盘上拿钱撒尿有失检点,猪仔三这样想着,出了洗手间,手机响了,莫不是张从止反悔?猪仔三接了电话。
“三,快逃。”
猪仔三的神经扯成了一条直线,控制着心跳,装模作样的上了偏三轮,跑了。
怎么也想不起来,除了仁刀王还会有谁这么叫他,还说了什么?越想越多,越想越糊涂,这时手机又响了,他随手把电话丢进稻田。惊出的一身冷汗,这时才感到了冷,看着破烂的偏三轮,家是不能回了。从未感受过的孤独渗透了他的身心,使他莫名其妙的张皇起来,这时的仁刀王是他唯一的依赖。
天渐渐的黑了。
水库被一片雾气笼罩,黑黑的山体勾勒出天空的轮廓,蝙蝠飞出漆黑的洞穴熟练得煽动宽大的飞翼,尽情捕捉慢舞招摇的蚊虫,无语的星星在遥远的天空游戏着点滴的光亮,柔弱的月亮还在山后渲染着神秘。
仁刀王情绪淡雅,这是郭晶莹给他的清爽,有一种甜甜的却又不能明状的东西包裹着他,周围的一切都变得十分安逸。他倾听着鱼在水库里翻滚的水浪,无心有意的想听出丝丝征兆。
猪仔三来到了他的身边,俩人抱在了一起。
“没事了,没事。”
“我对我自己很失望。”
仁刀王笑了起来,“我第一次被抓也是。人都这样,往往死都不怕却怕有烟没火。”
猪仔三想起了抽烟。
“给你打电话的是刘壳。”仁刀王又说:“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刘壳就在我身边。”
“你对他都说了什么?”
“还能不说什么?”
猪仔三不知是喜是忧叹了口气,沿着刀王的示意,回头看去,黑色里走出身影,“三,不想拥抱吗?”
水库里的鱼翻腾起来,有一种迫切,自然似乎在点化着什么规律,有一种冲动在空气里漫延。
一整天,范心松蚁食未进。
石金喜火气冲冲连夜从邻县赶了回来,“什么事?我的天!风忙火急的要死人吗?”
范心松只是可怜巴巴一付死样地看着他。
石金喜松了口气,“家里被雷打了?还是被火烧了?”
范心松依然一付要死的嘴脸,石金喜很少抽烟地点了一支。
范心松从兜里抓出一把药,一颗一颗往嘴里丢着嚼,药粉干燥的苦涩扯动脸腮没规律的悸动,石金喜动了恻隐,起身给他倒了杯水,“有什么话,你说。”
他说,范心松说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尽管是单相思爱得也是深沉。他说,他说这个女人叫郭晶莹,一边嚼着药一边说,范心松从头到尾都说了。
听完,石金喜没有说话,长时间沉默。
范心松跳了起来,石金喜阻止了他,“可不可以抹去一段记忆?也就是说那批货,晶莹也没去过通市。”
“石总,我在吃药。”
“看见了,让人恶心。”
范心松继续示弱,象一条癞皮狗,他要买下郭晶莹这条命。石金喜很轻松地笑了笑说:“我得到一条消息,很荣幸你老弟又被刘壳盯上了,为你做点什么我是可以的。”石总又补了一句:“不要给脸不要脸。”
“就是一个女人。”
“我的天!一个女人。“
“就是一个女人。”
“说够了吗?”
“应该是没完没了。”
“确定?”
“确定。”
石金喜松了口气,“好吧,80万。只是刘壳又在折腾。”
范心松想笑,又没笑出来,“据我所知,刘壳在找姜长毛,几乎没人知道高三就是姜长毛。”
“死了的汤堂有没有东西在高三手里?”
“高三是一个装得下东西的人吗?您多想了。”
“假设,假设,”石金喜突然不想说了,“还是多留心刘壳。”
范心松站了起来,感到很饿得做了个肢体语言,说了一句:“这里面有你的事。”
石金喜张口想骂,停了停,用手指点了他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