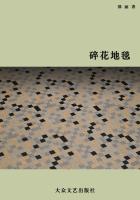颜颇挡住二人,说:“不能逃!咱们不逃,事情尚有回旋余地。回纥若是发现咱们逃走,岂不要恼羞成怒?万一激怒回纥发兵犯境,咱们可就是千古罪人了!”
玎零收回匕首,一双美目盯着颜颇,柔声笑道:“好啊,我就陪哥哥一块儿死。咱们比翼双飞,我可喜欢极了。”
司徒央颤声说:“嗨,你们比翼双飞,奈何桥上正好一对,大叔我可是孤零零一个哟。”
颜颇哭笑不得,忙道:“你们都说些什么?咱们生死事小,要紧的是决不能让登里可汗发兵!”
玎零走到锦榻边,看着昏迷不醒的可敦仆固琪,小声说:“除非她苏醒,我可想不出招儿阻止回纥发兵。哥哥,你聪明绝顶,一定有两全其美的法子吧?”
颜颇摇摇头,无可奈何地盯着仆固琪,暗暗惦量当前的危急局面。
仆固怀恩拥兵灵武,已说动吐番、吐谷浑、羌等戎狄部落出兵攻打中国,只碍着回纥尚未答应出手,自觉无必胜把握,是以才延缓下来。
自打突厥衰落,回纥雄据在中国西北,南至阴山,北至冰海,西至金山,东至俱伦泊,疆域纵横万里,国势十分强盛,远非吐番、吐谷浑等部族可比。
回纥精兵近百万,铁骑驰骋大漠,威名令人闻之丧胆。中国历经七年安史之乱,国力兵力耗费过甚,正是虚弱之时,对付吐番尚不足虑,如若回纥参战,那却危乎殆矣!
仆固怀恩力促登里参战,许以半壁中华江山。回纥久居苦寒绝域,自然为此动心,因此不少酋长和药葛罗都督都主张出兵。唐天子深知其中厉害,自去年仆固怀恩反后,不断派使者慰抚登里,赐赏金帛无数。登里可汗碍着“信义”二字,一直举棋不定。
在这种情形之下,登里可敦突遭暗算,实在于中国大大不妙。无力救她却又要稳住登里,谈何容易!颜颇三人计较一会,均觉无计可施。
帐外回纥们等候得心焦,渐渐吵嚷起来。喧哗声不断涌进帐中,更使人心慌意乱。
颜颇抱头苦思,彷徨无计。司徒央焦急地踱来踱去,嘴里唧唧咕咕把天下神仙一个个拈来祷告,玎零说:“大叔你消停些吧,骆驼似的走来走去,晃得人眼花!”
司徒央立住脚步刚欲跟玎零斗嘴,颜颇忽道:“咦,外头怎么不吵了?”
果然帐外沸腾的人声沉寂下来,安静得有些奇怪。
司徒央大喜:“好哇,回纥们都走了,咱们也走!”
颜颇从帘缝里向外张望,又惊奇地“咦”了声。玎零忙凑近帐门,一瞅之下不由大奇——回纥武士全都在,鸦雀无声围成半圈,瞧着可敦锦帐门前的丑书生陆羽发呆。
只见陆羽面色沉静,盘腿端坐在锦帐门外,身边摆着与他形影不离的茶器都篮。
他面前的鼎型风炉中炭火通红,方耳宽边的大口浅底壶坐在风炉上,热气蒸腾,茶水欲沸未沸;风炉旁依序摆着盛炭的竹筥、碾茶的桔木圆碾、筛茶的纱罗盒、岳瓷青茶碗;椆木水方满盛清泉,鹾簋中尚余半皿盐末;小竹架上黄铜荚、葫芦杓、漉水绢囊摆放井井有条。整套茶具古朴盎然,十分典雅,与清标蕴藉的中华处士相得益彰。
帐内是昏迷不醒的可敦,帐外是虎视眈眈的回纥武士,陆羽端坐炉前,把烹茶手段一一做来,虔诚而镇定,恍如不觉身旁箭拔弩张的情势。
回纥武士们被这位丑书生的从容风度震慑,瞪目看着他烤茶饼,碾茶末,轻摇罗筛,频添精炭;静观壶底水珠晶莹升起,水面微波荡漾……陆羽此时此刻烹茶于此,当真匪夷所思!
颜颇知道茶圣此番演习茶道,必定别有深意!他定睛把陆羽瞧了片刻,暗想:“处士分明是在提醒我,要沉心涤躁,处变休惊,勿以外界风云陡乱神智。颜颇呀颜颇,你怎样才学得处士的风采呢?”
定一定神,惶急之态尽皆退了,默然思想有顷,大眼闪出光彩。
玎零问:“你在想什么?”
颜颇道:“处士烹茶,武士们竟被他震慑住,我猜回纥不兴茶道,定以为处士烹制的是救人神药!咱们何不利用这个法子……”
司徒央忙道:“陆处士说天下茶以蒙顶雷鸣茶为第一,我叫登里可汗去摘些雷鸣茶来制神药,不就能稳住回纥了吗?”
玎零摇头说:“回纥的马好,去蒙顶山要不了多少功夫,咱们再难他一难吧。西域有种七彩锦蛇,额头上顶着一只蛇角,听说奇毒无比……”
司徒央忙插嘴:“知道知道!以雄黄十斤熏那锦蛇,把它熏晕了,锯下它的角,最是解毒的好东西,咱们就要这个!”
玎零又说:“南海有种巨鳖,鳖肚里有四五寸长小人儿,叫鳖宝,能驱百毒,又能避邪。把鳖宝藏在活人臂肉中,这人可以瞧见地底下百丈深的宝物。咱们要登里找几只鳖宝来,岂不是妙?不过那东西靠吸人血才能活命,人血吸尽,它立刻就死,怪没意思!”
司徒央不肯输给她,急忙又想出一物,说道:“鳖宝不算稀罕,闽西有种蟾蜍,背上三条金线,其鸣如狗,当地人称作犬煞蛤蟆,最是剧毒……”
一语未完,忽听颜颇轻喝:“快看!”
司徒央急忙住嘴,和玎零一起从帐门缝隙探视外面情形。
此时壶中水开始沸腾,陆羽投下茶珠,清醇的茶香顿时弥漫开来。回纥人不知不觉向丑书生走近,聚成紧紧的人圈,贪婪地嗅着这种幽雅香气。
陆羽取三只青瓷碗,摆成“品”字形状,将茶汤均匀分作三碗。司徒央咂咂嘴巴,小声嘀咕:“好香呀,不知哪位有幸能吃茶圣的这三碗神仙汤?”
只见陆羽端起“品”字头上那一碗,微笑着递向登里可汗。登里可汗双手接过,两眼狐疑地看着丑书生。
陆羽端起第二碗茶汤,微微低头嗅着香气。蓝天白云映照着青碗黄茶,波光闪闪反射在他的脸上,他欣喜地陶醉其中,智慧之光令相貌的丑陋淡然隐退。
登里可汗见了丑书生怡然之色,试探着也将茶碗端到鼻下,深深地嗅着。香气缭绕而起,渐渐抹平可汗紧皱的眉头。接着他的脸色悄然发生变化,变得平静起来。
陆羽举碗浅饮一口,细细品尝。可汗迟疑一下,也举碗喝了一口。清纯香冽的茶汁是这位回纥可汗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他惊喜地赞美一声,不再犹豫,学着陆羽一口一口品尝。
陆羽对可汗微微一笑,端起最后一碗茶。
众多回纥人眼见这丑书生隆而重之烹出三碗香汁,可汗饮之神清气爽,心里都料着香汁定有神奇之处,大家不由自主往前挤了两步,眼巴巴盯着那只青瓷碗。
可敦的锦帐里,颜颇三人也睁大眼睛,看陆羽如何处置这碗“神水”。
忽听陆羽叫道:“赛神仙法师!”
司徒央一愣,以为自己听错了。颜颇忙推他一把,道:“大叔快去!”
司徒央被颜颇推出帐篷,惶恐不知所措,心里胡乱想:“哎哟,人家的王后还没救醒呢,我哪有资格吃茶?不如给那少年都督浇浇心头怒火……”
陆羽高声说道:“神农尝百草,茶水最神奇!法师请把这碗解毒清神的茶送给可敦饮用吧。”
司徒央恍然大悟,心想:“不错,茶叶确有解毒提神的功效,医书上都写着哩!”急忙接过茶碗,返身钻进帐篷,命玎零扶起仆固琪。
半碗温热的茶汁入肚,仆固琪微微动弹起来。三人屏声敛息紧盯着,只见她胸口缓缓起伏,忽然“嘤”地一声,吐出一口气息!
三人又惊又喜,玎零急叫:“九爷醒醒!”
仆固琪宛如大梦初醒,睁眼迷糊片刻,轻声唤:“公孙姐姐……”
颜颇暗忖:“玎零没猜错,点她穴位的果然是公孙玉娘!奇怪,玉娘深明大义,怎会有这种乖张之举?”
玎零笑吟吟埋怨说:“好九爷,你可真会吓唬人哪!你跟玉娘姐打架了?嗨,她是顶尖儿的剑侠,你跟她打架,自然打不过。”
仆固琪又朦胧一会,方浮出一丝倦笑,低低说道:“我中了汉使暗算,玉娘姐怕我伤动胎气,封穴让我静睡七日……你怎么来了?身后是谁呀?”
颜颇从玎零身后转出,含笑向仆固琪抱拳施礼。他听了仆固琪刚才这几句解释,心头疑惑已然冰消。仆固琪见是颜颇,十分欢喜,刚想开口招呼,忽然想起刚才自己说那“胎气”的话,不觉羞红了脸,抿嘴一笑。
司徒央见仆固琪醒转,大喜欲狂,顾不上跟她寒暄,奔出帐外宣告:“可敦饮了茶圣的茶汤,已经苏醒啦!”
登里可汗大喜,向陆羽深施一礼,激动地说了两句,药葛罗连忙译成汉话:“可汗说,茶圣的大恩大德,回纥人没齿不忘!”
丑书生陆羽抱拳一揖,爽朗地说道:“中华茶道神奇无比,陆鸿渐愿与回纥兄弟共饮神茶,共享太平!”
话刚落音,人群一片欢声雷动……
可敦安然苏醒,陆羽成了回纥可汗的尊贵客人,发兵攻打大唐的事儿自然作罢。仆固名臣悻悻离开草原,回灵州去向仆固怀恩交差。
九爷十爷姐妹重逢,无限欢喜。登里可汗担心仆固琪听到母亲惨死的消息伤心,吩咐众人都瞒着她。仆固琳毕竟孩子天性,见不许说伤心的事儿,便迷上了打猎,成日跟着药葛罗骑马飞奔,没个安静的时候。
这日仆固琳放马来到一片草甸,嫩绿无涯,花红蝶舞,景色十分迷人。她骑术虽精,箭术却不怎地,撵着黄羊跑来跑去,一袋子箭射光,好不容易才射中一只。
黄羊负箭奔逃,仆固琳紧追不舍,直追到草甸边,眼见黄羊朝个小山包直冲而上,仆固琳笑骂:“蠢东西。”心知黄羊负伤竟往山顶奔逃,一定是吓糊涂了,坚持不了多久。
果然那蠢东西刚及山顶,趔趄几步,骨碌碌滚下山包另一边。
仆固琳欢呼一声,打马绕过山包,却见有个陌生男子已抓住了那只黄羊。
草原打猎见者有份,这规矩仆固琳知道。不过小十爷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打着一只,正要拿去向药葛罗炫耀,若是分一半给这人,药葛罗准以为是别人帮忙打的,那多没趣?
小十爷回头望望,幸好药葛罗没追过来。她打定主意,嚷道:“喂!那是我打的黄羊,快快还我!”
陌生人提着黄羊,两眼瞅着小十爷,脸上似笑非笑,慢呑呑地说:“这是我养的黄羊,怎么是你打的?”
说罢松手放开黄羊,那黄羊果然乖乖地站在他脚旁不走。伸了嘴低头啃草。
仆固琳四下瞅瞅,哪里也不见第二只黄羊。她心里疑惑,低头望去,嘿,吃草的黄羊屁股上还带着自己的箭杆!
她叫道:“好哇,明明是我打的,你白赖!”催马上前,伸手去夺那黄羊。
陌生人笑道:“是我养的,不信你瞧。”挥手向前一指,喝道:“笨东西,快跑。”黄羊昂头嗖地跑向前去,小爷恰好抓了空。
黄羊跑出数丈,陌生人手臂向东挥挥,大声说:“向东跑五丈。”黄羊毫不迟疑,跳起来,折头东奔。陌生人挥手又道:“行啦,向西吧。”黄羊掉头果然又向西跑,像是家养的黄狗一般。不过狗儿养得再熟,也决无这般懂话驯顺的。
小十爷瞧得发呆,暗想:“啊哈,原来黄羊这么聪明!明儿我也捉几只养了,叫它们操练排阵。”
转念又想:“黄羊极难活捉的,就是捉了,谁知怎样驯训?不如干脆把这只乖乖的黄羊先抢回去,跟它玩几天再说!”
她一踢马肚,兜头迎向那只“乖乖”的黄羊。陌生人慌着问:“小丫头,你干什么?”
仆固琳哈哈大笑:“抓它回去!”
陌生人道:“它是我的,不能抓。”
仆固琳打马直冲,边叫道:“草原上的黄羊都是我姐夫的,我爱抓就抓,你管不着!”
陌生人顿了一顿,忽然惊呼:“哎哟,怎么你骑着我的马?”
仆固琳一怔:“你胡说!这是药葛罗送我的马。”
陌生人笑道:“你又不信?瞧着。”嘴里叫一声:“往东。”那坐骑急忙扭头往东狂奔。只听陌生人又叫:“往西!”
坐骑陡地抬起前腿,立起来发出一阵长嘶,翻转身往西奔去。仆固琳连连呵斥,只是喝它不住,不由心头又疑又惧,大骂:“该死的药葛罗!居然偷别人的马送我?”
忽听马蹄疾响,药葛罗飞奔而来,怒喝:“呔!你是何人?竟敢弹石惊马欺负人,混蛋!”
恰在此时,仆固琳耳旁掠过一声锐响,坐骑受惊一跳,扭头向南急驰。
小丫头顿时恍然大悟——那人原来是利用弹出的石子控制骏马!暗想这人当真了不得,扔个石子竟能把黄羊和骏马弄得晕头转向。假若人人都会这一手,世上还要弓箭和马鞭何用?打猎放马只须揣一袋石子儿,那就够啦。
这么一想,她立刻打马奔回,佩服地打量那陌生人,只见他穿一身汉人服装,高高的个子,细长眼睛,脸上虽然带笑,眼光却显得十分冷峻。
小十爷惊奇地“咦”了一声,觉得以前似乎见过这人,却想不起他是谁。
回纥人素性刚猛强悍,药葛罗更是其中佼佼者,他认定这汉人欺负小十爷,大喝一声策马上前,冲着那人一鞭抽下。
蓦觉鞭梢一紧,已被陌生人抓住。药葛罗使劲连扯几下,竟带不动分毫,不由大惊且怒,喝道:“什么人敢来大漠撒野?本都督今日要教训教训你!”
他扔了马鞭,拔出钢刀,刀在阳光下发出万点寒光,宛如流星飞迸。陌生人失声叫道:“高昌宝刀!”
药葛罗得意洋洋,大喝道:“你既认得宝刀,还不快来受死?!”挥刀连出数招,把陌生人逼退几步。
陌生人眼瞅宝刀冷冷说道:“你叶护大哥就是死在这把刀下,原来登里可汗把它送给了你?”
药葛罗眉尖急竖,狐疑地问:“你怎么知道这事?”陌生人冷笑笑,不屑答话,掉头就走。
药葛罗哪肯放过?两腿一夹,胯下马哒哒疾冲,兜头拦住陌生人去路。他厉声喝道:“我大哥被人暗害,你怎么知道得如此清楚?哼,我瞧你鬼鬼祟祟,不像好人!”
陌生人冷笑道:“好刁蛮的小子。”
他带笑说出这话,谁知一语未尽,药葛罗怒骂一声,手中刀已当头劈下!陌生人偏头避过,第二招又挟风横扫过来。回纥刀法本来精妙,药葛罗这两刀更是迅捷异常,瞬息要人性命。陌生人纵身高跃,让过刀锋。
药葛罗见他轻易躲过自己最得意的两招,不禁大怒,奋起神威,把手中宝刀舞得雪光一片,顷刻之间连施杀手,满心要当场劈了这大胆的汉人。
陌生人低喝:“小子找死。”忽地拔身而起,凌空掠过马头,快如闪电抓住药葛罗后颈,把他扯离马鞍掼倒在地。药葛罗连挣几下,竟挣扎不起,眼见那陌生汉人脸色冷如寒冰,伸出一只巴掌,便要当头拍下!
仆固琳见了他的身手,触动记忆,失声大叫:“想起来了——我在成都见过你!”
陌生人的巴掌停在半空,瞅着小十爷微微一笑。仆固琳噘嘴埋怨说:“好哇,你干吗白赖我的黄羊?亏你还是玎零的大哥呢!”
范无心松开药葛罗,问:“听说玎零陪你来了大漠,她在哪儿?”
仆固琳没来得及回答,忽听远处一声清啸,茫茫草原一骑奔来。鞍上人笑问:“师兄又在找顽皮小妹么?”
范无心脸上忽地泛出笑容,扬声应道:“玉娘,怎么今日才来?”
玉娘笑道:“骨利干部落没在独乐河,我寻到娑陵水南岸才找着,所以耽误些时日,让师兄久候。”
范无心迎上两步,说道:“玉娘,你辛苦了。”
这一声问候,实在温和无比,一直笼罩在他周身的那团冷气刹那间消融殆尽,长脸焕发出柔和光彩。
药葛罗在草原上威风八面,没承想今日输得莫名其妙。他悻悻地爬起,欲待跟范无心再打一架,人家已经把他忘了,在那里谈笑风生;就这么溜走吧,那可太丢了面子!他一时不知所措,十分尴尬。
范无心瞅见他的神色,抬手一揖,说道:“刚才逗小十爷玩儿,冒犯了都督,范无心这里赔礼了。”
仆固琳悄悄劝药葛罗:“范大哥是中原最厉害的剑侠,他肯向你赔礼,你就饶了他吧。再说,玎零不是咱们的好朋友吗?”
药葛罗忙向范无心回了一礼,道:“久闻范侠大名,今日得见,神技果然非同凡响!药葛罗欲拜范侠为师,不知范侠肯不肯收我这个笨徒?”
范无心哈哈大笑,道:“合胡禄都督威镇大漠,谁敢当你的师父?咱们不如义结金兰,做一对纵横天下的好兄弟!”
药葛罗大喜,等不及备香案美酒,就在山丘前撮土为香,与范无心八拜结义。
礼毕两位兄弟握手大笑,俱觉踌躇满志。药葛罗将义兄邀至大帐,下令杀牛宰羊排开宴席,回纥武士们开怀畅饮,在席前各显绝技,与汉人剑侠切磋武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