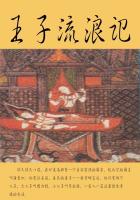这时,只见她将烟蒂放在地上,用脚轻轻踩灭,然后拾起来,转身走到垃圾桶旁扔了进去。我和朋友默默地看着眼前的一幕,她那一连串的动作是如此的娴熟,丝毫没有做作之感,完全是长期养成的一种习惯性行为。我低头看看脚下的挺多的烟蒂想:她可以不用把烟头扔进垃圾桶,因为她在踩灭烟头的时候肯定也看见了地上的烟蒂。但那位女郎似乎根本不受这些烟头的影响。紧接着另外几个人也吸完了烟,都是同样的动作,踩灭了烟蒂,再扔进垃圾桶。
我突然被这小小的生活细节袭击得不知所措,再次看看脚下被人遗弃的烟蒂,感慨万分。垃圾桶就在旁边,抽烟的主人难道不能把它送到属于它的地方?扪心自问,我们抽烟的人中有几位能做到先踩灭了烟蒂,再扔?即使有,又有几人呢?经常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放肆地扔自己的烟蒂,根本没有踩灭的意识。
外国人把烟蒂踩灭了,再扔进垃圾桶,除了因为清洁外,还不想将桶中的纸屑引着,预防带来没必要的麻烦和环境污染。而我们在乱扔烟蒂而引起火灾,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的众多教训中,仍不见抽烟人注意这一点。有人认为,那些灾难不是他们带来的,也不会带给他们任何损失。
抽烟的朋友们,让我们从今天做起,把烟蒂踩灭了,再扔!
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劳一分才。
人蚊之战
我应该怎样表达对蚊子的心情呢?恨、惧、烦、怒……好像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好感。
生我养我的故乡,只是吝啬的让我了解到蚊子仅是昆虫而已,并未给我和它真枪实弹交锋的机会和缘分。来北京之前,有人意味深长地说,北京的蚊子很厉害,我不以为然地嬉笑:“难道我能怕蚊子?”
北京的夏天很热,这或许更强壮了蚊子的生命力。夜晚,将门窗大开,欢迎凉风的涉足,可养精蓄锐的、逍遥的蚊子,动作轻盈、飘逸地开始“第三者”插足。灯亮时,蚊子按兵不动,隐蔽在安全的地方觊觎房中的猎物,只要灯一灭,它们便对我开始了穷凶极恶的围攻。
第一次品尝蚊子的“初吻”,那个刺痒,那个生疼,真是受“益”匪浅。我满头雾水地打开灯,只见露在被单外的双腿上凹凸不平,越看越痒,抓呀,挠呀,可痒到心里的那份罪何时挥去?让人如人茫茫苦海没有尽头,原本光洁如玉的皮肤被点缀得朵朵红晕,在我的莹莹泪光中折射出粉红的花瓣。
蚊子,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根深蒂固的烙印。
领教了蚊子的魅力后,我感到委屈。在什么防范措施都没有的情况下,遭到众多蚊子肆无忌惮地猛烈进攻,我当然没有招架余地。这,能算公平吗?不行,我要向蚊子挑战,与蚊子较量。
我四处向旁人打听对付蚊子的经验,有位朋友嗤之以鼻地说:“蚊子嘛,能咬你多痛,习惯后就好了。”看她满不在乎的神情,我由生的可怜——她难道真的甘心被蚊子任意侵略和宰割?
归结了多种说法,不外是用蚊香。
翌夜,我算是有备而战了。早早地把门窗紧闭,宁可忍受闷热,也不愿再和蚊子亲近。蚊香的怪味在房间弥漫,熏得我鼻塞头晕,暗自偷乐——我都快熏晕了,何况弱不禁风的蚊子?在自得中我安然入睡,并放肆地把胳膊、腿伸在被单外。睡至半夜,又被阵阵刺痒惊醒,我一跃而起,迅速地打开灯,赫然瞧见只要露在外面的身体部位全部遭到袭击。我边挠边想,这北京的蚊子真是见过世面,蚊香的味对它已是习惯成自然了。我为自己的掉以轻心而后悔,是呀,经过大风大浪的蚊子,这小箭小镖的又怎能奈它如何?
连败了几场,依然削减不了我作战的锐气。拍蚊子,是我每晚的必修课。孙子兵法曰: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在和蚊子的对峙中我偷窥到,蚊子在乘人开门时会敏捷地钻进屋,好似它早已在门口等得不耐烦了,机会一到就毫不客气地成了不速之客。蚊子在白天常出动,房间亮着灯时也很少有,它们总是聪明地隐藏在屋顶或和它颜色接近的物体上。我时常为蚊子的高智商感到惊讶。临睡前,我用湿毛巾四处扇,有的蚊子沉不住气,飞了起来,我便身轻如燕地跃起把它狠狠拍死,把消灭的蚊子放在一起,然后满怀激动地欣赏这些瘦小的战利品,仔细的研究着它们。蚊子呈深灰色,长有尖尖的长嘴,就是这张嘴吸了不知多少人的血,传播了多少疾病。它有一个专门盛装偷吸无辜者鲜血的大肚子,还有帮它助纣为虐的一双翅膀和三对细长的脚。蚊子在空中飞舞的时候猖狂而得意,被拍死后,堆放在一起便显得那样无能、丑陋和龌龊。
凭我个人的力量似乎有些力单势薄,于是,同舍人也参加了大战。每到夜幕降临时就开始了灭蚊行动。我们大眼瞪小眼,努力地寻找蚊子的倩影和芳踪。谁拍住了一只蚊子就炫耀一番自己的身手,常常是和蚊子的战争演绎成了我们的竞赛。
我心里很明白,纵然是布下天罗地网、战果累累也不能掉以轻心、放松警惕。睡时我用被单盖得严严实实。果然,不到五分钟,幸存的蚊子又在耳边嗡嗡作响,并把目标瞄准我的脸部,进行狂轰乱炸。清早起床,同舍人看见我满脸的红点,肿眼泡瞪得贼大,说:“呦!都什么年龄了,还长青春痘?”我一照镜子,不免吓的一机灵,感叹道:“我还是学乖点,露个胳臂任它咬吧,只希望它留情放过我的脸部。”
现代汉语词典对“蚊子”一词这样注明:雄蚊子吸植物汁液,雌蚊子吸人和畜的血液。我思忖,人有善恶之分,莫不说蚊子也有贵贱之别?
天渐渐转凉,我们和蚊子的战争也面临着结束。回忆这段时光,不禁联想到现在的社会像蚊子这样的人不是很多吗?他们不顾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瞅准机会能捞一把是一把,完全不考虑给社会和他人带来的损失和痛苦,抱着自得其乐的腐败人生观,侵蚀着改革开放的大业。蚊子自私自利的本能,见缝插针的特性,在他们身上淋漓尽致地体现着。虽然,有许多的法律在制裁着他们,但就像蚊香对蚊子的抵御,只是被动的、死板的、甚至是徒劳的。让我们担忧的是,蚊子只是在夏季显身,而像蚊子一样的人却无时不在,无处不存。
知识是从刻苦劳动中得来的,任何成就都是刻苦劳动的结晶。
换童裙
妈妈的女儿哟
长到十三四岁
鸡鸣起床来
出门天没亮
不怕大雪漫天飞
一天要背三背柴……
优美而古老的民歌唱起来了。我知道姑娘的童裙已换了。年长的妇女们把换童裙的姑娘围在中间,身边的火光把她们紫色的脸映得透红。沙子和我干着急。我们是汉子,不能参与,去偷看是不道德的行为。下午沙子来约我,我说我不去,有啥看头,他坚持要去,说就是要去。我知道他喜欢那位姑娘,那姑娘十六岁。我执拗不过他,便来了。
按民俗,凡十三到十七岁的彝族少女,经过这个仪式才能参加社交活动,才能与相好的青年男子谈情说爱。
现在什么也没看到,而且蹲在灌木丛里,动都不敢多动一下,周身甭提有多不自在。我说:“扫兴扫兴!”“嘘——小声点。”沙子几乎是哀告。
这时妇女扯开圈子,围着火跳起舞来,一位嗓音极好的姑娘唱歌,女主角也出现了。往日的独辫不在了,梳成分头。以前红白两色相间的童裙被中段为黑蓝两色的裙子所代替。漂亮极了。
“沙子,活象个新娘。”我俏皮地说,他使劲捶我,呼吸急促。
“我们如花似玉的姑娘哟,你喜欢上谁呀?”那嗓音极好的姑娘唱着问。
“一定爱上在山外边读书的俄吉沙子了吧。”一个正在欢跳的姑娘唱着答。
女主人公羞红了脸,捂脸不是,搓手不是,玩刚分开的头发也不是。
火光在跳跃。一个民族亘古的主题都在火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
我悄声对沙子说:“嗨,活象含苞待放的山花。”我故意把“含苞待放”说得很重。这边沙子激动得抖做一团,只晓得用拳头捶我。这下该我哀告了:“别捶了,再捶,我就要喊那姑娘的名字啦……”
这时,一个年长的阿妈说:“没关系,你现在自由了,爱谁,就大胆去爱吧。”……
那年沙子和我都十八岁。如今沙子的孩子已四岁了,不但会喊我“干爷”,还能帮沙子看羊子了。我呢,从一个地方漂泊到另一个地方,依旧没有找到港湾。但是我想起老阿妈的话和那夜贼头贼脑偷看的场面,我永远觉得年轻而激动人心。
看呀!世界不是劳动的艺术品吗?没有劳动,就没有世界。
岁月的根
山中妇人
儿时的乡村是多雪的。
那年我十岁。
我的好奇心驱使我随着砍柴的哥哥及院里的伙伴进了山。
踏着积雪,翻过一座山,穿过一道山腰,在一个平坦的坝子边上,砍柴的便各自行事了。
我饿了,哥哥却无暇无力搭理我的饥饿。
坝子那边应该有座土屋,我已看见在风里歪歪扭扭的炊烟了。于是,饥饿挟着恐惧迫使我朝土屋潜了过去。
我听见柴禾在宽大的灶堂里噼噼啪啪作响。门并没关,一个穿红袄子的女人正在往火里送柴禾。
我在退缩,我怕!我想起了自己读过的半懂不懂的《聊斋》。
女人仿佛看见了我。立起身,往红袄上“啪啪”拍了几下沾上的柴屑,然后两手互拍了两下,弓身朝面前的大锅里抓了什么东西,在我退缩的目光里,来到我面前。
我看见两个圆溜溜直窜热气的红薯!
我红通通脏兮兮的小手,从那双红肿的咧开大口小口的手里接过红薯。在女人的微笑里,我羞涩地吞咽起香甜的红薯来了。
十七年的风雨过后,山野里的那幢土屋估计已经换了容颜。我想循着记忆的来路,转回头,去看看那位红袄女人。当年,她应是新嫁娘吧!
老宅
祖母既已离去,老宅便只剩下一个躯壳。
灶台上的香炉依旧,我看见袅袅的烟雾如一只只轻盈的鸟儿,在昏暗的灶间扑楞着翅膀。灶台前,我和矮小的祖母正在进行晨昏三叩首的仪式。我听见祖母念念有辞的祈祷了……
泪来了,一切都是乌有。
老宅没了灵魂,也是朽了。
老宅曾经是怎样的青春噢,一如我蓬勃的秀发:笑语喧哗,瓜果飘香,鸡犬之声相闻……
如今,没了人的疼爱,老宅真的老了,犹如暮色的老人。它老迈的神经再也经不起我年青脚步的震颤了。
可怜的您哟,当初为何不庇护好在您怀里的我的祖母!
子规夜啼
“播谷——,播谷——”
你清脆的啼鸣,在城市的夜空嘹亮地响起。
你是在城市的罅隙寻找懂你的农人么?
其实城里人也是需要提醒的。
你的呼唤带我回到了故乡,那个春天的田野永远铺满紫云英的小村庄。
你在城市的垛口寻找家园,栉风沐雨。然而,你甚至未能找到一棵可以栖身的树,或者屋檐。
在鳞次栉比的城市丛林里,冷冰冰的钢筋水泥咯疼了你。于是你只有不停地啼叫,拼命地飞翔。
你的血泪滴落成花,盛开在城市的土地上,那可是杜鹃花?
哭泣的泥鳅
七月流火。
菜场外,白惨惨的人行道上,一条从猎人屠刀下逃命的泥鳅,正在惊惊惶惶把自己藏在路道的坑缝里。
她无处可逃,她觉得自己快要被烤焦了。
一双又一双大脚朝她铺天盖地而来,她一边哆嗦着,一边尽量缩着身子。她只想捱到黄昏后,再继续自己的逃生之路。
哼哼唧唧的泥鳅陷入了无尽的悲伤里,他在哭泣失去的乐园。
“哈……,我家咪咪又可以打牙祭了!”
伤心之极的泥鳅,被一双带茧的老手紧紧捉在了手里,为防止她再度出逃,主人用塑料袋将她滑溜的身躯紧紧缚住了。
泥鳅哭不出来了,因为她已经背过气去。
邂逅
我是在荒冢与废墟的旷野与你相遇。那时,凄冷的雪花没有边际地覆盖下来。罩住了旷野灰色的我,我在白色的网里作彻底绝望的颤抖。
寂寂无人的旷野里,连一只鸟儿也不肯留在这样的寒冷里陪我。在渐渐的冰冻里,我没有奢望有谁会来和我一起颤抖。
远远的,你向我走来,手里扬着一根鞭子。难道你也信那个疯子,到女人那里去,非得带上鞭子。
不,我是用它来抖落将你紧紧缚住的雪花。
你拯救了我!
你对我说:咱们回家吧!
今日复今日,今日何其少!今日又不为,此事何时了!人生百年几今日,今日不为真可惜!若言始待明朝至,明朝又有朝朝事。为君聊赋今日诗,努力请从今日始。
扫垃圾的老人
我的新家是一片宿舍区。宿舍地处林木苍翠的半山腰上。我时常悠闲地漫步在宿舍前的山路上。
扫垃圾的老人朝我走来,永远低垂着眉眼。也许,他觉得自己不配对任何人微笑。
一副担子,不干净的筐里永远装着垃圾。老人一手扶着肩上黄亮的楠竹扁担,一手提着一把随时会在脏了的地上拂上两拂的破扫帚。三伏天了,老人那身捡来的黄军装便整天吸附在他瘦瘦的脊背上。许久以来,老人以满是汗味的形象走过衣冠楚楚的人流,走过裙袂飘飘散发着“毒药”香水的我的身边。
每月的第一个星期天,清晨,老人沙哑的声音便从门缝里传入我困倦的耳朵。
“收渣滓钱了!”
开门,老人站在门外。对于我的出现,老人甚至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只是微微向我伸出一只枯手。
久了,对他,我便有了新的发现:人们扔在门外的东西,若是他觉得有用,他就会规规矩矩地摆在住户的门边,怕是住户错扔了东西。两三天过去了,未被收回,他才喜滋滋捡了去。
走在宿舍外的路上,清爽的路面使我偶尔会想起那位扫垃圾的老人。我不知道老人住哪里,只是经常看见他来宿舍区用水。
一天,单位领导发现来此讨便宜的人太多了,便一把大锁锁住了宿舍区的清静。
我上屋后山坡的公厕时,看见老人用一个浑身补丁的铁桶搓洗衣服。当时,他正坐在厕所旁的小路上,小路那边是一个窝棚。我心里“咯噔”一下,这窝棚可是老人的屋子?我不敢对窝棚作过多的窥视,我怕那是一种残忍。
“老大爷,你到宿舍去洗吧,没人会说你的!”
说这话时,我有种做小偷的惶恐。我迅速而认真地扫了一眼老人的面容:突鼓的眼,黄黑的脸,典型的尖嘴猴腮。
老人没有对我的关心做出及时的反应,依然垂着眼。嘴角动了动,想说些什么,最后只是讪讪地笑了笑。老人的笑容很不美观。其时我已逃开。
终有一天,我按捺不住好奇,假装从那间小屋前的小路经过。我匆匆地朝小屋瞥了一眼。就一眼,我把小屋看了个透明:十平方米左右,土墙,房顶或许有瓦,然即使有,也残缺了。因为整个屋顶被一张张捡来的塑料薄膜覆盖着。风一过来,便一片“哗啦”之声。小屋内部的格局我不甚清楚。我看见门前屋檐的塑料薄膜由棍棒支撑着伸出好长一溜,这大概是厅堂吧。老人平时的洗衣做饭大概就在这里进行了。
老人的小屋,唤起了我来自心底的悲怜。那应当是鼠类的家园!正当我对小屋倾注我所有的同情的时候,我又有了一个新的发现,这个发现差点让我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