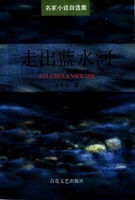梅子又熬过了一个无眠之夜,早晨起来精神恍惚,走路像踩在云里。用温水洗了头,又在太阳穴上擦了清凉油,暂时抑制了困倦。接着开始涮锅点火。她给父亲预备了一天的饭菜,自己却一口沒吃。出门的时候被老爷子叫住了。老爷子坐在门后,门半开半掩,旮旯里光线很暗。老爷子抱着膀子趴在自己的膝头上,倦缩得像个螺。只听一个沧桑的声音在幽暗中说:我的时间不多了,有沒有人送终都沒啥。小西还没成人,不能扔下他不管。梅子强忍着伤感,说:爸你放心,我是出去有事,昨晚跟你说过。老爷子说,这就好。去吧,别担心我。
梅子在新村工地又遇到邹浩东,他还是坐在砖堆上看着几间半截子屋仓发愣。工程停建有日子了,丝毫没有复工的迹象。看来这个冬天没有希望住进新房了,邹浩东除了在这里发愁也没有任何办法。梅子走到这里停了一下,邹浩东是侧着路坐的,肯定看到她了。看不到也听得到脚步声。但他却装看不到,或者并非装,只是不屑一顾。梅子站了一分钟,然后默默地走开了。和王二柱的事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她没法说清楚,随他怎么想吧!现在更重要的还是一百万的下落,弄清楚了这事儿,黑洼容不容人都无所谓,到哪里都是活一世人。
经过村口,梅子的视线避不开那座断碑。断碑像根刺,戳在她心里,现在连她都想把这块碑搬走,眼不见心不痛。死鬼呀,你看你给我留的遗患!你让我咋法活呀?
在后垱上车的时候,梅子突然有种奇怪的感觉,好像背后有双眼睛。这种感觉在进城以后又重复了几次,每次回头结果都是一样的:后面并沒有可疑的人。她觉得奇怪,为什么会反复出现同一个错觉?
刚出车站大门就有一辆麻木截住了她,麻木截客有个常识:下车东张西望的人被劝上车的概率比较高。大姐去哪儿?梅子东张西望本是因为那个错觉,被麻木一问才发觉这还真是问题。梅子说,东街有个夏雨百货店吧?这话外行了,她传出的信息是她对自己的目的地缺乏认识。这给了开麻木的一个钻空子的机会,结果五块钱的路程绕成了十五块。梅子的确沒到过东街,东街是县城的另一个极地,没事走不到那个地方。知道夏雨百货在东街还是夏雨告诉她的,那已经是五年前的事了,如今还有没有这个店都不确定,只能这么问。
五年前夏雨给梅子制造了一个意外,那时夏雨和林向西的事情已经开了天窗,换了是谁夏雨都会有场麻烦。夏雨也在等着这场麻烦的降临。但结果让她很意外,梅子没去找她。梅子有梅子的考虑,她认为林向西就是贪色,男人都有这个坏毛病。男人的毛病应该在家里治,闹到外头去不好。男人要面子,自己也还要尊严。这对夏雨来说实在是一种幸运,但夏雨没有为自己庆幸,她反而决定去找梅子。夏雨有一个愿望,在她决定退出之前要把这个愿望托付给梅子。梅子那天正在柿树下洗衣服,夏雨突然出现在她面前,这是她无论如何想象不到的事情,发了好一会愣。手里还提着正在浆洗的衣服,浆水稀里哗啦往下淌,那个样子好像她是第三者似的。与其相反,夏雨因是有备而来,倒显得从容淡定:嫂子你好!梅子冷静下来,嘴角翘起一抹嘲讽:你叫错了吧!夏雨犹豫了一下,改口叫婶。梅子冷笑道:错得更远了,像我们这种关系,你应该叫姐姐。夏雨的脸上稍作颜色,很快又恢复了淡定:你有气尽管出,我保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梅子说,笑话!我还沒那么绝望,要出气不会等你找上我的门。说吧,想怎么样?同侍一夫还是劝我让位?夏雨说,都不是。我还有第三个选择:放弃。梅子愣了一下,问:是你放弃还是他放弃?夏雨说,你何必纠缠这个问题?不管谁放弃,结局对你都是一样的。梅子说,好吧!就算一样。那我问你,既然你们都放弃了为啥又来找我?要我感激你?夏雨说,我承认我伤害了你,但我今天来没有恶意。请你别用这种口气讲话行吗?梅子这才起身给夏雨端只凳子:坐下说吧!我还奇怪呢,我没找你你倒找上我了,善意恶意我都要听听。夏雨接过凳子坐下,说:我来是不放心他。就这半句话又激起了梅子的不满:你不放心他?夏雨很坦率,并不回避梅子的锋芒:你是个好女人,但不能算一个好妻子。你对他的工作不闻不问,根本不知道他在外面是怎么做事怎么做人的。我今天来就是想提醒你,别只安心做你的家庭妇女,他需要一个能约束他的人,这个人必须陪伴在左右,所以最好是女人。梅子再度起身,这次是给夏雨倒水。她把水杯递到夏雨手里:具体点说。夏雨说,不可能更具体,我不是来做工作汇报的,只能向你指出问题。黑洼的企业表面上欣欣向荣,内部却很混乱,形势一点不像外面吹嘘的那样好。这些你可能不关心,下面的话你就得关心了:企业形势不好,不是一家不好,是大局不好。我这么跟你说吧,只要他一睁开眼睛就有一大堆难题在等着他,很多难题根本就没办法解决。但他是能人,别人都这么说,他也这么认为,什么难事在他手里都必须得到解决。解决不易解决的难题需要手段,他是个不缺手段的人,但是他的那些手段多数违规违法。人就怕有侥幸心理,今天侥幸没出事明天侥幸没出事,以后胆子就会更大。常在钢丝上走,难免有失足的一天。梅子被夏雨说得一愣一愣的,她开始相信林向西对夏雨决不是单纯贪色。而夏雨对林向西也决不是猎奇。夏雨继续说,这些还不是我最担心的,我最担心的是水泥厂。水泥厂的水很深,我怕他会陷进去。就算那不是个陷阱,也会增加他的压力,增加他走钢丝的难度。梅子几乎被夏雨逼到了绝境,凭她说的这些,根本不是她能够力挽狂澜的事情。人到了无能为力的时候就要为自己找一个理由放弃,梅子忽然觉得夏雨对她说这些是有用意的,这是在拿林向西的安危威胁她。什么放弃?没有放弃的借口说不出来这些话。梅子又恢复了她冷嘲热讽的语气:妹妺比姐姐能耐大,你可是一直陪在他左右的,就没约束他?夏雨听出了梅子话里的火药味,针锋相对地顶了一句:我想单独和他说句话都得躲躲藏藏的,能起多大作用?梅子双掌一合:哦,明白了。你这是在要名份。夏雨勃然作色,恨恨地把手里的水杯摔在梅子面前,气咻咻地走了。
梅子做梦都不会想到她今天会来找夏雨,这和当初沒有想到夏雨会来找她一样。不能不承认她的动机不如夏雨有情操,夏雨找她是为林向西,而她找夏雨是为林向西的遗产。
梅子付了车费,站在夏雨百货铺外整理情绪。她需要一份自信,自信是实现目标的保证。她还需要一种说辞,得让夏雨相信她并不是冲遗产来的。她可以不要一分钱,只要一个答案一种公正。就在这时那个感觉又出现了,这次还不仅仅是感觉,她仿佛看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在视觉中闪了一下。等她去捜寻目标时,人流中又都是一张张陌生的面孔。究竟是错觉还是真有人跟踪?她环顾了一下环境,仄身走进对街的一间服装店。服装店有一面试衣镜正对着大门,她站在衣架前试着一件上衣的手感,眼睛却盯着那面镜子。可能是这个动作保持时间长了点,也可能是她的神情不对劲,引起了店老板的注意。店老板是个中年男人,高佻瘦削,西装革履,却在腰间松松垮垮地系了一个腰包,显得不伦不类。他晃到梅子面前,毫不掩饰他的猜忌:是不是买衣服的?梅子见他不友好,自己也友好不起来:看看不行啊!痩男人说,还真不行。我的衣服很贵的,不买别伸手,摸脏了没人要。梅子心里懊丧,走一百里遇不到个好人,够倒霉的。她走出服装店,站在街心左顾右盼,看到的仍然是一张张陌生的面孔。看来是我太紧张了,人紧张了容易产生错觉。
梅子走进夏雨百货铺,感觉视线很拥挤。四壁全是货架,中间还横列了三排。从地面到天花板,三四米高的空间被五颜六色的商品塞得满满的。与丰富驳杂的陈列对比,店内显得过于冷落,只有三、五个人在狭窄的甬道倘徉,一副还没想好买什么的神情。门口收银台后窝着一个无法判定年龄的男人,小眼睛滴溜溜地监视着顾客。搭眼一瞅,横竖不见夏雨。梅子凑近小眼睛男人打招呼:大兄弟忙着啦!大兄弟木然地眺了她一眼,问:有事?梅子说,我找夏雨。大兄弟听她说找夏雨,小眼睛大了一圈:山里出来的?梅子说,哎!小眼睛忽然眺过梅子的额头,冲后边喊:商品看过后请归位,谢谢你的合作。小眼睛明显不准备归位了。不在!这倆字儿是给梅子的。梅子问:去哪了?回答说,进货。梅子又问:在哪儿进货?回道:襄樊。梅子心想,咋两个字两个字地吐啊!是不是我问得也太简洁了?大兄弟,夏雨妺妺啥会儿能回来?大兄弟这回吐了三个字:不知道。
从夏雨百货铺出来,一时沒了主意,不知该往哪儿走。早知道有今天,当初不该把房子退了。如果夏雨天黑前回不来,晚上得去住旅店,几不方便。她六神无主地在街上蹓跶了一会儿,感觉好惆怅。凭什么我得面对这些龌龊难堪的鬼事?人都死了,谁愿意纠缠谁去纠缠好了。她一冲动,真恨不能掉头回去。这也就是个念头,她清楚自己不能跟着这个念头走。找不到答案今生今世别想在黑洼抬起头走路,还要准备接受司法追究。林向西呀林向西,你看你都干了些什么?
梅子转了一圈又回到夏雨百货店,夏雨还是没回来。她不想走了,在街上走路真累。进店找小眼睛男人要一块纸皮,小眼睛问她干什么用?她说,我在外头坐一会儿。小眼睛说,你别等了她今天回不回来还不一定。梅子说,我还是等一会儿,这么远来一趟不容易。小眼睛问:你是她什么人?梅子想了想说,我是她姐。小眼睛说,她只有个妹,哪里蹦出个姐来?梅子说,堂姐。小眼睛将信将疑,给了块纸皮她。她在外面一屁股坐下来,就等于坐在了小眼睛的心里。从县城发往后垱的最后一班车是下午五点三十分,错过这趟车她就得滞留下来。滞留下来就牵涉到吃和住的问题,万一她真是堂姐,那就得由他们安排。安排一个人的吃住也不成问题,主要是麻烦。梅子出去以后小眼睛就进了一趟卫生间,在里面给夏兩打电话,让她快到店里来。原来夏雨根本沒去进货,而是在家里。夏雨问男人有什么事,男人说,你堂姐找你。夏雨说,我哪里来的堂姐。男人问:你见不见?不见我就撵她走。夏雨说,谁让你撵了?让她等一会儿我马上过来。
夏雨见到梅子时比当年梅子见到她还意外:怎么是你?梅子一副难为情的样子:对不起,打扰你了。夏雨有点揶揄的意思:没想到你会来找我。梅子说,我也没想到。夏雨问:什么事?梅子踌躇着:想跟你谈谈。夏雨很犹豫:还有什么可谈的,都结束了。梅子说,还是谈谈吧,谈了才知道结没结束。夏雨的目光在梅子的脸上停了几秒钟,说:那家里去吧!
夏雨的家要穿过这条街,再过一条臭哄哄的污水沟。桥头有座院,门楼灰败破落。两扇钢栏门上加置了一道拱弧,弧上有几个锈蚀的铸字:东街针织厂。显示着这个院落曾经是一个街道小厂。如今这个院是县城最早的商品住宅区,入住的都是进城经商的农民。放在大城市应该是个什么花园,放在小县城就是一个迁徙过来的农村,有着农村一样的混乱和肮脏。梅子跟在夏雨后边,小心地绕过脚下无处不是的拉圾袋和小孩粪便往里走,一直走到最后一幢楼。踏上楼梯的一剎那,梅子忽然发现自己两手空空。夏雨回头问:怎么啦?梅子有点窘:我、我应该给孩子买点啥。夏雨冷冷地说,我没孩子。梅子的窘态凝固在脸上,她不知道该为夏雨表示祝贺还是表示惋惜。
夏雨把梅子让进客厅。客厅很大很厰亮,陈设不多但该有的都有。梅子在沙发上坐下,接过夏雨递来的水杯,问:林向西的事知道吧?夏雨反问:你指什么?梅子想了想,说:他有一本日记在网上传播。你上网吗?夏雨说,很少。他的日记有涉及到我?梅子说,都是官场日记,沒有涉及到私情。夏雨问:那你为什么找我?梅子迟疑了一下,说:涉及到一笔款子,一百万。夏雨问:什么性质?梅子说,黑吃黑。算受贿吧!夏雨挺吃惊:他受谁的贿?梅子说,胡水垓。夏雨冷静下来,她开始猜测梅子的来意:你认为这件事和我有关?梅子说,我想不出还有谁是他信任的人。夏雨说,那你就想错了。我走的时候他们正闹得不可开交,根本不可能发生这种关系。梅子说,是你错了,我来不是了解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我、我是来追查一百万的下落。夏雨勃然变色:你什么意思?梅子想:到这一步了也沒必要再顾惜颜面,必须把话说透。因而说:林向西这个人你我都清楚,他不是乱花钱的人,一百万不可能在他手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定是托负给谁了。
夏雨显得出奇的平静,愤怒在她心里:你说完了吗?梅子说,我就这个意思。只要一句话,不要钱。夏雨起身开门,不小心碰了茶几的一只角,掀翻了梅子面前的水杯,一杯水刚好泼到梅子的裤裆里。夏雨说,出去。梅子一边掸着裤裆里的水一边说:夏雨你别误会,我
不是为争遗产来的。夏雨突然大声喝道:滾出去!
夏雨连推带搡地把梅子逐出了家门,梅子在外头说:我会一直坐在门口的。她说到做到,当真一屁股坐到天黑。这时候在街上做生意的人陆陆续续回来了,这些人都算是土财主。财主怕贼掂记,对楼道里赖着一个生人很犯忌讳,纷纷来拍夏雨家的门,问是怎么回事?夏雨不耐烦,冲人喊:我怎么知道?我又不认识。说完哐当一声甩上门。后来楼道里聚的人越来越多,连别个单元的人也跑来凑热闹。有问的有劝的也有恐嚇的,梅子不好说明来意,只说有事找夏雨。围观的人说,夏雨不认识你呀!梅子说,她说的不是真话。孰是孰非无从判断,人们议论着:还是报警吧!梅子心想,报警也许是好事,说不定能镇住夏雨。后来果然有人报了警。城关派出所来了两个警察,上来就要带她去所里问话。她也没有声诉的机会,只能随人家走。走的时候冲夏雨的门喊:夏雨我还会来的。